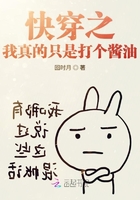我进来的时候,福尔摩斯正弯着腰在一个低倍显微镜上观察着。不久他直起身来向我介绍观察的东西,我以为是他办的一个新案子。他告诉我是帮一个朋友——警署里的梅里维尔——办一个案。一会儿他不耐烦地看着表。
“我有个新主顾要来,已过了预约时间。对了,华生,你懂赛马吗?”
“应该说懂一点,我的负伤抚恤金有半数浪费在这上面了。”
“那你就暂时充当我的赛马指南。你听说过罗伯特·诺伯顿吗?”
“当然。他住在肖斯科姆别墅,我对那儿了如指掌,因为我曾在那里住过一个夏天。有一次诺伯顿差一点吃官司。”
“怎么回事?”
“他在纽马克特用马鞭几乎把萨姆·布鲁尔打死,此人是科尔曾街的一个放债人。”
“嘿,他真有两下子!他常那么干吗?”
“是的,他可是有名的危险人物。据说他曾取得利物浦障碍赛马的第二名。但他与自己生活的时代格格不入。”
“了不起,华生!你能告诉我一些肖斯科姆别墅的情况吗?”
“它位于肖斯科姆公园的中央,这里有个着名的肖斯科姆种马饲养场和训练场。”
“教练官是约翰·马森。”福尔摩斯说,“我刚看的这封信是他寄来的。还是再谈谈肖斯科姆吧,对它我极感兴趣。”
“英国一流的狗肖斯科姆长毛垂耳狗,肖斯科姆的女主人以此为荣。”
“女主人是罗伯特·诺伯顿爵士的妻子喽?”
“罗伯特爵士没有结婚。女主人是他丧偶的姐姐比特丽斯·福尔德夫人。”
“这个宅子其实属夫人的前夫詹姆斯所有。罗伯特先生在这儿没有任何产权。在夫人有生之年,产业的利钱归她,在她死后房产则归还他的小叔子。她只是每年收租钱。”
“这些租钱就由罗伯特花了吧?”
“差不多。他是一个随心所欲、不计后果的家伙,可是我听说她对他非常好。那么,肖斯科姆出了什么乱子呢?”
“这正是我想知道的。能为我们解释些事的人来了。”
门被打开,走进来一个整洁、高大的人,此人名叫约翰·马森,他是肖斯科姆驯马师。他镇定自若地鞠了个躬,在福尔摩斯指给他的椅子上坐下。
“福尔摩斯先生,我的信接到了?”
“是的,有什么解释。”
“这件事十分敏感,相当复杂,不好一一写在纸上。我只能和你面谈。”
“好吧,你说吧。”
“首先,福尔摩斯先生,我觉得我的主人疯了。”
福尔摩斯扬起眉毛说:“你这样说有根据吗?”
“先生我的主人近来办事十分古怪。我觉得肖斯科姆王子和赛马大会把他给弄得神经失常了。”
“肖斯科姆王子?是你驯的一头小马驹吗?”
“是全英国最好的马,福尔摩斯先生,这一点我绝对有把握。在这次赛马比赛中,罗伯特爵士只能取胜,他已经铤而走险了。他把他能弄来的钱都押在这匹马上了,而且赌注的比值也悬得吓人。押的是近于一比一百。”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他在做孤注一掷的游戏,现在他心里装的全是马和赛马的事,这是他的生命。王子一旦失败,他也就破产了。”
“可你凭什么认为他疯了呢?”
“憔悴的面孔。晚上没睡过觉,他整天呆在马圈里。他两眼发直,神经绷得快断了。还有他对比特丽斯夫人的行为!”
“什么行为?”
“他们感情一直很好。他们兴趣相同,她也像他一样爱马。她每天准时坐车来看她最宠爱的王子。那匹小王子,一听到石路上的车轮声,就立起耳朵,小跑到车前去吃那块糖,可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为什么?”
她对马似乎已经完全失去了兴趣。一个星期以来她虽然每天驱车路过马圈,对于王子却毫无表示!
“他们吵架了?”
“而且吵得很厉害,互相仇视。否则,他绝对不会把她的狗送人的。前几天他把狗送给了胜隆旅馆店主人老巴恩斯。”
“很奇怪。”
“夫人心脏不好,又浮肿,以往他一直每天晚上到她屋里坐上两个小时。因为她们姐弟感情很好。可现在他再也不亲近她了。因此她很伤心,心情变得郁闷,开始酗酒,福尔摩斯先生。”
“在俩人疏远以前她喝酒吗?”
“也喝一杯,但现在她一晚上就能喝一瓶,太吓人了。这是管家斯蒂芬斯告诉我的。更奇怪的是,主人为什么深夜去老教堂的地穴?谁在等他?”
福尔摩斯的神情更加专注。
“讲下去,马森先生,你的话越来越有趣了。”
“我和斯蒂芬斯万分小心地跟着他。”
“他去的是那个闹鬼的地穴,那儿还有人在等他。”
“这个地穴在什么地方?”
“一个教堂的废墟,既古老又破旧,根本无人知晓,它的年代久远。它下面有一个地穴。白天那地穴就很阴森恐怖,晚上更没有几个人敢走近它。但我们的主人胆子很大。不知他夜晚到那里去干什么呢?”
“等一下!”福尔摩斯说,“你说那儿有人在等他。你一定认识他和他说话了吧?”
“我不认识。”
“你怎么知道?”
“有一个晚上,我和斯蒂芬斯则像兔子似的躲在灌木丛中。在月光下,我们看见罗伯特爵士从地穴那儿回来,当他走过我们身边时,我们听见后面传来一个人的脚步声。等罗伯特先生过去后我们就直起身来,假装散步不经意地碰见他,我问他:你好,伙计,你是谁?他看见我们时,就像是看见了地狱的恶鬼。他大叫一声撒腿就跑。眨眼间就踪影全无了,他是谁、是什么人我们都不知道。”
“月光下,你看清他的脸了吗?”
“是个黄脸的下等人。他能和罗伯特爵士有什么关系呢?”
福尔摩斯沉默起来。
“谁陪伴比特丽斯·福尔德夫人?”他终于问道。
“她的侍女卡里·埃文斯。五年来她一直忠心耿耿跟随夫人。”
他们兄妹争吵原因是什么?
“可能为了他跟女仆的关系。”
“我们可以假设夫人过去并不知道,现在突然发现了。她想辞退她的侍女,但她弟弟不同意。这个弱者由于身体不好,又不能走动,没法实现自己的意愿。她怀恨的侍女仍打发不走。于是她对任何人都不说话,独自生闷气,借酒浇愁。罗伯特爵士一气之下送走她宠爱的小狗。这不是都联系起来吗?”
“是的,这些好像还能联系起来。”
“对极!但他去地穴去干什么呢?这还无法解释。”
“还有更充令人费解的事。罗伯特爵士为什么要去挖一具死尸呢?”
福尔摩斯霍地站了起来。
“昨天罗伯特爵士到伦敦去。我和斯蒂芬斯下了地穴想看看,一切都是原样,发现在一个角落里多了一小堆死人的尸骨。”
“先生,这只不过是一具千年古尸的头和几根骨头。我们也没有去在意。”
“你们怎么办了?”
“我们什么也没做。”
“这样做是明智的。罗伯特爵士,现在回来了吗?”
“今天应该回来。”
“罗伯特爵士把他姐姐的狗送人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一星期前的这个时候。那天早晨罗伯特爵士心情正坏得很,小狗在房外汪汪叫。他就把狗抓了起来。他把狗交给了骑师桑迪·贝恩,叫他去送给胜隆旅店的老巴恩斯,他讨厌这条狗。”
福尔摩斯点燃烟斗沉思地坐了许久。
“马森先生。”他最后说。“还有什么奇怪之处吗?”
“你看看这个,福尔摩斯先生。”客人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纸包,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有一根烧焦的碎骨头。
福尔摩斯兴味很浓地查看起来。
“你从哪里弄来的?”
“在比特丽斯夫人房间底下的地下室里有一个暖气锅炉,已经很长时间没用了,罗伯特爵士抱怨说天冷,让仆人开始烧暖气。负责烧锅炉的哈维是我的好朋友。今天早晨他突然拿着这个来找我,说是在掏锅炉灰时发现的。”
福尔摩斯说,“你能辨别一下吗,华生?”
“这是人大腿的上髁骨。”我回答说。
“不错!”福尔摩斯的神情立即变得非常严肃。“那个仆人通常什么时候去烧炉子?”
“他每天晚上烧起来后就走。”
“就是说晚上那里没有别人了?”
“是的,先生。”
“从外面能进到那里去吗?”
“外面只有一个门,里边还有一个门顺着楼梯可与比特丽斯夫人房间的过道相通。”
“这个案子非同寻常,马森先生。而且有浓浓的血腥味。你说昨天罗伯特爵士不在家?”
“不在,先生。”
“那么烧骨头的不是他,而是另有其人?”
“不错。先生。”
“你刚才说的那个旅店叫什么?”
“胜隆旅店。”
“那一带是不是有个不错的钓鱼的地方?”
这位诚实的驯马师露出不知所措的神情。
“我听说在那里能钓到鳟鱼和狗鱼。”
“那太好了。华生和我非常爱好钓鱼,你先给胜隆旅店送个信儿,就说我们今晚就过去。现在你回去,有事也不能去那儿找我,只要写个纸条就行了。如果需要的话,我去找你。”
于是,在一个爽朗的五月之夜,我和福尔摩斯来到了胜隆旅店,一个旧式的小旅店。热情好客的店主乔塞亚·巴恩斯热切地询问我们钓鱼的美好计划。
“在霍尔湖能钓到狗鱼吗?”福尔摩斯问。
店主的脸一沉:“别打那个主意,先生。鱼没钓到,你就会先到水里了。”
“为什么?”
“因为罗伯特爵士非常不喜欢别人动他的鳟鱼。你们两位陌生人要是走近他的训练场,他决不会轻饶你们。”
“听说他有一匹马参加比赛,是吗?”
“是的,一匹非常好的马。我们大家和罗伯特先生一样,把钱都押在它身上了。”说完他怀疑地望着我们。“你们不是马探子吧?”
“看你说的!我们只不过是两个身心疲惫、渴望伯克郡新鲜空气的伦敦人。”
“那你们可找对地方了。这儿新鲜空气有的是,但是,请记住我的警告,离公园远些为妙。”
“我们当然会的,你放心。对了,大厅里叫唤的那个狗长得可真不赖。”
“你真有眼力,那是真正的肖斯科姆狗,全英国最好的。”
“我也是个养狗迷。”福尔摩斯说。
“冒昧地问一下,这条狗值多少钱呢。”
“先生。这条狗是罗伯特爵士自己给我的。我怕他会跑回别墅里去才把它拴住的。”
说完,店主就走过去招呼狗。
“华生,咱们乘罗伯特不在。今晚去一趟那个禁地打探一下或许用不着挨他的铁拳。有点情况我需要证实一下。”
“你有什么假设吗,福尔摩斯?”
“弟弟不再在去看望亲爱的疾病缠身的姐姐了;他又把她庞爱的小狗送了人。华生!你还看不出问题吗?”
“我只看出弟弟的残酷无情。”
“这儿还有一种可能。如果这场争吵存在的话。夫人闭门不出,一改常态,除了和女仆乘车外出就不再露面,而且不再在马房停车去看她宠爱的马,开始酗酒,都说全了吧?”
“还有地穴里的事。”
“那是另一条线索。它们是不同的两件事,你不要把它们混为一谈。第一条线索是关于比特丽斯夫人的,闻没闻到犯罪的味道?”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