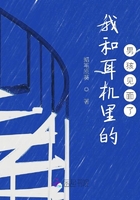这么一张脸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吓得尖叫一声,人猛地往后栽倒,矿灯脱手掉在那人的脚下,条件反射地就把手上的洛阳铲挥了出去。人在危机情况下的潜力总是很大的,这一下的攻击力气极大,正中了他的面门,额头上的一块肉就被铲了下来,露出森然的白骨。
我一把他打倒在地,就手忙脚乱地转过身,往那边爬去,没想到他的速度极快,一下子就站了起来,身体探进塞石里,两只手抓住了我的脚踝,把我用力往外拽。
他的力气极大,抓住我的脚腕的手好像铁箍一样,好像要把我的脚踝扭断。我的整个身体趴着被他拉得往外走,手挣扎着乱画,可是四周都十分平整,根本没有着力的地方,裸露的皮肤划破了皮,火辣辣地疼。
我被他从塞石里拖了出来,脚仍然被抬高拽着,可是面朝下猛地往地上摔去,我连忙用手肘去撑地缓冲,这才免去了下巴从一米高的地方磕在地上,被摔得头晕脑胀的厄运。
他一直拖着我往后倒着走,根本没有放开我的意思,而且力气太大了,我拼命地想收回脚,根本等于蚍蜉撼树,我吓得满头是汗,浑身发软。如果这要是个平常人的话,力气再大,我也不害怕,可是他这副样子,满脸是血,眼神呆滞,是不是个活人都不知道,长了这么大,我根本就没见过这样的东西,就没有对付他的经验。
我反手从腰上拔出枪,颤抖着指着他,心突突直跳,嗓子也在抖:“你放开我!不然我开枪了!”他根本就没有反应,只是麻木地把我往后拖。矿灯掉在地上,正好往这边照,我回过头一看,这个长长的甬道两侧有几道低矮的拱形石门,里面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清,可是却从其中两个里面各出来一个人。
这两个人头发都很长,披散在肩膀上,下身好像还穿了裙子……真是变态!他们动作僵硬,力气也极大,一人抓住我一个手腕,往相反的方向拉。一瞬间,我的身体就产生了撕裂了一样的痛,痛得我尖叫了起来,可是他们根本就不停手。
这根本就是想将我活活撕开!
我心一狠,管你死人还是活人,这是要杀了我了,我为什么还要心慈手软,法律里面还有正当防卫这个说法,我怎么可能坐以待毙?
手中的王八盒子威力很大,那个人拉高我的手腕,正对着他的胸部,我直接开枪,他松了手倒在地上。右手一解脱,我就紧接着给拉住我左手的那个人一枪,左手也解脱了,我腰部使力,一个翻身,朝身后开枪。
因为抓住我手腕的两个人都离我很近,所以都打在了胸部,而抓住我的脚腕的那个人,因为离我比较远,我又是第一次打枪,所以只打到他的肩膀上。他的身形微微一晃,好像没有任何感觉一样,继续走。我又赶紧补了一枪,打中胸口,他这才松了手。
脚腕一被松开,我立刻爬起来往塞石那边跑,可是没有想到被我打中的两个人还在地上挣扎,在我路过的时候,离我最近的那个,突然一伸手抓住了我的脚腕,我吓了一大跳,怎么甩都甩不掉,眼看着另外两个人颤巍巍地站了起来,往这边靠拢,我急得用枪砸他的手,可是纹丝不动。
我突然想起以前看的那些美国丧尸片,好像那些人杀丧尸的时候都打的是头部。我看面前的这三个人也根本算不上人了,第一个出现的那个满脸是血,身上的肉虽然看起来还有弹性,可是连疼都不知道,从石门里出来的这两个,黑瘦干瘪,一点水分都没有,加上浑身长的那些白毛,根本就是发了霉的腊肠,哪里还有人的样子?恐怕就是传说中的粽子,以前听人家说粽子怕黑驴蹄子,可是现在就算给我黑驴蹄子,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就算粽子算不上丧尸,那也和丧尸沾亲带故,可以试试老美的方法。
我咬了咬牙,拿着枪顶着这个人的脑袋,心里说了句:“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一枪打在他的脑门上,有腥臭的液体溅出来,喷了我一身,手立即松开了。我强忍着恶心,接着往前跑,一到塞石前,捡起矿灯就钻了进去。可是没走两步,视线中出现了一条一米多长的花蛇,正高昂着蛇头,吐着芯子,朝我示威。
一股无力感袭遍了我的全身,这几天发生的事情真是太多了。外公去世,一坑的白骨森森,绿色小怪物,第一次被亡命之徒用枪追杀,阿文的意外死亡,言言的不听话,这三个人的屠杀,现在又多了一条蛇挡住了我的逃生之路,这一切的一切,都让我心力交瘁。
我强忍着内心的酸楚,从口袋里摸出水果刀,手腕用力一掷,小刀带着蛇身猛地就往后飞去,叮的一声扎在了塞石外面的甬道里。那两个人已经到了塞石口,第一个人的身手明显灵活一些,一下子就爬了进来,而另一个却被塞石阻挡住了,只能探着上半身,腿却抬不起来。眼看这个人已经爬到了我的面前,一股子腥臭的味道扑鼻而来,我不得不屏气凝神,对着他的脑门就是一枪。他的脑袋像开了花一样,液体飞溅,腥臭味更浓了。外面的那个人对这一幕没有任何反应,依旧向我探着身子,僵硬地挥舞着双臂。眼泪快要出来了,视线很朦胧,我对他举起了枪。
这三个人一共用了七发子弹,弹夹里只剩下最后一发。后面甬道的那道石门打不开,我根本出不去,面前的甬道黑漆漆地望不到尽头,不知道还有多少个这样的人。言言不知道身在何处,有没有遇到他们,更不知道是死是活。阿文死了,爸爸他们不知道有没有事,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下去,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找到言言,更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出去。
相比被这种东西弄死,我宁愿自我解决。所以,这一枪如果不打在别人的脑袋上,我就只能打在自己的脑袋上。
我从没有像此时此刻这样思念子庚,如果他在,我就不会这么孤立无援,也不会这么害怕难过。脑海里又浮现出另一张脸,清冷的眸子,平静无波地看着我。王佑铮,他要是在,那该有多好!
命运把我推入了一个毫不可知的境地,不给我自怨自艾和痛苦担忧的机会,如果我不振作起来,就有可能死在这个地方,腐烂成白骨,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在乎。
“一分钟,就一分钟。”我对自己说:“这里没有人,我允许自己害怕难过,但是只有在这一分钟之内,我还要出去,就算是爬,我也要爬出去。”
我捡起掉落在塞石石道里的洛阳铲,回到放了四块塞石的甬道,关上矿灯,蹲了下来,静静地靠着塞石。在这个黑暗无人的地方,我很孤独很害怕,却只能抱着膝,将头埋在双臂里,让泪水肆意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