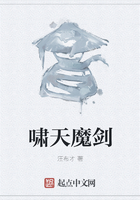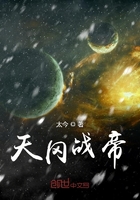初冬,土著各部落与元人的战争仍示平息,元廷开赴而来的军队零零散散,几万人驻扎于播州与思州,却不见挥师顺元与义军决一死战。而此时宋隆济名声大噪,各地土著纷纷反元,滇桂一带更是兵乱如麻,有农民起义军、部落军、元廷反叛汉军等,铁木真无暇边陲之地的重要,却恐怕宋隆济之名,影响整个朝廷,于是让兵部暗派军中武艺高强之人,前往顺元,企图暗中杀害宋隆济。
高原之地,雾气重重,阴风连连,百姓被连年战乱和税赋逼迫得家破人亡,城池之地看上去热闹非凡,而那些官道边上的村子,早已白骨一片。
播州宣慰府和都元帅府,日夜探子急报,义军步步迫近,不惧几万元军,想一举拿下播州和思州,把元人赶走。
路三平与杨邦宪原本不合,此番各路援军前来,朝廷又传来密旨,告诫路三平提防杨邦宪叛乱,为此援军将领表面到都元帅府安顿和议事,实际上有重要的军务便到宣慰府与路三平商议。路三平早就看不习惯杨邦宪平日里目中无人的个性,想趁此机会清除异己,无奈播州城内杨家军如铁笼一般,杨邦宪除了有五百人的亲兵,还有上千民兵,各方援军将领军务在身,大多不愿卷入路杨之斗,大有坐山观虎斗的阵势。
这日,路三平与众将领商议,按照元朝兵役之法,成年这人应服兵役,让都元帅府加快征兵速度,尽快组建一支千人民兵,协助元军进攻顺元。
此时,梁王阔阔遣云南行省平章床兀儿、参政不兰溪的援军与义军于南部作战,一时之间,义军被南北夹击,只是援军队伍众多,将领中有元人汉人,大家意见不合,南部军队攻打不下,而北部军队又不挥师南上,才导致义军连连取胜,声势越来越大。
杨邦宪身为都元帅府指挥使,不敢违背朝廷旨意,便张榜出去,播州范围内的男丁,一律充军。
尽管元法严明,但到民间,汉人官兵早已不服其法,私自不守法纪的众多,征兵之法从万户到千户再到百户,多半是抓些老弱病残,身强力壮的早已躲了起来,或是拿银子粮食买通官员。
征兵令下了十天,仅有百余人。
路三平以征兵不力为由上奏朝廷,一边联合各方将领,一边让心腹路冲为监军,进一步牵制杨邦宪,想瓦解杨家军。
这日,路三平请来杨邦宪商议军机大事。
“杨指挥使,不知近日征兵如何?”
“路大人,想必你也了解这民间疾苦,若是把汉人全部都抓来当兵,咱们的军粮何人来种,实不相瞒,这征兵之事举步为坚,不知路大人有何良策?”
“杨指挥使身为朝廷命官,不思叛乱之患,反思百姓之苦,难道叛军打进了京城,你还在这固守民心不成?”
“大人言重,如今南北重兵夹击,想必叛军坚守不了多日,但不知援军为何迟迟不动?”
“这倒要问杨指挥使了,军务之事一向是都元帅府的事。”
“听路大人的口气,南上镇乱,倒只是我杨家军的事?”
“不是你的事,难道是我的事?”
“为何各方首领不在我元帅府议事,跑到你宣慰府来议事?”
“笑话,本人乃堂堂宣慰使,难道不能参与军机要事?”
“在下这就上书朝廷,请辞这指挥使之职,这样宣慰大人便可统领这播州之事。”
“请便。”
二人大闹一场,不欢而散,众将领都是征战沙场之人,见惯了这种争斗,怕两方都得罪,也都坐山观虎斗。
路三平下令,让路冲带领驻军到各村征兵,务必半个月内招募一千人。
路冲原为路三平的师爷,精于算计,路三平在京城为官时仗其收敛了不少财物,到播州后,扩建路府的银两,便由路冲出谋收刮而来,路冲本人更是贪婪成性,不但苛扣朝廷的粮响,也榨压下人,中饱私襄。
任监军一职后,路冲更是变本加历,无视都元帅府,插手军中事务,朝廷发放给地方的粮响自然也被他扣了不少,杨邦宪虽是朝廷钦封的从二品大员,但毕竟是招安之人,又要仰仗朝廷下发粮响,对一些官员是敢怒不敢言。
征兵本就由都元帅府主持,如今宣慰府插上一脚,杨家军反而成了伙夫,驻军成了冲锋军,元人无视百姓死活,一律按照朝廷兵役入户抓人。按照朝廷兵役,每户二丁、三丁者一人,四丁、五丁者二人,六丁、七丁者三人。但凡充军之人,朝廷发放米五斗,盐一斤。
老百姓依靠男丁农作生存,这一服兵役,大多有去无回,谁也不愿意当兵,一时间播州城内人心惶惶,年轻力壮的男丁都躲了起来,甚至有人假死,以埋葬在老家为由逃走。
元军在南北城门设卡,男丁出城一律要百夫长文书,又在集镇及村子里大量征兵,并重赏那些举报逃兵之人,一可免服兵役,二可得十两银子。这样一来,大多数男丁都被抓捕到宣慰府临时设立的新军营,短短十天,就有千余之多。
路冲把五斗米和一斤盐扣了下来,以支援前方战事为由,把粮响屯积于地下仓库,再通过粮商盐商高价卖出,所得赃银,分为三份,一份交于路三平,一份分于元军各方将领,一份作为后备战资。这后血战资实际上就是路冲自己的银库,从未拨出过银子。
很快,路冲便组建了百人自卫军,并设立了监军营,但凡违反军令的汉军,都会被监军营问罪。路冲手握大权,又有自卫军和监军营,一时间权势熏天,大有与宣慰府和都元帅府成三足鼎立之势。
路三平忧心重重,朝廷几度下旨责问镇压叛军之事,都以援军较少为由搪塞过去,各方援兵将领也都怕与叛军交战,迟迟拿不出良策,杨邦宪更是袖手旁观,如今心腹路冲又趁机笼络人心,恐日后无法驾驭。这日议事后,路三平请宋真留下,谈论时下担忧。
“宋兄弟,眼下这时局,依你之见,那宋隆济能不能打来播州?”
“宋隆济之流,不过是些野蛮之人,凭着那种地的力气来打仗,哪能和圣上的铁骑相提并论,如今援兵也有三万之多,与梁王首尾相应,只需一鼓作气便拿下叛军。”
“你说得倒好听,援兵倒是有三万,可没有谁愿意去打仗,这帮援兵就没有一个主将,派来的全是副将,打不打,还得送一封文书去禀报,一去一来,半月之多,我看这仗还没打,粮食就不够了,那运粮的军队据说还要十来天,等这批粮食到了,这帮人又要等待装备,装备有了又要养马匹,我看这仗打不了。”
“大人所言及是,这帮援兵仗还没打,已经把咱们的军粮吃得差不多了,这朝廷的粮响迟迟不到,过不了几日,恐怕军队内部就会先乱,那宋隆济要打进来,咱们拿什么挡,现在又征兵千余人,一千多张嘴巴要吃饭,元军一日三餐倒是少不了,只是这汉军新军一日两餐都成问题,这样下去如何是好?”
“宋兄弟有何良策?”
“路大人,下官以为,应敦促援兵进军顺元,这仗越早打越好,这样拖下去,寒冬将至,行军打仗更是不利,播州本就不富足,现加重税赋,恐怕加深民怨,让那叛军有机可趁,把汉族人也拉进去,可就……”
“是啊,本官夜夜忧心,生怕这叛军攻打过来,咱们空有三万多人,却无力还手。”
“大人可让监军路冲与杨指挥使商议出兵之事,都元帅府要打仗,相信那帮援兵也不会不管。”
“好,我这就叫路冲去办。”
路冲前往都元帅府,被挡在门外,顿时发起火来:“你们不要命了,连本监军也敢拦?”
守卫说:“大人,您就别为难小的了,元帅府向来有规矩,就算路大人来了,也得提前通报,容小的先行通报,可否?”
路冲挥了挥手:“赶紧通报,就说本监军有事要和杨指挥使相商。”
不大一会,守卫出来,说:“监军大人,杨大人有令,今日不见客。”
路冲大怒,说:“什么,杨邦宪那匹夫竟然不见我?”
守卫不再说话。
路冲便大骂起来:“杨邦宪,你有什么了不起,你就是缩头乌龟一个,敢不让本监军进去,你不想活了……”
守卫正欲阻止,只见一支箭从门内射出,正中路冲帽顶,箭带着帽子飞了出去,钉在一棵槐树上。
路冲吓了一大跳,急忙摸摸脑袋,幸好还在,见府内走出一年轻小生,手里拿着一张弓,便破口大骂:“小子,你他娘的不想活了,知道本监军是谁吗,你他娘的敢射我。”
来人正是杨家军白面将军杨五,此人面如小生,实已四十有余,系杨邦宪左膀右臂。杨五冷笑一声,说:“什么狗屁监军,在此大吵大闹,不要命了?”
路冲说:“你是何人?”
杨五说:“亏你还是监军,连我也不识。”
路冲说:“你认得我?”
杨五说:“你不就是路三平的那条狗吗!”
路冲大怒,上前几步,一拳揍了过去,却发现自己的身体飘了起来,肚子上挨了一脚——他屁股着地,屁股与地摩擦了足足有一丈远,裤子破了两个口,皮开肉绽。他想骂,肚子疼得骂不出来,眼泪不由得流了出来,屁股又痛得像刀绞一样,不由得更加伤心。
杨五说:“就凭你一个小小的监军,也敢在元帅府撒野,骂我也罢,敢骂杨大人,你不想活了。”
路冲擦着泪水,捂着肚子,缓缓站起来,沮丧的说:“好汉……好汉……我这不是奉了路大人之命,来与杨指挥使有要事相商,不料你们这么不讲道理,俗话说君子动口不动手,你竟然打我,这回一定要请杨指挥使评评理。”
杨五说:“你再不滚,别怪我手下不留情。”
路冲不得不滚,之前跟着路三平到过元帅府,那杨邦宪却也没正眼看过任何人,如今看这势头也讨不了什么好,不如回去从长计议,报这一脚之仇。
看到路冲被抬回来,路三平又好笑又好气,笑的是路冲不识抬举,自认为是监军便为所欲为,气的是杨邦宪太不给面子,打狗还得看主人。
路冲哭着说:“大人,你可要为在下做主,好杨家也太目中无人了,明明知道在下是大人派去的人,不但不见我,还打我。”
路三平说:“惹谁不好,去惹白面虎。”
路冲说:“我在那门口,要见杨邦宪,不料他们不让我进去,还派了个年轻人来打我。”
路三平说:“你啊你,来播州也有些时日了,连白面虎也不知道,打你的那人,正是杨家军的副使杨五,人称白面虎,功夫了得,特别是那一张神弓,箭无虚发,在播州他要称第二,没人敢称第一。”
路冲一脸的委屈,抱怨几句,便退下治伤。路三平说得不假,杨家军之前在边陲之地极有声誉,部落战争当中,杨家军从未落败,杨五一张神弓可谓天下无敌,据说那张铁弓有足足五十斤,远可射箭,近可作替刀剑,威力无比。
宋真说:“这次路冲吃了苦头,想必会收敛些,不过这么一来,那杨邦宪显然是曹营心在汉,大人何不参他一本,请圣上撤去他指挥指之职,只要这杨邦宪一除,收复那蛮荒之地指日可待。”
路三平点了点头,说:“宋真兄弟所言极是,只不过这杨邦宪是朝廷招安之人,没有证据,恐怕难以拔掉这颗毒牙,如今平叛宋隆济,还得借刀杀人,把杨家军利用起来,让那土著人找杨邦宪报仇去,一但平叛不力,再上书朝廷治他的罪。”
宋真说:“大人高明,可眼下杨邦宪躲在元帅府不出兵,也不是个办法,何不把路监军招来的新兵充入杨家军,让杨邦宪带着这帮人去拼命。”
路三平说:“此计甚妙,甚妙,不过,想要杨邦宪出兵,还得加一剂重药,把这援军的指挥权交给他,私下再与各方将领们计谋好,表面服从,冲锋上阵让杨家军和那帮新兵让,这样也能减少我军的伤亡。”
二人计谋已定,便叫来各方援军将领,交待了下去,路三平又把路冲的自卫军百夫长王将叫来,赏了些银子,安排了自卫军与新兵营合编入杨家军的计划,让其伪装听从杨邦宪军令,做那军中探子,掌握杨邦宪和杨家军动向。
王将受宠若惊,拿着军令到新兵营撤营,把新兵和自卫军带到元帅府附近半里地扎营,听候杨邦宪差遣。
各种援助也开始严密整顿,一副要出征的架势。
杨邦宪和路三平同为从二品官员,但军机大事还得与路三平商议决定,如今又有各方援军支持路三平,那军改文书也盖着各方援兵将领的大印,就算杨邦宪不顺从,上书朝廷也得有些时日。杨邦宪深知元人心计,更知路三平等人的阴险,即使不同意,上书朝廷,也会被中途拦截下来,到时各方援兵将领再联名上奏,御加之罪,何患无辞。
都元帅府汇集援兵三万五千人,杨家军五百人,新兵一千人,准备即日与宋隆济在顺元决一死战。
十日前,路冲带着元军各地征兵,黄泥塘首当其冲。
朱武带着几名汉兵,在街道和村道上叫喊。
“各位父老乡亲,按照朝廷兵役,每户二丁、三丁者一人,四丁、五丁者二人,六丁、七丁者三人。但凡充军之人,朝廷发放米五斗,盐一斤……”
第一天,朱武便到了赵家沟,通知常顺服兵役。
“九叔,朝廷的兵役咱老百姓没法改,每年征兵打仗,咱们黄泥塘的年轻人都当兵了,要是不打仗多好,元人没来时,咱们这里多太平。”
“小武,叔和你商量商量,顺子已经订亲了,能不能通融通融,咱们交些银子,顺子就不用去当兵了。”
“这可不行,我的堂兄都当兵了,这一次是宣慰府征兵,是那元人要征兵,杨大人都说不上话,听说了吧,援兵已经来了有三万多,我看那宋隆济折腾不了几个时日了。”
“新兵也上战场吗?”
“九叔你就放心吧,顺子去当兵,我给上面说说,就当个火头兵,不用上战场。”
“可我怎么听说新兵都得去打仗,这让咱们自己人打自己人,多毒啊?”
“那姓宋的要不起什么义,这仗也没法打,九叔,可别让我为难,过几天就让顺子来找我,你放心,只要我朱武活着一天,绝不让顺子去打仗。”
“有你这句话,叔就放心了。”
常家父子原本想一走了之,不料又遇上征兵,黄泥塘大多数男丁已入了伍,少数逃跑的被抓了回来,砍了头挂在镇头的树上,一帮元兵在那看守,亲人下葬都无全尸。见此情形,常家父子只得从长计议。
两天后,常顺带着铁刀到征兵处,朱武与另一人正在言谈,见常顺带刀前来,便说:“顺子,你是火头军,不用带刀,再说了,你真要兵器,朝廷会给你的。”
常顺说:“朱哥,你就让我带着吧,这刀是我亲自打的,真要上战场也用得着,别人打的刀我用着不省心。”
领头的百夫长王将不耐烦的说:“行了行了,带着就带着吧,反正是去打仗,带了也好。”
朱武扯了一下王将的袖子,说:“王将兄弟,我这兄弟可是从小玩到大的,你得照顾着。”
王将瞄了一眼常顺,说:“放心吧,让他当火头军,朱哥交待的事,兄弟一定办到。”
朱武走到常顺跟前,说:“顺子,这位是王大人,今后你就在他麾下谋生计,来,给王大人磕头。”
常顺心道:“老子长这么大,都没给我爹磕头,要让我给这元狗磕头,门都没有,头可断血可流,我一刀结果了他,大不了一命抵一命。”
王将急忙制止,说:“朱哥,这点小事,你就别瞎折腾了,你是不是瞧不上咱王将?”
朱武说:“好,那这头就不磕了,王将兄弟,我这兄弟要是在军营里出了啥事,我可要找你麻烦。”
王将笑着说:“放心吧,只要我王将的脑袋还在,绝不让他打仗,再说了,他对路大人多少也有些功劳,路大人要知道了,还不得责怪我。”
常顺被安排在火头军中,与卢小七、黄老坤、贺飞等七人一起,为五百余人煮饭炒菜,常顺力大又勤快,便负责挑抬,黄老坤掌厨,卢小七年龄最小,做些下手活。
“饭煮熟,起锅喽!”
那两百斤重的木甑被常顺抬起。
“菜好了,端菜喽!”
一盆又一盆的菜被常顺抬走。
黄老坤吆喝着,给那些十五六岁的新兵做饭,他总感叹的说:“饭要做熟,菜要炒好,吃了不顿,说不定就没下顿了。”
没事做的时候,八个人便围着火聊天。
“顺子,你当个火头军还扛着把刀,是不是想去打仗?”
“不想打仗,就怕有一天被人打,带把刀防身。”
“你这把刀好,比元兵用的那些好多了,你得把刀放好了,莫被人偷了。”
“放心吧,我睡觉都抱着它睡。”
一天,王将带着路冲前来查看军情,走进了厨房,路冲见新兵吃得这么好,便对王将说:“还没打仗,就有鱼有肉,这可不行,从明天起,七天吃一次肉。”
黄老坤插上嘴,说:“大人,这些新兵都还是些孩子,这伙食要是跟不上,哪有力气打仗。”
路冲一愣,奸笑着说:“现在战事吃紧,哪有这么多肉吃,咱们这一千多号人,一天得吃多少头猪,你心好,那你去给我弄几头猪来。”
黄老坤说:“我上哪弄猪去。”
路冲脸一黑,说:“赶紧给我干活,不然就把你当猪一样的杀了,真没规矩。”
王将急忙解围,说:“路监军息怒,此人是掌厨,手艺不错,以前在酒楼里掌厨里,改天让他给您老做几道菜,算是赔罪。”
路冲不屑一顾,说:“这帮农民,得好生管教,王将,咱们当差的,一定要当好这个差,从今日起,七天吃一次肉,一天吃两餐,派人把这厨房重地看管起来,莫要被那些新兵偷吃了。”
王将说:“遵命。”
看着路冲远去的背景,黄老坤吐了一口痰,愤恨的说:“这元人的走狗,真他娘的恶心,龟孙子每天大鱼大肉,咱们一天也就五十斤肉,现在七天才五十斤肉,这饭怎么做,这菜怎么吃?”
常顺说:“老坤,别生气了,和狗犯不着生气,这年头能有口饭吃就不错了。”
黄老坤说:“我是替那些娃不值,这么年轻就被抓来当兵,一上战场,准没命,能多吃一口肉,那也是福分。”
正所谓:
号角未吹铁勺响,少儿命里战沙场;
谁知今夜随月走,何日再见爹和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