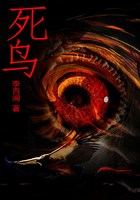铁匠铺的生意,突然淡了下来,偶尔有几个街坊会打几把菜刀锄头,大多数来铁匠铺的,都是打听路府消息的。
自从常家父子给路老太太打了金镯子后,街坊们都生疏了,几个百夫长却经常来混些酒喝。
没活干,常顺便到铺子上守着,看有无生意。
向大寡妇偶尔也会到铺子上转转,扭着那蛇一般的小蛮腰,背后总有几个长舌妇说闲话。
唯一热情不变的是铁牛,除了给王婆干活,便到铁匠铺帮忙。
这天,向大寡妇打扮了一番,正准备给常顺送点吃的,被婆婆拦住。
“你这丫头,怎不知羞耻,总是往常家铺子上跑,就不怕别人说闲话?”
“干娘,我又没做什么坏事,别人要乱嚼舌根我也没办法。”
“那你也不能总是往那地方跑。”
“那地方怎么了,难道去还犯法了?”
“常家父子什么人,那是和官府有勾结的人,咱们这种老百姓,踏实的过日子就行了,听干娘的话,别去。”
“干娘,你这些话是从哪听来的,常家平常也照顾咱们家不少,他们就是给那死去的老婆子打了个金镯子,怎么就成了勾结了,如果百夫长叫咱们家杀只鸡,咱们家能不杀吗,我就不明白了,这街坊邻里的,怎么都不记得别人的好。”
“我说不过你,干娘也是提醒你,别让人说闲话。”
“谁爱说说去,我一寡妇,怕谁说。”
“你——”
“干娘,你别生气,我走了,晚上要回来得晚,你帮忙喂下圈里的猪吧。”
向老太太气得说不出话来,只得眼睁睁的看着儿媳妇端着一碗鸡肉出门,她只恨自己的儿子太短命,要是还在,这水灵灵的媳妇也不会跑到常家。
常顺坐在铁匠铺的板凳上,一边啃着鸡腿,一边听向大寡妇抱怨着。
“顺子,你说这些街坊都怎么了,平时你给他们打了那么多的锄头都没有收半文钱,你们给路老夫人打了个金镯子,他们就眼红了,说常家和官府勾结,这都什么世道,以后啊,你别帮这些人,这些人就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好好好,听你的,对了大嫂,什么时候给我爹做只叫化***我给你银子。”
“什么大嫂,说了多少次了,叫我平儿。”
“这个,我叫不出口。”
“你叫不出口,那你就别吃咱的东西,让铁牛一个人吃。”
铁牛嘿嘿一笑,说:“顺子哥,你不叫我叫,平儿,平儿。”
向大寡妇一巴掌打在铁牛脑袋上,说:“你跟着瞎闹什么,平儿是你叫的吗,这辈子就我爹娘和顺子可以叫。”
黑牛拿着鸡头,边吃边走开,嘴里一股不服气的味道:“凭什么只让顺子哥叫,说好的,顺哥不叫就把鸡给我吃,说话不算话。”
常顺看着铁牛,无心再吃鸡肉,喝了口酒,把盘子端到铁牛面前,说:“铁牛,哥给你吃,吃了赶紧回家。”
铁牛顿时开心起来,接过鸡肉,笑嘻嘻的说:“还是顺子哥对铁牛好。”
向大寡妇扬了扬手,说:“死没良心的,什么都是顺子哥好,你忘记那鸡是谁的了。”
铁牛憨笑着说:“平儿也好。”
向大寡妇的脸顿时红了起来,指着铁牛说:“你再叫我平儿,以后就没你的份。”
铁牛端着鸡肉便跑了。
铺子里剩下常顺和向大寡妇,一时间尴尬了起来,常顺喝着闷酒,向大寡妇靠在门上。过了一会,向大寡妇终憋不住。
“顺子,你娶不娶我?”
“啊!”
“啊什么啊,你是不是嫌弃我嫁过人?”
“没有。”
“你明明就有。”
“我真没有。”
“那你娶我,我是嫁过向大,但人家也还是黄花闺女,嫁过来前向大就生了病,大家都知道。”
“我真没嫌弃你,就是我爹不同意。”
“你爹他凭什么不同意?”
“他说你比我大。”
“我比你大怎么了,我可以做饭,洗衣服,养几头牛和猪,把你爷俩伺候得好好的。”
“我爹他——”
“是你娶我还是你爹娶我?”
“要不我再和我爹商量商量。”
“行,咱俩也不能这么下去了,街坊们都说闲话了,再这么下去,你不给我个名分,让我怎么活。”
“我和我爹商量商量。”
“你是男人,得负责任,我一个女人,可不要欺负我,你爹凭什么不答应,我做了那么多叫化鸡给他吃,难道都喂狗了?”
“话也不能这么说,我爹又不是狗。”
“他瞧不起我,就是狗。”
“你骂我爹。”
“他不同意,我就要骂他,我还要当着他骂。”
“你不能这样,爹常对我说,做人要讲道理,你这样不讲理,谁敢娶你。”
“你娶了我,我就什么都听你的。”
“我和我爹商量商量。”
二人的对话,被路过的王婆听得一清二楚,王婆是个热心人,会心一笑,便到去找向婆婆。
“我说大姐,忙什么呢?”
“哟,是王弟妹来了,快请进屋坐。”
“段平那丫头不在啊?”
“不在,不知道去哪了。”
“是不是去铁匠铺了?”
“你看见她了,这死丫头,吃着咱们向家的饭,却往常家跑,这都叫什么事,都怪我那短命的儿子,唉。”
“大姐,话可别这么说,咱们都知道段平这丫头能干,可她毕竟才二十一岁,人又长得水灵,你真舍得她守活寡?”
“可不是,我这当婆婆的,也不好作这个主,我看出来了,那丫头早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她喜欢顺子,我人老心可不瞎,那常家可不喜欢她。”
“你是说常老九不想做这门亲戚。”
“可不是,这孩子们的事,大人做主,他也没上门来提,咱们不可能拿着热脸倒贴这冷屁股吧!”
“这么说来,大姐是同意这门婚事了?”
“不同意有什么办法,段平这丫头本来就是我的表侄女,只是我向家没福气,我也想通了,不能耽误她,只希望她能找个好人家。”
“老九这人平常对街坊们都不错,咱这铁牛,一半是他的一半是我的,我见这顺子和段平你情我愿,也想做这个媒,只要你同意,这件事就好办。”
王婆从向家出来,回到家里与儿媳万春香谈起向常两家的事,万春香也是一百个支持,吃过晚饭,王婆带着铁牛到了石屋,正遇上常九手在茅草屋收拾东西,便与他提起孩子们的事。
“老九,顺子也不小了,总不能每天晃来晃去,给他找个媳妇吧,瞧你爷俩这日子过得,没个女人怎么行。”
“今个吹的是什么风,王婆你怎么提起这事?”
“你这个爹是怎么当的,一天只知道打铁打铁,我问你,顺子今年多大了?”
“好像十六吧!”
“唉,你们男人,有时候真不如女人,顺子马上就十八了,你不是说他是冬月生吗?”
“冬月,对,就是冬月,一晃就十八了,真快,我们来黄泥塘时,他才两岁多。”
“那你是咋想的?”
“顺子的婚事啊,我是这样想的,这几天也没活干,正准备带顺子去趟思州,看看他表妹秋兰,那丫头十六了。”
“听说了,顺子不喜欢那丫头,说长得又胖又难看。”
“这小子,怎么说话的,再难看,那也是亲戚,咱们这样子,谁能看得上。”
“恐怕是你看不上别人家的姑娘吧?”
“王婆,你这话中有话,有话你就直说,我这人性子直,要是平常有什么对不起街坊的事,还请王婆多说好话。”
“得了吧老九,你到宣慰府一趟,这人就变了,是不是赚了些银子,就把咱们黄泥塘的街坊给忘记了?”
“哪里赚什么银子,咱使的都是力气活,我知道街坊们瞧不起我,说我巴结官府,拿老百姓的血汗钱,我常九手可以对天发誓,从来没有干过伤天害理之事,也没有替官府杀人越货,我赚的每一文钱,都是干干净净的。”
“瞧睢你,说你几句还没完了,我辈分比你大,有些话你还得听我的,谁叫铁牛是咱孙子,咱们还是亲戚呢,按辈分你还得叫我一声姑姑,这么说吧,段平那丫头也不错,顺子也喜欢她,向家也同意,你看——”
“不行。”
“咋不行了?”
“她是寡妇,克夫。”
“你不知道向大怎么死的?”
“知道,我还去抬了棺材。”
“那你还说段平克夫?”
“寡妇就是不吉利。”
“你眼睛没瞎吧?”
“好着嘞。”
“这么水灵的丫头,你们常家不要,后面排着长队呢!”
“……”
常九手拒绝了王婆,怕生出是非,便关了铁匠铺的门,带着常顺前往思州,去找妹妹一家。
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常顺只得跟着父亲走,他心想:“到了姑姑家里,跟表妹说清楚,自己已经有了意中人,相信表妹能理解,到时候父亲便再无话说。”
播州通往思州的官道,偶尔会有几匹快马奔驰而过,百姓却很少,每到一个镇子,由百夫长带着元兵设卡,遇上土著人必定严查,汉人和蒙古人则可以通行。
常家父子骑着刚买的马,慢悠悠地在官道上行走数日,便到了思州城,只见城门处守卫深严,元兵对进出城的人员严加盘查,搜出的银两则被强行抢走,妇女则被元兵摸来摸去。
见此情形,常顺义愤填膺,咬牙切齿的说:“这帮元兵,从北方那么远的地方而来,如此嚣张,光天华日之下侮辱良家妇女,抢人钱财,和盗匪有什么区别,真不知这世道怎么了,没有了王法,没有了正义。”
常九手说:“正义个屁,赶紧想办法把咱们的银子藏起来,不然被那狗日的搜了去,咱爷俩就得饿肚子。”
常顺狠狠的说:“要敢抢咱们的银子,咱就和他们拼命。”说着便动手去拿马鞍上的杀猪刀。
常九手说:“你这小子,不要命了,和元兵斗,就等于是自杀,你莫牵累爹,你要这样,赶紧给我自杀了,省得爹提心吊胆。”
常顺笑了笑说:“放心吧爹,我也只是说说。”
二人说着边到了城门口,一名百夫长挡住去路。
“下马下马,赶紧给我下马。”
父子二人下了马。
“干什么的?”
“走亲戚。”
“从哪里来?”
“黄泥塘。”
“老子问你从哪里来,你说从黄泥塘,咱不从河里来?”
“军爷,咱们真是从黄泥塘来,就是播州城外的黄泥塘。”
“妈的,早说播州不就得了,这么哆嗦,说,走什么亲戚。”
“来看我妹妹,城东巷李老毛,那是我妹夫。”
“什么毛不毛的,老子不认识,包袱拿过来检查,有没有带银子。”
“军爷,小的是打铁的,哪来银子,就带了几把菜刀和杀猪刀送给妹夫。”
百夫长黑着脸,走到马前看了看,用手按了按包袱,从马鞍上拿了一把杀猪刀,说:“妈的,打铁的,老子看你不像打铁的,倒像杀害东顺号伙计的凶手,来人,给我抓起来。”
十余名元兵顿时拔刀围了过来。
“住手——”
一名俊俏的公子,边上跟着两名奇形护卫,后面十几辆马车拉着棺材。
百夫长正想骂人,见到公子,立即行了一礼,说:“原来是莫少东家。”
莫少离冷冷的说:“放了这两人。”
百夫长油嘴骨舌的说:“莫少东家,这可不行,宣慰使大人已下了令,但凡进出人等必须严查,东顺号的案子还未结,杀人凶手逍遥法外,这二人藏有兵器,说不定就是杀人凶手。”
莫少离说:“刚我听见了,此人乃播州外黄泥塘的铁匠,你怎么说他是凶手?”
百夫长说:“难道莫少东家认识这二人?”
莫少离看了看常家父子,说:“听说宣慰使路大人请黄泥塘的铁匠常九手打了两只金镯子,难道这两位就是——”
常九手立即明白过来,抱拳行礼,说:“莫少东家,在下正是常九手,这是小儿常顺。”
莫少离还了礼,说:“常师傅在播州可是名人,来这思州,知道要遇上麻烦,怎么不让路大人给道公文?”
百夫长态度马上转了一百八十度的弯,对常家父子说:“原来二位是路大人的朋友,又认得莫少东家,真是误会误会,常师傅何止在播州有名气,在思州也是大名鼎鼎,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今日多有得罪,改日我定在思州酒楼摆上几桌,兄弟们给常师傅陪个不是。”
常九手皮笑肉不笑,说:“不敢不敢。”
另一边,莫少离已下了马,走到常顺面前,见他手放马鞍上,眼神带着杀气,便说:“你们真是黄泥塘常家?”
常顺说:“如假包换。”
莫少离说:“你想杀人?”
常顺说:“杀该杀之人。”
莫少离说:“什么人该杀?”
常顺说:“欺男霸女胡作非为之人。”
莫少离说:“好骨气,不愧是常九手的儿子,只可惜——”
常顺说:“可惜什么?”
莫少离说:“你有杀人的肚量,没杀人的力气,如今这世道,欺男霸女之人何止元兵,何止官府,这么多人,你杀得完吗?”
常顺说:“杀一个少一个。”
莫少离说:“你真固执,不过我喜欢,在下莫少离,你是?”
常顺说:“常顺,大家都叫我顺子。”
莫少离说:“今日之事,你父子欠我一个人情,改日我来黄泥塘,还请帮我打把刀。”
常顺说:“好说好说。”
莫少离说:“以后有什么事,尽可到播州找我。”
常顺说:“怎么找?”
莫少离从杯里掏出一块红木,上面雕刻着“莫”字,递给常顺,说:“你只要拿着这东西,到莫府找莫少离便可。”
常顺接了过来,说:“行,你今日出手相助,来日定当还情。”
莫少离说:“好,一言为定。”
莫少离上了马,百夫长立即前来相送,浩荡的棺材车队,行人不由得躲避开来。
天鬼不屑一顾的说:“少东家真是广交朋友,这等铁匠也这般客气。”
莫少离说:“师兄是在笑话我?”
天鬼说:“我不是笑话你,只是觉得这两个人也就普通百姓。”
莫少离说:“他们才不是普通百姓,师兄难道没有听说,路三平的二管家亲自到黄泥塘找常九手打两只金镯子,而路老太太在八十大寿当晚失踪,二管家也失踪,这事你不觉得蹊跷?”
天鬼说:“少东家认为此事与打铁的有关?”
莫少离说:“我有一种感觉,那小子是个干大事的人。”
天鬼说:“一个打铁的,能干什么大事。”
莫少离说:“师兄,俗话说海水不可斗量,你别小看这个打铁的,他目露杀意,咱们来早了点,晚了便可看上一场好戏,说不定那百夫长的人头,早已落地了。”
天鬼说:“这个我倒没看出来,这二人除了精神有力气,看不出有武功。”
莫少离说:“他们没武功,但那小子的力气,估计你比不过。”
天鬼说:“听你这么一说,有机会我倒要和他比比。”
莫少离笑了笑,眼神略带悲伤,继续赶路。
常家父子进了城,找到城东的李家酒楼。
常顺进了酒楼,便看到了表妹秋兰。
只见柜台前坐着一姑娘,盘子脸,小眼睛,一字眉,两个小辫子冲天而起,一身蓝色长袍。
常顺嘿嘿一笑,心生喜悦,指着姑娘说:“爹,想必那就是秋兰表妹,前几年见她的时候,还没这么胖吧,你看,她那头发,如只扎一小绺,还真像蒙古人。”
常九手见四下无人,一巴掌拍在儿子脑袋上,说:“怎么说话呢。”
秋兰见有客人来,便站了起来,扭着水桶腰走到柜台前,眯着眼睛笑起来,说:“两位客官,想吃什么菜?”
常九手摇了一下头,看看得意的儿子,说:“秋兰,你怎么把舅舅都忘记了?”
秋兰一怔,立即走到跟前,从头到脚仔细打量常家父子,随后双手拍了起来,说:“哎呀,真的是舅舅,真的是舅舅,娘,舅舅和顺子哥来了。”她欢喜着朝后堂跑着。
常顺紧张的说:“她怎么认得我。”
常九手说:“谁知道呢,连舅舅都不认识,长大后她只见过你一面,记得这么清楚,真有心。”
常顺说:“爹,你也看到了,反正这事我不同意。”
常九手说:“行了,爹知道了。”
常二姑和李姑爷从后厨跑了出来,多年不见,兄妹之间有说不完的话,常二姑半了店门,做了好菜,一家人喝起酒来。
酒是上等的米酒,乱世之中,亲情更显珍贵,一顿饭吃了一个时辰,李姑爷带着两孩子去睡觉,剩下兄妹二人对烛交谈。
“大哥,你老了,都有白头发了。”
“可不是,快六十了,岁月不饶人啊,你也沧桑了许多,过得还好吧,姑爷对你怎么样?”
“他啊,老实人,平常都是我当家,想当年咱们逃到思州,你得罪了恶霸,跑到播州,与我们分离,刚听顺子说起,你们在那边打铁,生意冷清,要不就来思州吧,我把后院腾出来给你们打铁。”
“算了,兵荒马乱的,再说我得罪了那恶霸,再来思州,也是给你添麻烦,我走之后,他没找你麻烦吧?”
“没有,老李花了点银子送了点礼,说你回老家了,这事也算是了了。”
“这事多亏了姑爷。”
“一家人还说两家话,对了,你们这次来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没,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想你们了,带顺子来看看,顺子一直吵着要来看你和秋兰。”
“一晃,顺子都长这么大了,也该成家了,黄泥塘有没有好人家,请人给他说个媒吧,要是没钱,在我这先拿些银子。”
“有有有,这些年咱们打铁也存了些银子,成个家够了,顺子这孩子不听话,看上了个寡妇。”
“有这样的事?”
“可不是,要说这寡妇,也不完全是寡妇。”
“大哥,你这话把我说得云里雾里的,你快给我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
只道是:
年少不知世险恶,喜遇知音后话说;
良缘自古天注定,坎坷命运不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