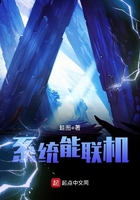小时候,我随外婆住在老家的一个小镇子上,那时我只有十岁左右的年纪,人读镇上的小学四年级。父母在外工作,顾不上我,我的童年是调皮而贪玩的,不怎么好好学习,常常拿着家里的馍馍送给高年级的大孩子带我到山梁上捉黄鼠玩,或者在种有洋姜的地里挖地溜子吃。我那时年龄虽小,却记住了一个人,他就是住在镇子北头果园里的一个驼背老人。他也许是镇子上最不起眼的人,但镇子上的人甚至邻近乡村的村民都知道他。因为他是一‘个天生的佝偻病患者,背上长年累月仿佛都背着一口沉重的锅,压得他直不起腰来,走起路来像爬行一样向前挪动,人们都叫他“背罗锅”。他的头很大,常常戴一顶黑色瓜皮帽,脸部布满皱纹,几根稀疏的焦黄胡须随意地长在他的上唇和下巴上,他的身体上半部隆起像半个圆球,两条腿很短。由于长相丑陋,小孩子家见了他都不敢靠近,只有远远地喊他“背罗锅”“背罗锅”。他却并不生气,或许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称呼。很少有人和他搭话,他也总是避开往人多的地方去凑热闹。不过,他有一手绝活,能够使他在众人面前“露脸”,那就是打干鼓。那时候镇子上经常演样板戏,从演员到乐队都是由有特长的公社社员来担当,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当然要比下地劳动轻省,工分也记得高,大家都乐意干。演戏就得有乐器伴奏,文戏有板胡、二胡、笛、唢呐、大号等;武场有干鼓、堂鼓、小锣、铙钹、铰子等。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杜鹃山》等多是武戏,没有干鼓不行。找来找去没人能敲得了,只好“屈尊”到他的头上。这些都是后来听老人们说的。但我确实看过他在舞台上的“演出”。干鼓大小如一只小盆,牛皮绷面,用一双略比筷子粗的木捶敲击,声音尖高,清脆悦耳。在七十年代初的西北农村,乐器是十分奇缺的,干鼓就成了伴奏唱腔的主要家当。“背罗锅”在演奏时手腕弓起,双手握捶高举至头顶,上下挥舞,动作敏捷,似乎全臂之力都集于棰尖,全身之力都惯于鼓面,雨点般的敲打使鼓铮挣鸣响,随着剧情波荡起伏,节奏感很强。这个时候,甭说看戏,专看他的神情,他的皱巴巴的脸上每个沟纹仿佛都流淌着兴奋。
记得有一年秋天,正是果子成熟的时候,我和几个小伙伴去他住的果园里偷果子吃,等我们几个翻过矮墙刚刚攀到树枝上时,被他发觉了,我们知道他跑不动,嘴里还喊着“背罗锅”欺负他。没想到,他从屋子后面牵出一条大黄狗,狗一叫,可把我们吓坏了,我们几个拔腿就跑。由于惊慌,我从矮墙上跳下来时崴了右脚脖子,疼得直叫唤,想跑也跑不动了。心想,这下让他抓住非挨一顿狠揍不可,经常喊他“背罗锅”不算,偷摘果子自己还送上门来。越想越急越怕,一时的疼痛也顾不上了,爬起来一瘸一拐地就往前走,没走几步,只听身后“岐”的一声,矮墙的门开了,他走了出来。看来我只有束手就擒了,索性倒在地上装“死狗”,看他能把我怎么样。只见他慢慢走过来,沙哑着嗓子说:“把哪里绊着了?”畏惧的我没敢搭话。他看见我的手放在右脚脖子上,又缓缓地说道:“把脚脖子崴了吧?碎娃娃家,不要伤了骨头。”我惊悚未定,还是没敢言喘,只准备着挨揍。这回他真的生气了,嗓音也高了起来你是不是把脚崴了?”我恐慌中尽量避开他浑浊的目光,却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这次他竟然笑了,我紧绷的心也随着松弛了一下,看来他并没有什么恶意。紧接着他吃力地蹲了下来,拿过我受伤的右脚轻轻地揉搓了一阵,又让我站起来试着走走,我只好顺从地试着走了几步,还是感觉很疼。这时的我完全像一个木偶由着他支配。随后他不由分说就架着我来到园子里的屋子。这屋子很矮小,烟把整个屋子熏得黑黑的,炕上堆着破旧的棉絮,炕台上是一盏煤油灯和一个旱烟锅子,连着炕台的是锅灶,锅灶边上的墙上钉着一个长长的木板,上面放着几个装盐醋的罐头瓶瓶和一个洋瓷碗、几只筷子,屋里没有几件像样的东西。我只觉得,呆在这屋子里用不上半天就会把人憋死。我面朝屋门坐在小木凳上,很不自在,但又没办法。他在一个很小的泥炉子上煎了半碗草药,等药温下来,他就用粗糙的手蘸着药水涂抹我的右脚脖子,他好像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不停地自言自语,显得很高兴,我却有些抖抖索索,任由他摆布。过了一会儿他出去摘了一些果子让我吃,我还是紧张,只听他说娃娃,不要害怕,吃吧。”。我吃了一个果子,润了一下因恐惧而干结的喉咙,渐渐也不再拘束,孩子的本性就露了出来,话也多了,这样我就和他拉了很多“家常”。快到吃晚饭的时候,我提出要回去,他却显得烦躁不安,脸色也变得更难看了,低声说道:“你会再来陪我一起说话吗?我会摘果子给你吃,给你讲很多故事的。”我怕他不相信,就使劲点了点头。他把我送到大路上,我走了老远,回头看见他还在向我摇着手里的旱烟袋。
后来我经常去他那里,有时一个人去,有时带小伙伴们去,他住的果园成了我们游戏的乐园。以前很少见他说话,自从和我在一起时,他的话就多了3他知道的真多,天南海北,古往今来的都有。他说兰州、甘州,在我幼小的心目中这都是些陌生又遥远的大城市,但我牢牢地记住了这些地名;他讲“毛野人”“瓜女婿”的故经,虽说离奇古怪,却浸润了年幼的心灵,不能不说是我最初文学记忆的启蒙,终使我一生受益。他一定走过很多地方,见识过很多事情,但也遭受过很多苦难’人们对他是看不起的,是鄙夷的,他是多么地自卑。我幼年是单纯的,感受不到他的痛楚,我成长的快乐只能稍稍减轻一下他的孤寂,其他什么也做不了,但我当时并不懂得。他心地善良,为人慈祥,从不因为我小而有丝毫怠慢,他是把我当作一个成年人来对待的。我们和睦相处了一年多时间,他就像小孩子一样快活,脸上常常挂着笑容,有时他还和小伙伴们捉迷藏、扔沙包,显得无忧无虑。他的背驼了,心没有驼,他是一个有喜怒哀乐的人,他也害怕孤独。
时间真快,转眼我就要上中学了,父母把我从小镇上接走的那天我去向他告别,可四处都找不见他,我急得差点要哭了,但在父母的一再催促下我还是走了。临上车前外婆说:“他可能是不愿意看见你走,躲起来了。”我心里怅怅的,纠结了好一阵子。换了一个新的地方,又有了新伙伴,很快就把这事给忘记了。随后外婆一家也搬离了小镇,我再也没有回过给了我童年许多快乐的那个地方,尽管那里还有许许多多让我难以忘怀的人和事,但一切都变成了记忆。一晃很多年过去了,我也步人了中年,回忆往事的时候总有他的影子在闪动,抹也抹不去。从老家临走的时候没能见上他一面,我常感到歉疚,我当时虽然理解不了他内心的孤寂,但我们也算无话不说的忘年朋友。时间愈久,我的一些念想就愈真切,但愿我的歉疚能化成真诚的告慰,告慰无论是地上或是地下的他那颗善良而孤独的心。
改自1985年5月旧稿
老盼是一个绰号,是我四十多年前一个发小的绰号,那时候我们只有九、十岁左右的年纪,很小,所谓“老”字,只是成人们给他起绰号时用的一个词头。四十多年前我和老盼共同生活在宁夏南部山区的一个小镇上,他比我大一岁,年纪相仿,经常在一起玩耍,是好伙伴,不论是干好事或是什么“坏事”,大人们都认为是我俩干的,想分也分不清。四十多年一晃就过去了,我们也已年过半百,两鬓飞霜,儿女成人,想想以前的事情虽觉好笑,但也充满着童年的乐趣。件件往事,历历在目,不能忘却,有时竟成为谈资,说给子女、朋友们听,博得快乐。说明我们已经老了,至少将步人中年与老年的交界了,细一想真能惊出一身冷汗,扪心自问:昨天我不是正年轻吗?怎么今天就老了,真快!其实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四十多年后我和老盼还在来往。
我十一岁时就随着母亲工作的调动离开了地处县城北川里的这座小镇,到县城东面的东山里的另一个镇子上去了,北川里的小镇与东山里的小镇之间相隔近100千米,这是一段很远的距离,加上当时的交通条件,说起来就更遥远了。虽说我们“天各—方”,但上了中学,慢慢懂得友情的重要了,又用通信这种方式联系上了。老盼精瘦、聪明,学习冒尖,高中时就被选拔到县城重点中学去了,后来考上了南方的一所大学。我则高中毕业后上了师训班,之后当了一名乡村中学的老师。我们尽管没有机会相见,但消息都知道。他上大学四年和我通了四年的信,说些往事、说些学习的情况,说些所谓理想方面的追求,互相勉励,精神支持一下,真是难能可贵,他给我的信件,我扎成捆至今还存放在家里的书橱中,几十年间,无数次搬家,都不忍舍弃。他大学毕业分配到了首府城市,这中间成家立业,忙于工作,我们就断了通信。记得有一年春节他回老家,大概是一九八三年吧,我在县城碰到了他,说了很多话,临别他拿出一只钢笔送给我做留念,让我感动了许久。后来我到首府学习,他来看过我几次,好像还有一次在我住的宿舍喝了点他拿来的葡萄酒。再后来各忙各的事,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但彼此之间的情况通过熟人都基本知道。不知谁说过,朋友就是不见面也经常能记起来的那些人,我们的情形大致就是这样。2010年初夏,我调来首府工作,他听说后即从他长兄处要来我的手机号码,一个电话过来,也不客套,请我吃饭。多年不见,一见如故,依然谈笑风生,没有丝毫的陌生和隔阂,他仍旧精明强干,智慧幽默,工作干得风生水起,事业有成。只是时间把我们曾经稚嫩的脸、单纯的心改变的老道、城府了,别无什么变化,真诚依旧,乡音依旧。
在我的记忆中,我与老盼有两件事值得一叙,其中一件就与他的绰号有关。
我家当时住在镇子上的供销社里,院子很大、很深,后院有一块空地,与前面的一排房子隔开,我们经常来这里玩。空地的下面是一个地道,是反帝防修的产物,地道口是斜着挖下去的,里面黑乎乎的,看不见什么。地道口的正上方是一个庞大的麦草垛,可能是供销社收的马料,当时到县城调货用的都是马车。空地其实不空,有时也种玉米或洋芋,在地的边角靠墙处生长着一丛很大的洋姜。有一年夏天,我和老盼就在这里挖洋姜和地溜子吃,不知谁提议,洋姜和地溜子烧熟了可能更好吃,于是我跑到前院家里拿了一盒火柴,又到地道口抱了一抱麦草,老盼拿着刚挖出的洋姜和地溜子说在外面烧大人看见了骂呢,拿到地道里烧大人看不见。于是我俩就来到地道里把洋姜和地溜子埋在麦草里点着了火,心里正想着吃烧熟了的洋姜和地溜子的滋味有什么不同,没想到一瞬间烟火弥漫了整个地道,熏的我俩眼泪直流,什么都顾不上了,只有“抱头鼠窜”出地道。回头一看,但见地道口浓烟滚滚,直冲地面而上。这时只听得有人喊道麦草垛着火了,快救火!”不大时间,供销社主任便领着一群职工拿着各种家当来救火,主任一看见我呆呆地看着地道口擦眼泪,就明白了几分。问道:是不是你两个把麦草垛点着了?我俩吓得不言喘。主任把老盼打了一巴掌,我们只好承认是在地道里烧洋姜和地溜子。主任一看麦草垛没着火,就把我俩赶到地道口让下去灭火。我俩边哭边捂着眼睛,摸到地道里用湿土盖到麦草上压住了火,然后战战兢兢出了地道,心想这下可能犯了大罪,不知要受到什么惩罚。幸好主任只把我俩训了一顿,让我们以后不要再来这里玩耍,就放我们回家了。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放火”也算是―场童年大的“游戏”,幸亏没闯出祸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