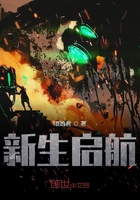整整一个下午,娃她舅也确实把力出了,干干一条毛巾,擦了一下午脸,能扭出水来。本该是一天的活,两个人一下午就拾掇得利利索索,感激得“老好”说:“哥哎,人常说,亲故亲顾,有人亲戚到底好,要不是你帮忙,这点活,我明日还得再干一天!”
晚上,“老好”告诉红裤子:“咱哥下午把力出扎了,确确实实乏了(困倦),晚上就让咱哥跟我到打麦场上去睡吧。那儿凉爽,疲倦了的人能歇好……”
红裤子眼睛一愣,说:“越说你越‘老好’了!咱哥是个客,到咱任家村来,人生地不熟,怎能让他和那些不熟识的人睡在一块呢……要睡,还是你去睡,让咱哥就睡在咱屋里吧。”
“可是……”老好为难了,“咱屋太小,太窄狭,况且,只有一盘土炕……”
“那怕啥?和我、和娃睡在一个炕上不对了,我们是一个娘奶头上吊下来的亲兄妹,怕啥?”
“那行,行。我倒忘了这一点!你看我这脑子,咳,真笨!”“老好”说着,肩上搭了一条被子向打麦场走去。
天气太热,打麦场上除了老人和女人,全是中年人和小伙子,有些人把精屁股的碎娃也领到场上来睡,一页芦席挨一页芦席,黑压压地睡满了一场。
当人们看到“老好”一个人来打麦场上睡觉,就有点诧异,随后,互相趴在对方的耳朵上窃窃地咬起来了。
不一会儿,二癞子光着脚片子走回家去了。
二癞子在半年前娶了南巷子一个寡妇,叫线旦儿,是妇女伙里一个热闹脚色,专爱打听人家两口睡觉的事儿。这阵儿听男人趴在她耳朵上嘀咕了半晌,脖子一蹴,眼睛一瞪,训斥男人:“胡说个屁!你胡说个屁!人家是亲兄妹,你犯啥神经?快睡觉去……”
二癞子被线旦儿熊了两句,吐了一下舌头,又光着脚片子踅到打麦场里去了。
二癞子一走,线旦儿抿嘴一笑,在心里说:“看个究竟去!”
换了一双软底胶鞋,线旦儿锁了前门,蹑手蹑脚地来到村东头。过了青石桥,顺着小溪边的大路,直直地朝独庄子走去。
天上虽然没有月亮,但星星却密密麻麻地撒满了天空。
独庄子三家住户,都没有后院墙,线旦儿畅通无阴地来到红裤子的窗子底下。窗子下边就是土炕。她先趴在窗台上听了一阵,不见炕上有任何动静,刚说要离开,却听见土炕上传来轻轻的嘤嘤的哭声。分明是红裤子的声音,线旦儿又凑了过去,并且把耳朵慢慢地贴在了窗户外面的墙壁上。
“……我想你,想的很呀……”红裤子的声音。
“我也想你,想得我好心慌……”一个男人的声音。
“白天不要说起,每天夜晚,想起咱两个在一块那阵儿,我的下身就痒得不行……”又是红裤子的声音。
“玲玲她爸不是在你身边睡着吗?”
“那是个笨熊,不会弄这事……”
……听不到声音了。
线旦儿心里一喜,就轻轻地抬起脚步,离开窗子底下,蹑手蹑脚地窜进了北巷子。
绒线嫂和线旦儿是很要好的朋友。线旦儿轻轻地敲开了她的门,把她从炕上赤条条地拉下来,并且趴在她的耳朵上说了一阵悄悄话。绒线嫂一喜,登了一条短裤,吊着两只大奶子,相跟着出了北巷。
线旦儿拉着绒线嫂的手,刚站到窗子底下,就听见土炕上传来红裤子“哼哼唧唧”的呻吟声,而且长一声短一声地呻吟个不停。
哼哼唧唧和呻呻吟吟的声音之外,还夹杂着男人“吭哧吭哧”的喘息声,这种喘息声又粗又野。线旦儿想起了二癞子和她干那事的时候,也是这种样法,想着想着,裤档里就有一股湿溜溜的东西顺着大腿流下来。她不由自主地在绒线嫂的交档里抓了一把。
绒线嫂正说要反抗,屋内的电灯“咯登”一下拉亮了,吓得线旦儿“倏”地一下离开窗台,跑到了小溪边,瘫坐在那里。
绒线嫂笑着赶到线旦儿跟前说:“正听到紧火处,你跑啥哩?”
线旦儿心里“嘣嘣”地跳着,说:“屋子里灯亮了,我怕红裤子看见咱俩……”
“你才是个瓜熊!晚上,屋子里越亮,外边就越黑,她把灯拉亮了,咱立在黑处,他们才看不见哩!”
“是不是?你看我这笨蛋!”
于是,两人又来到窗下。
土炕上继续传来踢里倒腾的响声。
“线旦儿一听急了,就想把糊窗子的纸扯破看看。绒线嫂把她的手挡了一下,就伸出舌尖,用口水慢慢地舔破了窗户纸。这种动作娴熟的程度,足以证明绒线嫂是‘听墙根’的老手。”
窗户纸被舔开了核桃大一个小窟窿,绒线嫂把一只眼瞪在了小窟窿上。
土炕上的事,全看到了……
周身颜色有点发黑的男子趴在女人的身上,女人的身上明显地发白,而且白得像一团棉花。两条又白又胖的大腿还勾住了男子的臂部,缠得很紧很紧;一双像莲藕般的臂膀紧紧地搂住男子宽阔的背脊,一双纤纤细手在背部不停地摩挲着;一头蓬乱的乌发撒在炕席上,眼睛挤得严严的,一张小口不停地在男子肩头咬着。忽然,女的把男子掀翻了,“啊”地一声又扑到男子身上……
听到土炕上的响声,线旦儿迫不及待地,把绒线嫂一拉,要她让开窗户上那个小窟窿。
线旦儿刚把一只眼睛凑到小洞上,身子就像扭麻花一样瘫坐在了窗子底下。
好在屋子里边的响声大,窗子外边的响声小,窗子外面发生的一切,红裤子根本不知道。
绒线嫂弯腰把线旦儿拦腰一抱,抱离了窗户底下……
2
虽然是夏收的大忙天,线旦儿和绒线嫂仍然没有下田割麦,她俩像负着什么使命一样,走东家串西家,不到半天功夫,昨天晚上窗户窟窿里边发生的事情,全村的女人们都知道了。
有人在巷子里挡住了二癞子,很神秘地问:“是你和你媳妇亲眼看见的吗?那两个狗男女耍的美不美啊?”
二癞子眼一瞪,在地上吐一口,说:“没有的事,少胡说!我昨晚在打麦场睡了一整夜,谁不知道!不信你问问‘老好’本人去,他跟我睡在一张芦席上;我媳妇昨晚熬娘家去了,不信你问问她娘家妈……”临走开时,又教训那人一句:“这号事,坚决不能乱说!人命关天的事喀……”
二癞子说罢,又钻进南巷子狗剩家,狗剩正在吃早饭。他和狗剩是自小钻大的一对光棍,两人好得像一母同胞。
昨晚她媳妇见到的新闻,他毫不保留地加盐加醋地灌进了狗剩的耳朵。
如今的狗剩仍是个光棍,听着二癞子这些十分刺激的话语,裤裆里不觉一阵臊热,立时坐不稳了,两条麻杆腿不住地扭动。然后,在锅台子上猛砸一捶说:“不行!他湖北客敢跑到咱任家村来胡骚闹?不收拾掉这个骚男人,咱弟兄们还算条汉子吗?再说,她红裤子也不对,你痒了你就言传嘛,咱任家村有的是光棍,难道没人给你止痒痒……”
二癞子把狗剩又按倒坐在炕沿儿,说:“我说狗剩呀,这红裤子可是和她亲哥哥在一块儿通奸啊,人家要不承认这事,你说出来可就收不了场啊……”
“屁!哪里是她亲哥哥?你倒忘了,四年前红裤子来咱们村时,不是怀着玲玲娃吗?这任月玲八成是这个骚男人的种……”狗剩说。
“照你这么说,这骚男人是红裤子在娘家时的情夫?”二癞子问。
“对,这两个货在老家那儿可能经常在一块日哩!”
“妈那个X,在你们湖北随便日,我们管不上,在我们任家村随便胡来不成……我们村有我们村的规矩!”狗剩扇火着说,“二哥,咱俩再联合几个人,到村长那儿告他去……”
“走,告他去!”
两个人粗野地骂了一阵,发了一阵牢骚,就走出门向村长的家里去了。
村子里发生的事情,“老好”不知道,他照常去田里割麦,照常给他的丈人哥递“大雁塔”香烟,照常去打麦场上睡觉……
红裤子和她的娘家哥,今天分外精神,走路都是轻飘飘的。两个人眼里不时地传递着感情的信息,和谐而甜密。
难熬的白天终于熬完了,夜幕带着闷热,又一次降临在任家村的巷巷道道。
喝罢汤,老好依然如故,又背着铺盖卷儿到大场里去歇息。
刚一走,娃她舅就迎面把红裤子抱住,一个劲地在脸上啃。红裤子推开他,说:“你咋这冒失的?月玲还没睡着,你……再说,天刚黑,村里人还都没睡哩,叫谁看见了,咋得活?脸往哪里搁哩?”
娃她舅松开了。
红裤子说:“既然我给娃她爸说你是我的娘家哥,当哥就要像当哥的样子,放得稳里稳重的,不能让他看出一点点破锭……”
“喔,你说得对,说得对!还是小心点为好。”
红裤子把他按到炕沿儿坐下,说:“我去打麦场上转一回,看娃她爸睡了没有。要是没睡,咱们还不敢胡张狂哩。”
“对,小心点好。”
红裤子端来热水瓶,说:“我给娃她爸顺便送一缸开水去。要不,咱们刚脱了衣服,他口渴,又转回来要喝水,岂不冲了咱们的好事……要是叫‘老好’发现了,他那好人犯了脾气,也惹不起呀!”
“好,你快去快回,不要叫我久等。”
还不过二十分钟,红裤子就从大场里转回来了。娃她舅问:“他睡了吗?”
“睡了睡了,正打着呼噜哩!”
“你们村里人有啥反映没有?会不会有人怀疑咱俩的关系……”
“没有,啥也没有,再不要疑神疑鬼的。你放心!刚才我到场里去,二癞子和狗剩两个家伙,还和我耍笑哩,要我陪娃她爸在打麦场睡觉,硬把我朝芦席上拉哩!”
“那你咋不在场上睡哩?”他笑着问。
红裤子“哼哼”一笑,钻进娃她舅的怀里。
娃她舅“蓦”地一下,把红裤子抱起来,撂到了土炕上。
“甭急,还没关门哩!”红裤子说着跳下炕,摸着黑关了前门。
十分钟后,当他们两人都脱得赤条条的,互相搂抱到一块的时候,电灯被人从屋子里边拉亮了……
二癞子和狗剩两人站在脚地当中,气势汹汹地说:“干什么?干什么?你们两个不要脸的东西!快松开!”
接着,屋子外面也有人敲窗子,还有人用脚踢门板,并大声吆喝:“把门开开,捉住这两个狗男女!”
衣服早被二癞子抓在手里,虽然是大热天的,两个人精屁股蹴在土炕上,还是直打哆嗦。
二癞子去开门,狗剩拦腰一把把红裤子软囊囊的肉身子抱在怀里,直朝门外走去。
冲进门的小伙子立即扑上去,用一根早已准备好的麻绳子把湖北客五花大绑,拉下了土炕。
大柳树上的铁钟被谁“咣咣咣”地敲得山响!
在这夏天的夜晚里,钟声传得很远,任家村南北两条巷子的人都赶来了,就连槐树庄的小伙子听到紧迫的钟声,不知这儿发生了什么失火事儿,也都像烽火救幽王一样急急地赶到了大柳树底下。
刚才还在水渠里一压声儿吼的青蛙,这阵儿也不见鼓噪了;蛐蛐儿停止了歌唱,乖乖儿躲在草丛中不敢动弹。
大柳树底下站满了各个村庄来的男女,有老人,有小孩,有光着膀子的老婆子,也有穿戴整齐的小姑娘,人们把目光齐刷刷地向柳树底下的一个大碌碡上望去。
村长站在碌碡上边,伸手朝老柳树的一个枝杈一指,说:“大家朝那儿看……”
霎时,树股上的电灯泡亮了。灯泡儿后边的树股上吊着一个光着身子的男人,两只手被反绑着,像杀猪架子上吊着一扇褪了毛的猪肉。
“正是夏收大忙季节,这位不速之客悄悄地窜进了我们任家村,乱搞两性关系,骚扰夏收秩序,害得社员们不安心生产……”村长在碌碡上转着身子,向大柳树下赶来的人们解释着事情起根发苗的过程。为了让所有的人都能听得见,他一会儿面向东,一会儿面又向西。当人们听到村长的讲话后,像一窝蜜蜂被谁戳了一竹竿那样,顿时“嗡嗡”开了。村长故意停了大约五分钟,让人们充分“嗡嗡”之后,又说:“我们任家村向来是礼仪之村,绝不容许这种腌趱的事情发生。为了严整村风民俗,你们大家说,把这个骚水水乱甩的湖北客咋样处理?”
大柳树底下立即爆发出各种不同声调的建议:
“点天灯!”
“活扒皮!”
“大卸八块!”
“开肠亮肚!”
村长朝四周围巡视一遍,见大伙儿义愤填膺,就跳下碌碡把一把皮鞭交到二癞子的手里,然后又跳上碌碡,说:“我们还要讲点仁慈,不能那么残酷。就抽皮鞭吧,让全村的人轮流抽打,一直抽到断气为止……”
“冤枉!”柳树上被吊着的男人,晃动了一下身子,大声哭喊。
“村长啊!我们确实冤枉……”大柳树桩上也发出了一个女人脆生生的叫冤声。
于是,人们又把目光朝大柳树桩上望去,只见一个女人光着身子被绑在那儿。一头乌发零乱地披在胸前和背后。两只雪白的奶子被麻绳子绑得奓了起来。肚脐眼和大腿上的绳子都钻进肥囊囊的白肉里去了。
“我们是亲兄妹啊,材长,不能冤枉了我们!”这个光身子女人继续申诉着。
这时,人们才听出是独庄子“老好”的婆娘红裤子,因为她那湖北口音跟任家村的人总是不一样。在任家村,操湖北口音的女人就红裤子一个人。
要是在平时,人们发现这两个让人眼馋的“西洋景”,不知要戏弄到什么程度;可是,今天晚上这个场合——村长那杀气腾腾的面孔,被绑的那两个战战兢兢的男女……人们只好悄着声儿站在那里,连大气也不敢呵一声!
二癞子走上前,给手心吐了一口唾沫,牙齿一咬就抡起皮鞭,朝柳树股上吊的那个男人打去。
那男人光嘟嘟的肉身子被二癞子的皮鞭抽了一下,就身子一摇晃,喊:“老爷们,我们冤枉啊!”
二癞子又抽一鞭子,那男人再喊:“我的妈呀!我受不了啦……”
二癞子再抽一鞭子,那男人又喊:“我俩没得那事啊……”
“嘴还犟!打不美你不讨饶……”村长又把皮鞭夺来,递到狗剩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