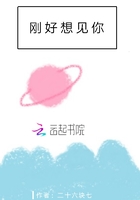冬日城郊,茫茫一片荒野,清晨薄雾笼罩,四下望出去都杳无人迹。天青一手提着一篮供品,一手扶着樱草,两人默默无言地走在小路上。数只寒鸦自他们头上飞过,呱呱叫了几声。
“三七也是大日子,按说应当由她亲人主持,好好做个法事啊。”天青惆怅地望着前方。
“我们自己尽心,也就是了。玄青师哥还是不肯过问?”
“他压根儿不肯开门……我对着门缝告诉他殷姑娘墓地所在,他明明就在院子里,却一声不出。问他到底出了什么事,更是不肯理我……”
樱草凝思良久,摇了摇头:“想不明白的事太多了……”
三七二十一天前的那场宴会,全然来了个出乎意料的结尾。天青与樱草本已抱了必死之志,孰料没人再来管他唱不唱戏,只听得小屋外面一直乱到半夜,几个日本兵冲进来,将他们二人与一班伶人一起,没头没脑地拖进地下拘留所,没头没脑地关了三天,又没头没脑地放了。押出红楼路上,天青望见停在刑场的尸首,这三天他已听说,是在宴会中下了剧毒,与焦德利、黑山少佐同归于尽的女人。
他认得她。纵然她已面目扭曲,嘴角血迹斑斑,仍然不减那眉梢眼角的风流韵致,她就是深居于官帽胡同玄青家里,被天青冒叫过一声“嫂嫂”的殷姓女人。天青怎么也搞不懂,这女人为何会从天而降,在这样的生死关头以性命相救,不但解脱了他与樱草的危难,还为他报了杀师血仇;他只记得那个小院中的短暂相逢,石榴树下款款待客的她,宁静温婉,风华绝代,她深爱他的师哥,言辞间满是浓情蜜意,小院中岁月静好,远隔红尘……怎么突然有这样急转直下的结局?
崔福水死也不许天青去红楼认尸,急得嘴唇都白了:“这次和白二爷那次不一样,这女人毒死三个日本军官,红楼正在满城抓捕同谋,你再上门,就是找死!”
“我不能任由她曝尸荒野!她于我有救命和报仇的双重恩……”
“那也不成!好不容易出了火坑,怎能又跳回去!再者说了,你怎么认尸,你是她什么人,知道她家乡何处,姓甚名谁?”
天青哑然。
这神秘女子,成了个解不开的谜。身藏的毒药被搜出后,日本人疯狂查勘她的来历,结果所有线索都指明她是焦德利的表妹,由焦德利带到酒宴中来。她与焦德利都已中毒身亡,了无对证,日本人把焦府搜了个底朝上,合家大小一一拿去讯问,也未得出个所以然。最后好不容易,顺藤摸瓜抓到邓漆园,拷打逼供,做成这桩大案的首犯,游街示众,押赴刑场枪决。殷绣帘呢,在红楼曝尸多日,无人认领,照以往惯例,用大卡车与其他无主尸首一起,拉去平则门外护城河边丢弃。
天青冒着冬日严寒,深夜潜藏在平则门外,寻到了死人堆中的殷绣帘。他背着她的尸首走了几里夜路,将她埋葬在梨园义地。这块地由梨园公会统一购置,葬的都是穷苦得买不起坟茔的梨园同侪,四下野寂荒凉,但是起码,是个魂灵安歇之处。没有棺木,没有随葬,没有法事,没有祭礼,什么都不能做,天青只能以一袭薄被,裹了殷绣帘尸身,埋在徒手挖出的土坑里。深冬寒夜,凄冷无匹,他燃起香火,恭恭敬敬跪倒,拜了三拜:
“姑娘深恩,终生不忘。往生之路好走,来世安居乐业,福寿双全。”……
梨园义地到了兵荒马乱的年月,墓园乏人修葺,更是荒芜一片。远远望去,遍地枯黄,荒坟中间,竟然有个熟悉的人影。
“师哥……”
玄青像一头受惊的狼一样从殷绣帘坟前跳开,恶狠狠地盯着天青与樱草。
玄青的世界,整个儿坍塌了。
他万没想到,殷绣帘竟然早萌死志,这一去再也没回来。他当然知道焦德利必将让她遭受一番非人蹂躏,但是殷绣帘是八大胡同出身,陪一次客,有那么重要吗?他穆玄青都不在意,硬是咽下心头怨气,将自己的女人送到别人手里,她怎么就不能忍耐这一回?居然拼上性命,真的做起了贞节烈女,不但自己死了,还毒死了堂堂的公安局副局长和几个日本人……讯息传来,只吓得玄青魂飞魄散,不知投奔哪里藏身的好:这若是被日本人查到殷绣帘的来历,他得是什么下场?
更没想到的是,这桩案子居然没有牵连到他,竟然从焦德利那里,直接扯去了邓漆园头上。玄青起先还庆幸自己福气好,后来才想明白:那是因为焦德利将这美女献给日本人的时候,根本没提他穆玄青的忠心!他又被骗了,总是这样被吃得死死的,所有人都欺他,骗他,害他!
失去了殷绣帘的家,变得阴沉惨淡,地狱一样凄清。再没人为他打理衣食,曲意奉迎,再没人娇语呢喃,软香温玉,宛转郎膝下,无处不可怜……这一个月来,玄青独居小院,日日暗风吹雨入寒窗,孤灯挑尽未成眠,凄惨得无以言表。到这时他才发现,自己的生活,早已和殷绣帘密不可分,这个身份低贱,始终没被他真正放在心里的女人,倾尽自己的一切来对待他,无怨无悔地守护他,他所有的舒适安稳都来自她,这世上唯一能让他顺心遂意的,只有她,她让他过了足足六年宛若深宫帝王般的日子,最后,被他拱手送给了别人……
深重的怨、恨、恼、悔,如熊熊烈火燃烧着玄青身心。焦德利死了,所有承诺都没兑现,戏协成立了,根本没有他的份儿……曾经企望过的前程与未来,一个接一个地破灭,能做的只有逛窑子、酗酒、抽大烟。失去了殷绣帘,他就快连抽大烟的好日子都没有了,已经没钱再去抽“公益厚”的上品烟膏,只能从小贩手里买些掺了灰的劣质烟土,味道辛辣,直冲喉咙,咳得五脏六腑全都翻转过来。他翻箱倒柜,把家里所有值钱东西都当掉,连这座寄托过未来梦想的小院,也给抵押掉……
那个冬夜,森寒透骨,抽足大烟的玄青,却感觉全身火热,宛若浮荡在一片蒸汽中似的飘飘然。他终于找到殷绣帘藏在抽屉深处的钥匙,打开了已经成年没进去过的南屋。灯火之下,这屋子也仿佛浮荡着一片烟雾,缥缥缈缈中,现出靠墙摞放的整排樟木箱。箱子里面,是他的行头,攒了二十年,全套的,金光灿烂,花团锦簇的戏衣盔帽:红龙蟒,蓝官衣,杏黄软靠,青素褶子,老斗衣,鹤氅,文阳,台顶,侯帽,鞑帽,高方巾,员外巾……
殷绣帘把它们收在这里,自他不唱戏后,再也不许他打开。这所有箱子加一起,起码值五六千大洋,玄青几次打过主意想当掉换钱,但是殷绣帘宁愿节衣缩食,把自己带出来的田契地契、珠宝首饰,一件件当掉,也不肯动他这行头一丝一线:
“总有一天,你还要上台的,我等着你把它们重新穿戴起来,仍是最好的角儿……”
玄青哆嗦着双手,翻出钥匙,一只只打开箱子。里面的戏衣盔帽,分门别类,叠放得整整齐齐。他已经很久没接触过这些东西了,手感都已生涩,但是一旦披了上身,仍立刻找回那熟悉的感觉。昏黄灯光下,他站在满地戏衣里,戴一顶王帽,裹一件黄龙帔,耳边响起隐约的丝竹锣鼓,一时间不知道是幻是真。他仿佛又回到广盛楼,台下万众瞩目,喊好儿声此起彼伏,而他傲立台毯当间儿,在那最醒目最亮堂的灯光下,唱一出圆满大戏,台下一排排充满仰慕的面孔里,他看到殷绣帘……
眼泪从他早已干涩的眼底,止不住地流出来。这本是他从小做到大的梦啊,人生唯一的、真正的梦想:唱戏,成角儿,师父的宠爱,兄弟的尊崇,万千戏迷的追随,心爱女人的仰慕……怎么一步步走到了今天的?是谁逼的他,谁害的他?失去的这一切,要怎样才能索回来?
天已经亮了,他迷迷茫茫地出了家门,往平则门方向走去。天青曾来告诉过他,殷绣帘葬在梨园义地东南角,木牌上写了姓氏。玄青怕受牵连,本打定主意一辈子不跟这座孤坟拉上干系,但这一片浑浑噩噩之中,仿佛有什么一直在牵扯、拉拽着他的脚步,让他控制不了自己的心……他都不知道是怎样走到坟前的,只见地上那么一小抔黄土,插着一个小小的木牌,只写了五个字:“殷姑娘之墓”。
他的眼泪,又落下来了,转瞬间被寒风吹得干在脸颊。面对着这座坟茔,他恍然又觉得自己是在戏台上,受着台下痴恋的目光追随,他下意识地掂起衣袖,眼望空茫的前方,嘶哑着嗓子唱了两句:
劝梓童把此事休挂心上,劝梓童把此事付与了汪洋。
宫娥女掌银灯引回罗帐,孤与你同偕老地久天长……
猛然间听背后似有人声。玄青如大梦初醒,仓皇转身,映入眼帘的,是他今生最不想见到的两个人。
天青与樱草都怔住了。
要说这位师哥的偏执脾气,暴戾性情,满心里不可收拾的妒忌,天青自小儿跟他一起长大,岂能全无所知,然而毕竟师兄弟一场,为着一家和气,屡次一忍再忍。但是,日前师父惨亡,全城相送,仍不见玄青露面,是可忍孰不可忍?天青胸中努力维系的一点兄弟之情,至此终于熄灭得干干净净。去他门上告知殷姑娘墓地所在,那是看着殷姑娘面子,吃他一个老大的闭门羹,实也是意料之中,倒是眼下,忽见他出现在殷姑娘墓前,令天青诧异万分。
“师哥……”天青看到他脸上半干的泪痕,心中不禁涌起了同情,“你来祭拜殷姑娘?”
玄青向后退了两步,全身绷紧,一声不出。
“她怎么会跟日本人……”
“跟我不相干!”玄青惊跳起来,尖声叫道,“我送去时候……可没……”
天青胸中震荡,一时呆在当地:“你……你把她送去?……”
玄青双手乱摇:“不,不是我,我不认识她!”
樱草抓紧天青的手,两人对视一眼,心中都充满了震惊。虽不知到底发生什么,但得是何等凉薄心思,才能把陪伴多年的身边人送到日本人手里?……玄青在天青怒视下,仓皇又退一步,眼神中疯狂的光芒,在天青与樱草身上扫来扫去,盯着他的腿、两人相扶相牵的手,最后视线停在樱草已经高高隆起的小腹上,死死地盯了又盯。
“殷姑娘,今儿是三七之日,我们来看望您!”天青咽下心头郁气,径自拉着樱草走到殷绣帘坟前,两人一同跪下,拜了一拜。天青自篮中取出鲜花供果,一一陈设坟前,又取出香烛、洋取灯儿,在手中点燃……
忽然间,仿佛空气中有一记无声炸裂,震荡天青脑海,令他本能地回头。他看到的是一张无比狞恶的脸,手举着不知从哪座坟前拔来的一座蜡钎,长长铁尖正冲自己后脑刺落。天青不及反应,先一把推开身边樱草,回手向后一格,蜡钎刺在他手臂上,划出深深一道血痕。玄青一击不中,猛地扑向樱草,一只手勒住她脖颈,拼命向后拖去,另一只手,将带血的蜡钎抵在她下颌。
“师哥!你……干什么!”
“干什么?要你的命!”玄青目光灼灼,闪动着异样的兴奋,咧起的嘴巴露出整排白牙,“我什么都没了!你什么都有!凭什么!宰了你,宰了你媳妇,宰了你的小崽子!”
天青惊骇万分,全然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的玄青面目狰狞,势若疯狗,樱草被他勒在手臂中,痛苦地挣扎着,抵在颌下的蜡钎染满鲜血,不知是自己的,还是她……天青后退一步,哑声叫道:“放开她,师哥!你要我做什么,尽管说!”
“哈哈哈,我要你做什么……”玄青嘶声大笑,“我要你死!给我血债血还,报仇雪恨!”
“你疯了,师哥,你我兄弟之间,哪有什么仇恨!”
“哪有什么仇恨?”玄青咬牙切齿,一字字仿佛都带着刀光迸出来,“你自小儿欺我害我,抢我的戏、我的戏份、我的头牌、我的班社、我的女人,逼得我没台可上、没戏可唱,行内行外瞧不起我,所有人都拿我当碎催,你问我有什么仇恨?”
天青咬紧了牙关。这师哥早已被嫉妒烧到疯狂,无可理喻,但如今樱草被他胁持,也只能竭力应对:
“你我之间都不是一个行当,完全可以各自打出一片天,何来抢夺之说?爹爹一心希望你承接他的衣钵,想方设法教诲你栽培你,只要你自己争气……”
玄青暴跳起来,抵在樱草喉间的蜡钎,危险地颤动着:
“靳天青,你从来不肯反省自己!我怎么争气?打擂台的是你,跑码头的是你,义务戏是你,堂会还是你,参加比赛赢取名利全是你,如今你红遍天下,富甲梨园,所有香的辣的都被你一个人吃了,什么各自打出一片天,你把我的天留在哪儿?”他的眼中充满疯狂的血红,放低蜡钎对准樱草小腹,“你挺有本事的,让你下高摔下来,也没摔死,把腿弄断了,还能接起来,抓着你的女人,还能被人救了……今儿她又落在我手里了,你猜我想怎么做?”
“啊……!”
被他勒在手臂中的樱草,忽然发出一声惨叫。天青大惊失色,连叫:“樱草,樱草!”他本是虽万千人吾往矣的血性男儿,但是事关樱草,顿时缚手缚脚,眼看着那支蜡钎随时都能伤她母子,一时间投鼠忌器,无计可施。玄青桀桀怪笑,得意地攥紧蜡钎:
“你寻思你什么都有,是不是?我叫你马上就没有!来,瞧好了,一尸两命,这是师哥我,送你们的一份大礼!”
仿佛一道炸雷直劈头顶,樱草刚刚已经乱成一团的脑海,瞬间恍如被直劈两半,痛得她整个人蜷下身去。这句话,这腔调,这如石块般尖锐冷硬的声音,这紧勒脖颈的手臂,终于割开心头一片长久笼罩着的迷雾,无数纷飞的碎片,旋风般翻腾到她的眼前:广盛楼的小屋,夜色中昏黄的灯火,站在门外的人影,一张泛着酒意的脸,血红的燃烧着的双眼……“要成亲了吗?可喜可贺啊,我送你们一份大礼!”黑暗、绝望、惊惧、苦痛,纠结在一起,割开她的头,刺穿她的心,撕碎她的身体……
“樱草!樱草!你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