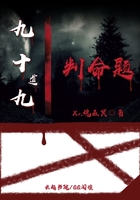“那十七年,美得不敢回头想。中途也有过不测风云:我师弟走‘高毛’时摔在我身上,撞坏了我的腰,回来就瘫炕上了。唉,咱们唱武戏的,伤筋动骨乃是家常便饭,但那一次真是几乎要了我命,全靠你师娘连日连夜伺候,吃喝拉撒亲手照料,几年时间才调理过来。后来她生了个宝贝女儿丹丹,小小的瓜子脸,黑黑的大眼睛,跟她长得一式一样。我们一家三口,就在这九道湾的院子里,过着和和美美的日子。那时候我改工老生,渐渐地也唱出名气,自己挑了班,收入很好,满拟终于能给她们娘儿俩好日子过,想不到……想不到…………”
他吸一口气,艰难地说下去:
“那年爆发伤寒,她和丹丹都染上了,没多久的时间就……就……就都……她临走时候,拉着我的手,说了最后一句话:大哥,跟你这十七年,我没过够……”
泪水终于从白喜祥眼中滚落下来。
“你问我怎么不续弦,你说我怎么能续弦?我心里不会再有别人了,这辈子不会有,下辈子也不会有。我就等着她来世回来找我,我们还要在一起再过几辈子。这些年我再没跟任何人提起她,但是她一直都在我心里头。”
天青眼中泪光闪闪,低声道:
“对不住,师父,我不该勾起您的伤心事。”
“跟你说说也好,你我师徒有缘,境遇相仿,心志也是一般,彼此相知相照。旁的人,听了也不以为然。我师父三老爹就总说我为人太痴,戏唱得多了,有点疯魔了。他说,戏是假的,唱戏的是疯子,听戏的是傻子,真实生活中,哪有那么多至情至性的事。唱戏的人,反而要比一般人更加远离七情六欲,方能把握戏的分寸。我始终没能做到他说的这一点,所以戏品总归不是上乘。”
天青认真想了一下:
“师父,我觉得,为人就是要至情至性,方不枉来世间一场。您和师娘,还有我和樱草,虽然都经历不少血泪,遭遇不少离合悲欢,可是和心爱的人厮守在一起的时光,千金难换,再叫我重新经历一番,也不后悔。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您说得对,有过这样刻骨铭心的情意,此生心无二致,就算没了樱草,我的心里也没法容下旁人。戏是假的,情是真的,这两样儿都是不能改变的。”
他眼中满是温柔,回头望向樱草,突然之间,猛跳起来:
“师父!樱草……”
白喜祥抬眼望去,一时也呆在当地。
樱草的眼角,挂着两行泪。
“你哭了,樱草?你听见我们说话了?”天青急切地握住她的手。
她的小脸正对着天青,夕阳照在眸间,光芒闪耀,反射着天青的身影。她千真万确地是在看天青,眼中已经有了神情,迷惘而专注的,分分秒秒都不舍得移开视线的神情。她的手指在天青手中微颤,一下下轻触他的掌心,这不是无意识的悸动,是在努力地想握他的手。
“樱草!”天青不顾茶棚里众人瞩目,半跪在轮椅车前,颤声呼唤,“你醒了?!……”
樱草已经在茫茫大雾里跋涉了很久。
四下空空寂寂,伸手不见五指,天地间只剩了她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来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出去,只是茫然地被白雾挟裹着,飘浮在无边无际的空中。
从未像现在这样意识到自己有一具躯体,因为那躯体上无处不痛,骨骼筋肉,仿佛都在翻滚挣扎着,一片一片撕裂开去,尤其是头上,时常涌起一阵难耐的剧痛,痛得脑海中一团痉挛,生不如死。她想挣扎,但是动弹不得,想喊叫,也完全发不出声音。
一直就这样飘浮下去吗?这样的痛苦,哪里才是止境?
“樱草,樱草!……”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她的肌肤能感觉到一点点温度,一点点轻柔的触碰,让她的孤独和绞痛,都有暂时缓和。她的耳边,也渐渐能听到一点点语声,她不能听懂它的含意,但那语声是那样地熟悉、亲切,仿佛已经伴随过她几生几世。每当这语声在她身边响起,空茫的心里,就感觉到一片安然,周围紧裹着的浓雾,也如一道厚重的保护层一般。
“樱草……等你醒过来,我们就……丁香树又开花啦,你能闻到吗……今天的戏……”
她就在这听不懂内容的低语中,在那不知所以的香气中,反复地入睡和醒来。
入睡和醒来,渐渐有了区别,眼前的浓雾有些许的消散,让她能看到模糊闪动着的影子。是个很熟悉的影子,发着很熟悉的声音,连他的抚摸触碰,都那样地熟悉。他好像无时无刻不在,在她想到他的所有时候,都陪在她身边,一句句喃喃地说些她听不懂的话……不,有的话她渐渐能听懂了呢,比如说,樱草,这是在叫她的名字。
她恍惚记得似乎也知道他的名字。她应该叫他什么呢?每当细想,脑海中便是一阵剧痛。他的声音,常常让她心中有莫名的酸楚,不能控制的,发生在内心最深处的翻腾。这声音屡屡地让她想挣扎着起身,想抓住什么,抱住什么,想发出声音,想喊一个名字……
耳边听到的,眼前看到的,这所有碎片逐一拼起,渐渐让她想起更多事情。一条狭窄的胡同,一个方方正正的院子,丁香树,枣树,金鱼缸……她想起了鱼缸里漂浮的绿色茶叶,想起树下拴的小羊……想起一张张的笑脸,一个沉静的老人,一个胖胖的满脸麻子的女人,还有一个长得敦敦实实的大光头,圆溜溜笑眯眯的眼睛,老是在她面前飞快地晃来晃去,还有一张清朗的脸,眉宇轩昂,目光湛亮地望住她……为什么一想起这张脸,总是有什么东西在心底涌动着,仿佛随时要爆裂出来?
她能看到这张脸了,越来越清晰,越来越亲切,让她想起更多东西:一个高高的台子,五颜六色的华服,铿锵有致的旋律,灿烂华美的身姿……这叫什么?她慢慢想起:这就是那个声音一直在说的“戏”。他有时候会唱戏给她听,每一句都似乎有一段故事,在她脑海中久久回荡,搅起一些沉在最底层的碎片:
“常言道,人离乡间,似蛟龙离了沧海……”
天啊,这曲子一准儿跟她还有更深的关系,她得慢慢想,使劲把它想起来。
“这些年来,我还是总能在画里,在梦里见着她……”
“大哥,跟你这十七年,我没过够……”
“此生心无二致,就算没了樱草,我的心里也没法容下旁人……”
“戏是假的,情是真的,这两样儿都是不能改变的……”
这些似懂非懂的话,里头带了些她无法说清的东西,是那熟悉的声音还是那真切的情意,让她控制不住心头的颤动。一瞬间仿佛滔滔江水开了闸,那积聚已久的泪水,终于夺眶而出。她没有办法抬手擦掉它,还好,那双熟悉的手伸过来,帮她拭干了双颊。
“樱草,你醒了?樱草,你,你能看见我吗?”
她能看见他,他急切地注视着她的脸,目光中盛满了深深的爱惜。这个人,她准定知道他,他与她的生命中,有些什么至为紧密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她努力地想握回他的手,以后一分一秒都不要分开,她的脑海中,逐渐地浮出他的名字来:
“天……”
想开口,但是嘴巴还是不听使唤。
“天……”
她凝视着他,眼中充满了希望也带着挣扎不出的绝望。她没有办法发出声音,但是她的目光似乎让他明白了,他抱住她的身子,脸贴在她的脸颊,滚滚泪水带着无尽的温暖和喜悦,一同传进她的心底:
“你醒了,樱草!我知道你会回来!”
“天青,社里出……出大事了!”
黎茂财气喘吁吁冲进白家小院时,天青正小心地搀着樱草练习走路。入秋以来,樱草状况大好,已经能被他牵着手走几步,能听懂几句简单的话,只是时常口唇微动却仍然发不出声音。现在的她,完全像一个懵懂孩童,眼神总是天真的单纯的充满困惑的,整日像刚出壳的小雏鸡一样紧跟着天青,目光只围着他转,寸步都不肯离开。
“慢慢说,黎爷。”天青安抚住慌得直跳脚的黎茂财。
“咱们被,被查封了!”
“什么?”
“说是戏码违禁,有碍社会秩序,勒令整顿……传您去局子呢……”黎茂财擦着汗,战战兢兢地递上传票。
天青真是做梦也没想到,自己此生,还会再次跟公安局扯上关系。不过这次在公安局里面对着的,不是威风凛凛的焦自诚局长,也不是阴毒险恶的焦德利,而是戴眼镜梳分头,看起来文质彬彬的一位风化科科长。
“敝姓叶,叶葱茏。说起来还是靳老板的戏迷呢,如今为了公事,不得不在这样的情形下相见,惭愧,惭愧。”叶葱茏双眼放光,客气得近乎毕恭毕敬,亲自为天青端茶倒水。
“不敢当。”天青起身施礼,“敢问叶科长,敝社因为什么缘故被查封?一直以来,经营上小心谨慎,戏码都经过反复斟酌,全以‘亲爱精诚’‘礼义廉耻’为宗旨,绝对符合政府‘新生活运动’精神,何来有碍社会秩序一说?”
“咳,靳老板还真是词锋锐利……”叶葱茏嘿嘿一笑,“这么说吧:‘亲爱精诚’‘礼义廉耻’那都是没错的,但是承祥社贴了太多抗金抗清抗匈奴的戏码,却不符合政府‘攘外必先安内’之指示。”
天青眉头微蹙,默不做声。
“贵社新编大戏《精忠报国》《德胜门》《破匈奴》在社会上反响极大,南方也有搬演,连地方戏都在移植,对民心之动摇,不言而喻。您在台上一准儿也看着了,每次贴演,座儿上都是一片激愤,纷纷谴责政府对日军侵略之不作为,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攘外必先安内’是政府经过周密论证后制定的国策,岂可如此公然针对?”
“叶科长,这我就不明白了:忠孝节义,保家卫国,乃是千古以来人伦至理,怎么到了开化文明的新时代反倒不能唱了?”
“非常时期,非常时期啊。诚心奉劝一句:这种敏感的政治问题,靳老板还是避而远之,明哲保身为妙。”叶葱茏莫测高深地推推眼镜,“说实话,还是我从中斡旋,才只是查封班社,免了靳老板的牢狱之灾。啧啧,单从戏本身来讲,《破匈奴》真是一出佳作呢,那段‘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西皮二六,可真是脍炙人口,家严每日都挂在嘴边。只可惜生不逢时,也只能道一声遗憾哪。”
“长官,长官,”黎茂财连连打躬作揖,“还要请您继续高抬贵手,解除禁令吧,社里百来位兄弟等饭吃,停业久了,难免也是社会之患。”
“那就要看贵社肯不肯悔改了。”
天青心中愤激,但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一个唱戏的班社,如何抵抗得了公安局的禁令?他沉声道:“恭请叶科长指教一下,现在倒是什么戏能唱?”
“‘唐三千,宋八百,数不完的三列国’,能唱的戏那可多着哪。搁我说呢,您可以多排些剿匪的戏码。”叶葱茏的眼睛在镜片后闪着精明的光,“您知道,南方共匪作乱,清剿十分艰难,乃是党国心腹大患。您贴些《恶虎村》啦,《洗浮山》啦,号召民心支持政府剿匪安内,才是正道。黄天霸的‘八大拿’也都是靳老板拿手嘛。您把戏单改了,呈报上来,缴过罚金,指日可获解禁。”
“我……日寇侵略当头,我去唱不痛不痒的剿匪戏?”
叶葱茏脾气倒好:
“靳老板,识时务者为俊杰哪。”……
“天青啊,伶人和政治,最好还是不要扯起关系。既然政府禁令如此之严,那几出戏还是挂起来吧。”白家小院里,白喜祥沉吟道。
天青犹自愤愤:“保家卫国都成了禁戏,这同前清的文字狱有什么两样?日本人打在家门口了还视而不见,倒和我们唱戏的较起劲来!社会上反响大,那是民心所向!凭这个责罚我们,我不服!”
“天青,你要为社里弟兄的衣食着想。”
天青闭上了眼睛。
“师父,难道真要按他们说的,去唱‘攘外安内’的戏?这种做走狗的行径,我真是厌恶。自己的心胸信念一概抹杀,只跟着官府做些违心的事儿,我岂不是真的成了黄天霸?共产党什么的我不懂,但是少湖兄跟我提起时是很赞许的。”
白喜祥凝目远望:“国家大事,原不是我们做伶人的能明白。你不愿意去唱黄天霸,那也由你,贴些别的戏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