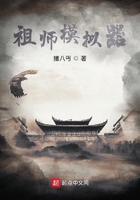“该不是跟那位顾小姐有关?”崔福水疑惑地念叨,“天青,她对你有意,这可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
钱师傅愤愤道:“这算什么,白字黑字的戏约在手,赖账不给?咱们回北平一宣扬,对他们顾家父女都没什么好处。”
“人家江北皇帝,哪怵这个。咱们又拿不出账上的真凭实据。”杨二爷摇了摇头。
“随他们便吧。”天青双手插在腰际,开始绕着院子踢腿,一记记踢得又准又稳,毫无犹疑:“只剩两天了不是吗?之后三天都是不收戏份的答谢戏了。钱是小事,行家眼睛都看着:三十六场戏,场场满座,没堕了我师父的威名。崔爷,劳您代大伙儿订星期天的车票,”阳光下他的额头微微冒汗,眼神却闪烁着比阳光更明亮的光彩,“只待吉时一到,奏凯还朝!”
广盛楼的夜戏唱到了尾声。
今夕登科皆因昨晚飞虎梦,英雄儿女原是前宵梦里人。
娘子啊!士为知己者用,女为知己者容。
儿女英雄熊罴梦,今宵好似鸳鸯戏水,其乐融融!
整出戏唱了有六刻来钟,樱草的嘴角一直就没平复过,忍不住始终挂着笑。台上那个笑眉笑眼的黑汉子,就是她的竹青师哥,如愿以偿地贴出了他师父郝二爷亲授的新戏《飞虎梦》。同是黑汉子,牛皋这个人,比李逵良善,比张飞温和,比焦赞睿智,是架子花脸中又一个有特色的人物,十分招人喜欢。戏中的牛皋和新婚夫人戚赛玉,在洞房里文比武比,谐趣连连,竹青在郝二爷调教下,将所有细节都唱得风生水起,分外热闹喜庆。
这位小师哥,终于也成角儿了。白喜祥已经给他挂了牌,郝二爷也十分器重,对他的前程,还有更多策划。看着自己关爱的人如此荣耀,比自己成功更加开心,樱草决定了:马上再为他做一顶相貂,助他学好师父的“活曹操”!
完戏后,彩声渐歇,看客陆续散去。因郝二爷在后台把场,樱草没去探望竹青,而是习以为常地,绕过戏园小楼,轻轻推开天青的屋门。夜幕早已降临,小屋中漆黑一团,樱草熟练地摸到炕头油灯,打火燃亮。昏黄的灯光将她窈窕的身影投在白墙上,微微跃动着,如一个仙子在轻盈地舞蹈,如一颗不安分的心在跳。樱草轻轻按住自己胸口,在炕头坐下来,安静地凝望四周。
天青已经来过电话,说后天早上动身,路上大约要走两天,那么,至多在四天之后,他终于又将回到她的面前。
如果说等待是被时光精酝的一坛佳酿,那么樱草的心房里,早已酿得满室醇香。这些天她不断地忙这忙那,拾掇九道湾的院子,归置小椿树胡同的院子,将两个家都收拾得整整齐齐,连这广盛楼小屋,都一遍又一遍,擦得一尘不染。其实天青回来之后,就不会住在这里了,他会搬到小椿树胡同去,迎娶她过门,从此以后,在那温暖的新家,永远和她厮守在一起。
她等这一天,仿佛已经等了一辈子。日日夜夜,都那么漫长。其实细细想来,从《八大锤》计起的话,他走进她的心里,也不过才四年时间,但是人生的厚度岂是长度能够计量,这短短四年时间里,他们经历了多少啊。就连这狭窄的小屋子里,也承载了他们不知多少记忆,点点滴滴,都只属于他们自己。
“你的小事,对我都是大事。”
“樱草,以后好好地爱惜自己,这一辈子,有你的平安,才有我的平安,你得知道,有人比在意自己更在意你。”
樱草慢慢盘坐到炕上,轻抚自己的脚踝。那个风雨之夜,就是在这个小屋里,受伤的她卧在这铺窄炕上,天青为她敷着面巾,按着脚,谆谆吐露他的心意;那个燥热的中午,也是在这个小屋里,她不知他在门外,大声地把深藏的心里话都喊了出来:我不但喜欢他,将来还要嫁给他,你去跟爹爹说吧,跟全北平的人说,我林樱草,要嫁给靳天青!
她终于要嫁给他了,不是幻想,不是梦,就在指日可待的将来。一个人要修行几生几世,踏遍几重关山,才能得到一个相知相契的爱侣?身边有了他,一切的风霜雪雨,颠沛流离,全都可以忽略不计。还有四天了,只剩四天了,走过这四天的时光,生命就将迎来最幸福最完满的巅峰,以后的日子,就如她颈上戴的那块小牌牌上镌刻的: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
夜已深了,樱草听得到门外人声,渐渐消失,院子里空荡寂静,仿佛只剩了她一个人。她站起身,却仍舍不得离开,满怀恋恋之情地环顾着屋子里的一切,轻轻拉过叠得整整齐齐的被子,依偎在自己脸颊边。那被子上十分明晰地带着天青的气息,她从小就熟悉的气息,令她一幕幕地想起,他练功练得汗流浃背的时候;他唱完一出戏,额头还留着勒头的印子,俯下身来冲她微笑的时候;他坐在她的枕边,伸出一只手给她握着,嘴里轻轻哼着戏文的时候;他将她拥进自己宽厚的怀抱,深深地吻她的时候……
“嗒”的一声轻响,屋门开了。
樱草从冥想之中惊醒,吓得几乎尖叫出声。缓慢打开的门缝里,透进一线月光,于门外的一片黑寂中映出一个穿长衫的身影,悄无声息,半明半暗,看起来熟悉而又陌生。他踏进门,看着她,眼神迷离散乱,有着揣摩不透的复杂神情。
樱草放下心来,笑了一下:
“……玄青哥?”
曲终人散后的广盛楼,和白天仿佛不是同一个世界。
玄青醉醺醺地站在院子门口,望着漆黑一片的戏楼。
这几天一直是竹青的大轴,玄青好不容易贴一次,只被排了个倒第三,唱《空城计》。做师哥的怎能为师弟垫戏?玄青抹不下这个脸儿,悄悄去找师父,希望起码改成压轴,但是白喜祥叫他开口唱了两句,登时连玄青自己也没法子再求下去。他最近大烟抽得多,嗓子确实不在家,一开口呲花冒嚎,别说压轴了,能上场都有点勉强。白喜祥十分忧虑:
“你这是塌中了么,才这个年纪?怎么越养越不济了。教你喝的汤药都在喝么?按说真不应该给你贴戏,但若是老不踏台毯,身上也完了。先唱着前几出,过了这个劲儿再做打算吧。为师对你也没有别的要求,稳着点,照大路唱下来就成。”
只照大路唱下来怎么成?玄青不甘心平平庸庸地垫这个场,铆足了劲儿准备好好要个菜。那晚的《空城计》,他振作精神,唱得比平时更加卖力三分:
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凭阴阳如反掌保定乾坤。
先帝爷下南阳御驾三请,算就了汉家业鼎足三分。
官封到武乡侯执掌帅印,东西战南北征博古通今。
周文王访姜尚周室大振,俺诸葛怎比得前辈的先生。
闲无事在敌楼我亮一亮琴音……
一段最能要好的西皮慢板,眼看着将将唱完,座儿上一片冷清,比起头几天竹青登场时那欢声雷动的场面,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玄青这心里的火,腾腾蹿起老高,一时也顾不上什么戏不戏的,将那最后一句“我面前缺少个知音的人”改了一改,先出一口气再说:
“……我面前只可惜对牛弹琴!”
座上轰的一声炸了,顿时乱成一锅粥,好几个人跳上戏台开始砸场子,连弹压席都在高声叫骂。玄青被揪下城楼,推在台前,见情形无法收拾,只好跪下来磕头赔礼,看客也依然不依不饶。黎茂财出来打躬作揖,根本没人理会,最后还是白喜祥亲自登台,说了不少好话,又承诺贴一出他的拿手好戏《打渔杀家》,凭这次戏票免费观看,这才平息了座上的怒火。
没说的,完戏后,玄青被师父责骂曰洒狗血,要菜,心中无戏,轻薄座上,罚跪了半宿的祖师爷。夜深人静之际,玄青烟瘾犯了,悄悄溜回官帽胡同抽一口,却又被打更的刘师傅发现,禀告了白喜祥。——这个老绝户的刘师傅,平日打更三心二意,都不怎么在院门口守着,怎么单单就这晚上长起了精神呢?
“什么事那么急,跪到一半跑开?”扮戏房里,白喜祥追根究底。
玄青一时答不上来。
白喜祥起身离座,仔细端详他的脸:
“你抽大烟了!”
他伸手指着玄青,微微发抖:“你犯了烟瘾!怪道嗓子这样,这一脸的烟容,我怎么早没发现!”
玄青原以为师父会雷霆震怒,至少也是一通咆哮甚至一顿耳光,没想到白喜祥并未发作,他只是盯着他,面色灰白,嘴角哆嗦,满眼都是伤怀绝望:
“玄青,我这么多年的教导,你听到哪里去了?戏品即人品,若是心术不正,再好的苗子也是白费!台上泡汤,阴人,台下疏于职守,无事生非,我念着十几年师徒之情,一次次宽容于你,你怎么至今执迷不悟,路子越走越歪?大烟这东西,祸国殃民,败家伤身,喜成社弟子,绝不允许沾染,我没说过吗?你从小儿一把好嗓子,瞧瞧今日败成什么样子!”
“那么多好角儿都抽大烟,还不是越唱越红,”玄青跪在地上,不甘心地抗辩,“杨大爷,谭大爷,马三爷……”
“你,你跟他们比?他们那么多的好处你怎么不比?台上的艺,台下的功,为人之德,处世之道,你好好儿比过吗?你跟他们比抽大烟?”白喜祥手抓着胸口,气息越喘越急,“玄青啊玄青!一直指望着你承继我的衣钵,这些年多少心血用在你身上,怎想到一次又一次地拉不回头,眼睁睁看着你走到这样!艺业荒废,还可以捡回来,人品败坏,谁也救不了你!”他浑身颤抖地望着他,良久,萧然转身,“你,你走吧!我没你这个徒弟……”
玄青低着头,狠狠咬着牙关。师父有了天青,有了竹青,不要他!虽然近年心情动荡,越来越不能专注于戏,但是毕竟也唱了半辈子,始终跟着白喜祥,一旦以这样的理由被开革出门,别的班社都不会再收,今后如何谋求生计?罢罢罢,只能再次忍得一时之辱——
“师父,您怎么罚我都成,就是别撵我走……”
黎茂财等人,百般劝慰,白喜祥本身又是个软心肠,说来说去,终于又收回成命,只罚他离社回家闭门反省,回归戏台之前,必须戒掉大烟。
玄青心头的郁火,无处消散。大烟,已经成了他的安慰,他的救命良药,他的精气神所聚,生命全部的依赖,如何能戒?戒不掉的话,以后的日子,又怎生处……几天来他闷塞难当,日夜饮酒消愁,连殷绣帘的软语温存,都不再安慰得了他。今儿又在肉市街喝了一晚上酒,酒足饭饱之后,走过广盛楼,只见夜戏已散,人去楼空,刘师傅又不在,院门虚掩着。他推开门,摇摇晃晃闯进去,望着那承载了半生荣耀与屈辱的戏楼,不由得满腔都是懊恨。
戏唱成这样,还叫什么戏?
自己这一辈子,算是彻底唱砸了。小时候,曾有过多大的雄心壮志啊,要站当间儿,要成角儿,要红遍天下,万人景仰……结果一直都被人踩得死死的,总是有人挡在他前头,无论他使多少劲儿,想什么招数,也始终都被挤得没路走!有的时候,真想一拍两散,不再唱了,此生彻底抛下这个戏字,但是,能吗?做得到吗?一日入行,终身带着梨园印记,十几年的功夫,满脑门的戏文,半生细细积攒、预备着有朝一日挂牌挑班的全套衣箱……怎能抛下,怎能舍得?他也爱戏啊,所做的一切,经受的一切,都为了要唱戏,要成角儿,只是,祖师爷不庇佑,命数不好,不像那个师弟……
他转过身,望向后院那间小屋,门缝里透出的一点灯光,闪闪烁烁地吸引着他的视线。那眼中钉肉中刺的师弟,就快回来了,去上海跑了一个月的码头,赚得盆满钵满,连北平报纸都连篇累牍地报道说轰动上海滩云云,捧得天上有地上无。这一回来,就要挑班,以后那更是站稳头牌的名角儿,哪里还有玄青的活路,连喜成社的班底和家当,也全部被他占去!那本应是玄青的,是玄青打小儿就认准了,必将属于自己的!他如今被逼到这个地步,全是因为他,全是因为他!……
一只蚂蚱自墙根半枯的草丛中跃出来,落在玄青脚边。玄青不待它跳开,一脚踏上去,狠狠将它碾碎,和满地的尘埃混成一团。忽然,他心中一动,猛抬眼盯着天青的屋门。
——既然天青还没回来,为什么屋子里有灯光?
“玄青哥,今晚怎么有空过来?”
玄青没回答樱草的询问,一声不响地迈进屋子,回手关上了门。他四下看了看,皱起眉头,视线又转回到樱草身上:
“你在这儿……”
他忽然明白了。根本不用问下去,樱草毫无疑问是在等天青。瞧她脸上神情,梦幻般的色彩还未褪,显然正畅想着两情相悦的场面呢。这么美丽的小师妹,侯门巨富的女儿,聪明体贴,心灵手巧,自小他只能像仰视一个仙女一样仰视着她,而她的眼中只有天青,一向都没有他……靳天青!他的运气怎么就这么好?
玄青向前迈了一步,在这狭窄的小屋里,马上就站到了樱草身前。他轻笑一下:
“他有什么好处,要你这样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