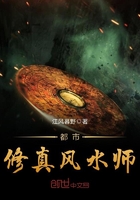大义务戏,就是不同班社的名角儿联合在一起搞的义务戏,伶人自身分文不取,收入用于赈灾或慈善。在北平时,只要大义务戏有邀,天青历来热心参与,本次虽然时间仓促,又是人生地不熟,他一听缘由,也还是毫不犹疑地接了下来。
“您想想吧,崔爷,为马司令筹军费,抗日!”天青的眼睛闪闪发亮,“马司令的名头,谁人不知,哪个不晓,东北孤军抗战,拼死守我疆土,那是真正的大英雄,大忠臣!能为他打日本鬼子出一点力,我觉得比我自个儿唱一个月戏更重要。听说他现在就在上海,要去庐山向蒋委员长申请,继续拉队伍抗日,希望他一举成功。崔爷,咱们这次的戏份儿,也拿出两成捐给马司令吧!……”
下午前来探望的魏华彩,闻听这个消息,却大吃一惊。
“勿可以,绝对勿可以。”他急得汗都出来,“靳老板,打炮戏之前,侬勿好去接别的活儿!”
天青安然道:“您放心,我心里有数,不会耽误打炮戏的成色。”
“勿可以,勿可以,这不是针对侬,是邀角儿的规矩。正式演出之前,侬勿好在公众活动露面,保持神秘感,才能上个好座儿。再讲了,侬初来乍到,人生地勿熟的,万一大义务戏唱砸了,后面这一个月侬自家的戏,啥人还来买票?稳妥为先,稳妥为先啊!这种大义务戏,上海本地角儿当然勿好推托,但侬是刚来,只讲辰光忒匆忙安排不开,谢绝勿去,啥人也勿会怪侬。”
天青沉吟片刻,缓缓开口,声音温和而坚定:
“魏爷,这场戏意义重大,我得去。虽然上海名角儿众多,绝不缺我一个,但这是我作为华夏子民的一份诚心。我会全力以赴,保得这场戏和打炮戏都能唱响,绝不崴泥。我也算是经历过大场面的人,您放心吧。”
“侬,侬介一意孤行额……”魏华彩拼命擦汗,“要是耽误了天蟾的生意,吾倒好讲,四爷勿会放过侬!侬也看着了,四爷的脾性……”
“我看着四爷也是个爱国重义的人。席间听说,去年日本人打上海时,四爷把天蟾关了,改成难民收容所,还免费供给难民衣食,运送回乡,足足撑了两个多月。实实可敬!国难当头,他不会阻拦我奉献一己之力,要不,这样吧,”天青望着紧张得面色发青的魏华彩,微笑一下,“若是大义务戏失手,影响到天蟾打炮戏的营业,我自掏腰包,补足八成以下的差额。”
“此,此话当真?”
“绝无反悔。”
魏华彩用力擦着汗:
“靳老板啊,侬这胆气,吾看也只有阿拉四爷有一拼!……”
静安寺路的爱俪园,是上海最大最著名的私家花园之一,因是犹太富商、“地皮大王”哈同所建,本地人都称它为哈同花园。哈同在前年已经去世,夫人罗迦陵倒还健在,已经七十高龄了。说起来,“爱俪园”这名字,还是因这位夫人而得名呢,她原名罗俪蕤,皈依佛教后,方从佛经取典,易名迦陵。哈同将这座呕心沥血建成的豪华园林取名为“爱俪”,也是一番引人遐思的恋恋之意。
哈同花园占地三百余亩,宏大壮阔,中西合璧,集中了中式、英式、法式、罗马式等各种风格的建筑和园林,从静安寺路大门走来,一路上海棠艇、接叶亭、听风亭、孔雀亭、舍絮桥、串月廊、延秋小榭、飞流界……美景不断,各种奇山怪石、佳木异草炫人眼目。哈同夫妇都好交游,花园建成之后,宾客盈门,留下许多名人踪迹。此次为马占山筹措军费的大义务戏,就假哈同花园内“天演界”大戏台举行。
“岳二爷好!”“给符大爷请安哪。”“高大爷,久仰了!”“杨爷安康!”……
因是慈善活动,票价定得极昂,前来捧场者非富即贵,都是叱咤上海滩的名流。演出阵容更是云集了上海本地名角儿和恰在上海的外地名角儿,前台后台,满眼都是梨园行响当当的人物。像天青这样第一次来上海的后辈,仅见礼就花了老大工夫。这里头还有位老熟人儿,偏偏“戏提调”不知有意还是无意,硬给他俩的戏码安排成了武生和武丑两个人的对儿戏。
“又见面了,江五爷。”天青先抱拳开腔。
江连碧神情极为尴尬。那晚他得蒙天青代为求情,才逃脱一难,虽然始终不甘心向这小子赔礼认错,但这情分总是欠在了心里,如今面面相觑,笑也不是,骂也不是,着实难过。他敷衍地还了一礼,道:
“这出《三岔口》,你是谁的路子?”
“是云二爷的传授。”
“私淑还是亲授?”
“亲授。”
江连碧歪歪嘴:“那就好。我傍着云二爷唱过,路子倒对头,但愿你学得瓷实,台上别出岔儿。就算我想看顾着你,这刀可不长眼。”
天青笑笑:“晚辈一准儿铆上。”
《三岔口》,讲的是杨家将故事:焦赞杀死奸臣后被押解发配,宿于刘利华开设的黑店,大将任堂惠暗中保护,于黑夜中和刘利华发生一场恶战。这出戏的戏眼,就在这“黑夜”二字,虽然戏台上明晃晃的,二人却要演出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生死相搏的险境,开打时的尺寸配合,必须间不容发,戏才好看。天青和江连碧虽是初次合作,但梨园惯例,这种老戏无须排演,直接“台上见”,能不能合作得好,就看两个人平素功力。
乔装改扮逞英豪,只为金兰旧故交!
天青的任堂惠,白缎蓝花罗帽,斜扎褶子,抱衣抱裤,潇洒亮相。虽为江湖好汉打扮,却是领兵大将伪装,既要边式利索,也讲求个工架气度,他的分寸拿捏,恰到好处,全身上下,无一处不透着劲力,登时台下就是一片肥彩。去刘利华的江连碧一身黑衣黑帽,在上场门后头暗暗看着,心下不自禁地铆上了劲儿。
绝不能输给这小子!
他也昂然登场,筋道十足地念出定场诗:
运去生姜不辣,时来铁也开花,
煮熟的兔子会跑,打得的豆腐生芽!
本就是一出好戏,两个角儿又飙上了劲儿,那是分外地精彩绝伦。待到“摸黑起打”一场,台上一黑一白两团身影翻翻滚滚,空手对双刀,单刀对单刀,单刀对空手,空手对空手……一个刚猛矫健,一个灵动轻捷,打得满台生花,水泼不进,之准之稳之紧之狠,都令人赞绝。这等大义务戏,台前幕后全是方家,每个节骨眼儿都情不自禁地给好儿,一时间气氛爆烈,哄燃整个“天演界”。
戏中武丑有个绝活儿,名叫“铁门槛”:右手捏住左脚脚尖,以右腿在左脚脚腕上方跳过,表现的是刘利华被桌子砸到脚,疼痛难忍的滑稽相。这个技巧需要极高的弹跳功夫,好角儿能连跳十来个,必定得好儿。江连碧跟天青较着劲儿,在这样要“死好儿”的地方,刻意炫技,刹那间前跳后跳接连不断,在满堂已经炸窝的情形之下,仍未停止,一口气竟然跳了四十个!如雷般叫好声里,他踩着“崩登仓”的锣鼓点儿稳稳亮相,得意地拿眼梢扫向天青。
天青看在眼里,心下自有掂量。
在北平,白喜祥不许他过分炫技。比如走旋子,天青日常练功,至少连走一百,若是拿到台上,足以独步梨园,但是每次唱戏,白喜祥只准他以五十为限。“这是戏,不是杂耍,技巧再高,不能脱了戏里情境。旋子不过是表示这个人身轻如燕,你走五十个,表示得足够了,再走三百个也不能让这个人飞到天上去。你擅长三起三落、高台倒扑虎,也不能每出戏都来个三起三落倒扑虎,像赵云这样的大将,随便起倒扑虎,成什么话呢!”
北平唱戏都是这样,跟北平人为人处事的风格差不多,讲究个“恰如其分,点到为止”。但是在上海戏台上,完全不同。这次的《三岔口》排在倒第三,前面已经唱过了几出戏,天青认真旁观,只见每个人风格都比北平夸张火爆,无论唱念做打,都极尽渲染之力,在天青看来,多少有些脱离戏情,但是看客显然十分受落,气氛热烈得很。
此际,眼看着江连碧以四十个铁门槛叫板,天青不由得童心大起,一时间技痒难耐。俗话说得好:入乡随俗,既然在上海唱戏,多少也得依着点上海的章法,对吧?
那就来!
锣鼓起,轮到天青走旋子,表现任堂惠于黑暗中机警探看之势。只见他劲透脚尖,腾空而起,又高又飘,又脆又美,连走一圈五个,已然得好儿。走到第五圈,台下叫好不断,走到第十圈,看客全都站起来了,兴奋的吼声直透云霄,只怕连爱俪园外面也能听见:
“……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
江连碧蹲在台侧,不能乱动,眼睛却一霎不霎地斜盯着天青。他自十三岁登台,唱这出《三岔口》已经不下几百场,傍过的成名武生数不胜数,旋子至多走到六十个,大多数在后几圈已经散乱松软,纯为耍玩意儿了,而天青这旋子走的,眼看着走到了七十个,仍然双腿紧绷,“两头翘”,真如一只燕子在高空翱翔,落地始终踏在原来的圈子上,端严规整,一步不乱!望望戏台之下,早已沸腾一片,满座都叫着喊着,帮他一个个数着,一直数到八十整,天青叫起崩登仓锣鼓,落地亮相,正正地踩在他最早起范儿的位置上。
“好!!!——”
天青到底还是记着师父的教诲,没敢过分炫技,走到八十个旋子便收了。但是这一片喝彩啊,已经翻江倒海,几乎把后面的戏都淹没在里边。
完戏了,天青进了下场门,被后台诸多同仁围着猛夸了一番,好不容易回到扮戏房坐下,江连碧又紧跟着过来。天青连忙起身,只见江连碧一双三角眼瞪着他,从头瞪到脚,又从脚瞪到头。天青不知他的来意,一时也没有做声。
憋了老半天,江连碧才开口:
“靳爷!您的人品、戏艺,我都服!”
他一躬到地,作了个通天彻地的大揖,又道:
“大恩不言谢,咱也不说别的了。您那一个月的戏码都排定了吗,请务必让兄弟我傍着您来几出,全是我看家好戏,保证添彩!”
天青连忙还礼:
“多谢江五爷提携,晚辈荣幸之至。”
两人正说着,崔福水满头大汗地挤进来,顾不上跟江连碧多作寒暄,一把拉住天青:
“天青,你猜,天蟾的票子卖得怎么样了?”
天青一扬眉:
“崔爷,你别吓我,昨天那打炮戏已经过八成了,该不会是有退票吧?”
“咳,还退票!你是没看着,刚才这《三岔口》还没唱完,台下那帮行家,已经紧着喊人去抢你天蟾的票子,各家小厮跑来跑去的,我在这行干了一辈子,还真没见过这种境况!”崔福水眉开眼笑,“知道吗,现在头一星期票子已经全部售空,加座都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