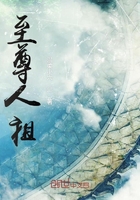丽丽婚前有个男朋友,在小学里教书。他有绘画的才华,在县里是小有名气的画家。他过于贫穷的家庭使他对丽丽的争夺,显得卑微弱小。丽丽是她二哥牵线认识她老公的。丽丽觉得认识这样的男人,是二哥对她的侮辱,“我怎么会嫁给他呢?你不觉得恶心吗?”她对她二哥说。一个没见识太多世面的女孩子,易冲动是正常的;易被引诱也是正常的。她二哥说服了父母,采取迂回、多管齐下的方法。晚睡前,她妈妈就坐在丽丽床沿,说生活的道理:“老徐除了年龄大一些,还有什么不好?他是土冒一些,但这样的男人可靠。他有胃病,这是可以治的,又不是癌症。男人的长相不重要。你想想,小徐会画画,是有才华,我也喜欢他,画画不能当饭吃啊。你再想想,老徐市里有房,他父母有钱,他自己是会计师。你愁什么呢?吃好住好,你这辈子就啥也不缺了。他还答应了,你一过门,就到银行里安排工作。再说啦,他可以提带我们家里。这又什么不好呢?”她妈妈边说还边数落她父亲,说他不知道拍马屁,当了一辈子的乡丁,穷得一家人跟着没出息,弄得四兄妹没一个有工作。说着说着,她妈妈就悲伤地低泣。她不理会妈妈。她骂妈妈。她躲避妈妈。她起先觉得自己很可怜,后来又觉得妈妈可怜。她也抱着妈妈一起哭。她好像不是去嫁人,而是去就义。她的房间里挂满了自己的单色画,铅笔的,毛笔的,水彩的。她一边看一边发呆。她怎么看也看不出画里的人是自己。葵花一样的脸铺满阳光。她把那些画全撕了。
美术师在1994年夏天,辞职到了市里一家广告公司做艺术监制。丽丽做了银行的代办员。但他们像河水冲走的树枝,在同一河岸不同堤段上搁浅。他们没有彼此寻访也没有路遇。她老公一直怀疑丽丽私下与美术师有来往。他的方法是,家里的电话上锁,掌控财务,暗地跟踪。
在王丽丽小孩十岁那年,银行改革,丽丽下岗了。美术师早已是广告公司的老总。美术师一直单身。
在前不久的我们一个老乡乔迁。我和美术师一起喝喜酒。对面的桌子上坐了一个头发有些麻白的女人,有些臃肿,神情木然,不时地看我们。我对美术师说,你认识她吗?他说不认识。又反问我认识吗。我说我也不认识。我不忍说出她的名字。她每天送小孩去学校,经过我家门口。小孩礼貌地叫我老乡舅舅。
同学聚会的时候,我们就取笑东东,说,你追豫惠安别一个人撑着,会哽喉。东东傻乎乎地坏笑,憨厚样,眼睛合成一条隙缝。当然,这是十年前的玩笑,假如是现在,会被人误以为侮辱。我们在考上中师,加试音体美时,正是炎炎夏天。东东一天到晚跟在豫惠安的屁股后,替她拎高跟鞋。鞋是镂空白色的塑料鞋,两根长长的带子。豫惠安赤双脚,沙子灸脚心,走路一歪一歪,绿裙子也在身上游泳一样,荡漾出波涛。她有点扁嘴,瘪瘪的,一条棱角分明的唇线,在面部凸现出来。她是学美声的,她是我班上最早懂得眉目传情的人。在我们的青春时代,她是我们荷尔蒙激活的力量。而暗恋她的,只是东东。但我们都知道,仅仅是暗恋—阴暗、卑微、窃喜、难以言辞的爱,不会有更多的明媚。事情的发展也验证了我们的推想。东东也只能提提鞋子,牵手的手,被另一双手所替代。
我们读普师,豫惠安读艺校。两个学校有三分钟的车程。在第二个学年,豫惠安的美貌,已在两校声名鹊起。她身材高挑,她野性的美像一团包不住的火焰。星期天,或假日,在市区的广场、主街道、商业区的大型商场里,我们经常看见豫惠安站在临时搭建的舞台上演出。这是普通的商业演出,一天三十块钱。豫惠安烫了鸡窝一样的头发,束得高高,她穿各式各样的衣服,有塑料皮似的,有帆布似的,唯一不变的是,眼眶和唇涂得黑黑。放了学,有人开小车到校门口,接她放学。她很少找我们玩,可能是没时间,也可能是我们根本就是两个时代的人。一个女同学说,豫惠安已经堕胎好几次了。豫惠安脸上那种失血的白,直到毕业也没褪去,那是她青春的标签。
学业的终点是我们都回到小镇。1989年夏,我们像一群山羊,被赶到了不同的山坡上。豫惠安在一个僻远的小学教书。现在回头细想,豫惠安的心情是极其沮丧的,骑一辆自行车,来回三十华里路,确实不是一个唱美声的人走的,中午的饭还没着落,生活的难度比高音更高,而我们习以为常。不到半年,她找了一个个体户做男朋友,并很快完婚。她的老公骑辆摩托,嘉陵牌的,载着她上下班。她老公是个很英俊的人,只是文化太低,只读了小学。当然,这没有影响她幸福的感觉—她的结婚旅游是串门,走完了艺校班上每一个同学的家。
1993年,沿海的城市,尤其是福建沿海城市,刮起了乐队之风,地下的演艺人像赶潮的虾,汇集到各个舞厅。舞厅由乐队支撑,一个领队、一个电子琴手、一个鼓手、一个吉他手、几个歌手。歌手是流动的,竞争非常激烈。领队决定了歌手的地位和收入。舞厅是免门票的,收入靠点歌,与乐队分成。歌手在台上唱歌,台下送花篮,花篮里包个红包。红包是空的,是一张填好金额的单子。按单结账。舞厅间的竞争处于白热化,领队拿出各自的招数,吸引客人。招数无非是边唱边脱,边唱边坐在客人的腿上调情。一个好的歌手,能使点歌人争风吃醋,掏空客人的口袋。客人出了门,经常骑自行车回家,连坐车的钱都没有。豫惠安也去了,停薪留职。一年后,小镇里传出豫惠安被人包养的消息。她还和领队,鼓手,有说不清的东西。她老公听之任之。1995年,豫惠安回到小镇,盖了全镇最高的洋房。豫惠安也落了个“银行”的外号。
小镇的寂寞,终究留不住属于繁华红尘的人。大量的砍伐木头,山上的资源已近枯竭。小镇的舞厅再也经营不了,成了镇政府的内部招待所。柏油路由于超载超重的碾压,坑坑洼洼,陌生的师傅常常把车开进窟窿里。
1999年夏天,我去深圳度假,到南山的南街玩。从南山的天桥,右下,进一个拱门,就到了南街。南街通用的语言是我的家乡话。我以为是我家的门口—米粉铺,案边摆一个筒骨汤的铝锅;榨花生油的,门面漆黑,粉油的脸;站在路口卖麻花的,用家乡话吆喝。我的朋友说,南街有六千上饶人,从事贩卖盗版书的生意。我的朋友在部队当过侦察兵,来深圳有六年了。我对贩书的事不陌生,我的表哥像候鸟一样,居住在深圳,寒暑假就回家。我表哥只读了初一,每年拎几十万回家。我朋友和一对夫妻合住一套房子,当晚,我在深夜的时候,听到夫妻打架。声音是从床板、墙壁、地上发出的,身子和头部撞击的闷响。我朋友辗转反侧,低低短叹。我朋友说,那女的是他情人,她老公是这两天来的。我说,她老公怎么知道?“我中午坐在沙发上,和她接吻,被他买酱油回来的丈夫撞见了。真是难堪。”我朋友笑了起来。第二天,我们一起吃早餐,有说有笑,仿佛什么也没发生。那天,我才知道,那个女的,就叫李海华。
住了两天,我一眼就能辨认出贩卖书的人—头发光洁,穿白衬衫、结领带,皮鞋油滑,戴眼镜(大部分人是平光镜,伪装成知识分子),拎一个真皮包,这是男人;口红,细眉,露出胸沟的吊带裙,高跟鞋,斜挎包,这是女人。包里的“暗器”是现金、假名片、假公章、假文件,一本深圳市领导干部的电话号码、地图、书籍价格表、书籍分类表。早上八点,深南大道的南山街口,拥挤着这些人。男的拉个推车,车上堆着书,神态仿佛出征。他们是成双成对出去的,在路上定下目标人物,到了目标人物楼下,男的负责打电话:“××经理,你好。我是××领导的秘书。我的同学是××图书公司的经理,要销××书,符合××精神。她带了样书和文件。你关照关照。”现金和美女是公关的“定时炸弹”。
在这里看见李海华,我非常吃惊。我的表情几乎是僵硬的。以前她是个裁缝,在中学的门口,开个小店,带几个徒弟,男徒弟一般是残疾,女徒弟一般是贫家女子,学三五个月,就去浙江打工。但我没见过李海华。我只知道她老公是个中学教师,喜欢打麻将。在乡村,男教师大都是这样的—娶女裁缝,或娶开店的,有点姿色,有生活来源,种几畦菜,生活就算美满了。李海华老公姓赵,个头不高,文弱白净,能烧一手好菜。我朋友和他夫妇组成了临时之家。李海华是个不怎么说话的人—她的眼睛会说话,脸上保持着微笑,两个酒窝漾出水来。她白而长的脸开在颈脖上,像一朵百合花。而到了宴席和舞厅里,她成了另一类人。她会劝酒,有攻击力,也善饮,粘人。她要跳疯狂的舞蹈,还吃摇头丸。
她知道怎样引发男人的注意乃至情情相吸,怎样保持对方常胜不衰的欲望兴趣,有了更多的技术和手段,知道其中的妙处和潜力,她会变得越来越讨人喜欢,怎样把自己装扮已成为她生活艺术的一部分。
她的胆量是过人的,在她老公严加看守下,他们仍然交往过密,在中午休息时,到宾馆开房间。“其实,也没什么奇怪的。我们是共同体。她是我的武器。做单子,要送礼,有人不要钱,那么她成了奉献给别人的盛宴。我们都习惯了。我出钱,她出身体,很少有人能抵挡的。利润五五分。”我朋友并不忌讳地说,“这是生活的核心。”
离开深圳后,我再也没看过她。她老公我倒遇见几次,他说,他们还在卖书,在深圳买了房,买了车,全家都迁了。他的语气充满了自豪。我朋友前两年离开了卖书的行业,去做了补屋漏。因为深圳一直在打击地下书贩子,抓了许多人,有的罚款有的判刑,还有的被保安打成残废,聪明的书贩子突围出深圳,往中山、顺德、佛山、湛江发展。前两天,我朋友给我电话拜年,我们聊了很长时间。他说了他最近的几次艳遇,也说到了李海华。“噢,李海华,她包养了一个小白脸。她这辈子够了。”电话喷出不屑和讥讽的唾沫。
我已很少回到小镇,一年也只有一两次,逢年过节走走。十年内,小镇大了一倍,像个马蜂窝。小镇成了老人和小孩的世界。只有到了过年,街上才散布着年轻人倦怠的影子和豁亮的面容。他们和她们,我都不认得了,每年看到的各不同。我确信,人不是一个一个长大的,而是一茬一茬。有一部分人在消失,有一部分人在彰显,他(她)们是小镇的两面体—背阴的墙体和朝阳的门楣。他(她)们构成了小镇的白天与黑夜,秘密与传说。
我大部分的同学和年少时的朋友,都搬迁到了城里生活。他们在城里买房,在乡下上班,有的干脆辞职,做生意。与我而言,小镇是个空巢。我想,没有四大美女的小镇也是寂寞的。
四大美人,是一个古典的称谓。小镇当年的评选,多多少少有点缺乏创意。而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现在小镇的年轻人,很少知道她们。她们的青春时代已经结束,她们被猛烈的大风刮走,她们飘落的羽毛成为风中的传说。努力追寻的东西在消失,这是时代的必然,即使伤感也是多余的,即使错误也是无辜的。这两年,通往小镇的公路变得宽阔,水泥的反光有些刺眼,与翠绿的山冈、葱油的田地,显得格格不入,它倒是与通讯塔、污染的河流、广告牌,组成了现代生活的基本元素。
美人。一个令人怦然心动的名词。一匹被美压迫的骏马。一片绽放与凋谢同时进行的时光显影。我们目睹的美人,多么不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