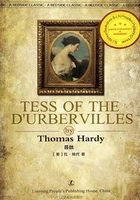—纯虚构文本
前几天,一个北方的朋友问我:“听说你的小镇上,有四大美女?”我说,是啊,其中一个还是我同学呢!没想到她们名气那么远播。不过,她们已经是日暮美人。“这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小镇。”朋友说,“让我向往。”
小镇在一个山坳,犹如在老虎的口腔里。“哦,那是小香港。”当地人向外地人介绍小镇时,会这样脱口而出。当然,这是在1990年前后。也是四大美女的黄金时期。与现在破败不堪、拥挤、嘈杂的景象不同,那时是安然、呼啸、神秘,还有膨胀、质感、柔软。仿佛是一个不愿醒来的梦,一个在长长走廊里漆黑处的转身,一个慢慢扑下的影子。
我在乡间的时候,经常去小镇玩。它离我家六华里。我吃了晚饭,一边散步,一边慢慢打开夜幕降临的景色—我去小镇,确实是想得到某种微妙的弥补。植物的气息和氤氲的最后一缕霞色,多多少少让人有些感怀。小镇呈“丁”字形,处于德兴至上饶的中间地带。主街上有酒家、邮电所、小门诊、美容美发厅、商铺。酒店一般是上下两层,楼上住宿,楼下吃饭,后院是厨房,养着鸡鸭,横杆上挂着熏好的野兔、山鸡、腊肉,前门悬着两个红灯笼,烛光耀耀,门口站着穿红衣服的迎宾女孩。名气较大的酒家有“姐妹酒家”、“夜来香客栈”、“车友之家”。美容美发厅的门楣上有闪烁的霓虹灯,角落里的旧沙发上坐着面容绽放的女人,黄色的卷发、厚厚的口红、长长的指甲上涂了银色的油,玻璃案几上放着零乱的梳子、脸膏、洗头剂。市里、县城、邻近的乡镇,到了晚上,就有一批批的人来小镇。他们是来跳舞的—美女会产生巨大的磁场,他们是铁屑。舞厅在镇招待所三楼,靠墙的两边摆了木长凳,里间是茶座,大厅顶上旋转着两个激光灯。门票一块钱一张。
你们都知道,舞厅是美女的集散地,小镇舞厅也不例外。舞厅对你的回报就是让你尽情地欣赏四大美女旋风一样的身姿。舞厅—青春期的第一个码头,窄小的空间有着另一种辽阔,热情、单纯、妍然,在小镇上,它还是情感的孵化器。而“四大美女”的名号,并不是从舞厅中产生的,而源于一次聚会。舞厅仅仅是,唯一可以集中她们的地方,我想,这是可以理解的—美女的神秘色彩具有蛊的力量。这是一次非常有意思的聚会。1989年8月,小镇搞了大规模的文艺会演。汇演结束,四十多个年轻人在一个林业招待所聚会。可以说,他们是小镇的精英,有教师、乡干部、银行职员、社会上文艺活跃分子、初有创业成绩的企业主。他们觉得小镇美女太多,必须有个座次,名额不能过多,就评四个,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他们没想到,他们仅仅为了度过一个寂寞夜晚的噱头,给小镇带来生趣和活力。
四大美女是王丽丽、裘榛榛、李海华、豫惠安。豫惠安是我同学,李海华是我不认识的。现在想来,她们的桂冠是不是改变了她们的人生,不敢说,有一点可以肯定,她们的梦想从她们成为焦点开始。
小镇的酒家以“姐妹酒家”最出名,不仅菜烧得好,更主要是由裘榛榛家开的。小镇离县城五十公里,盛产木头。每年的雨季结束,临近省份和周边县市的木材商贩,汇集到镇里。他们带来了饮食业的繁荣。他们是一些口音粗重的人,大把地花钱。裘榛榛二十出头,含苞待放。她只有初中毕业—在小镇,是一个让人自卑的学历,但是谁会责怪一个美人的学历呢?我们在她的脸上看到的是向往、孤决、明亮。这点可以从她花萼一样耸立的鼻子和微微仰望的姿势,得到证实。她通常会坐在门口度过下午眩晕的光阴。厅里坐满了烫黄发露出胸脯的混混、没安排课的教师、等车的人、结束了谈判还没打算回家的商贩。过往的客车、货车,会停下来,客人喝口茶聊几句,又走了。她穿一件白色的风衣、短靴,长长的头发盘成一个花冠。她的眼睛有些迷蒙,有梦寐的假象—她凭此获得高票。这种优势在酒店里,淋漓尽致地得到了发挥。镇政府定点餐店。客车定点餐店。我们去镇里,也会安排在她那儿吃饭。裘榛榛酒量惊人,她坐在你身边,像个盛情的东道主,她能够把整个宴席的气氛调得喜宴一样热烈。这种才华不是仅仅靠锻炼就可以获得的,还需要天赋。
1992年的秋天,我回老家探望亲友,同学少兵告诉我,裘榛榛被人打了,躺在医院里。同学是以当年小镇头号新闻的语气,叙述的。前两天,五六个外地妇女,到“姐妹酒家”门口,突然冲进去,按住裘榛榛,暴打一阵。边打边骂:“你这个狐狸精,勾引我老公,不就是贪图他的钱?打死你的烂×。”裘榛榛既没挣扎也没哭。她仿佛意料到事件的发生。她的口腔里流出许多血丝,眼睛淤肿,散乱的头发粘满脚印的灰尘。边上的人还没缓过神,外地妇女坐上雇来的小中巴,跑了。后来镇里四处传言,裘榛榛不止和一个木头商贩相好,并且镇里的头面人物、县里某领导,都是她的座上宾。暗地里,大家叫她“破鞋”。这对她的名誉确实是个摧毁,而她的生意不但没有败落反而越来越跑火。
而让人瞠目结舌的是,时隔一年,裘榛榛嫁给了她的厨师。厨师姓范,是我同学的哥哥。他是个敦实黝黑剃个平头的小伙子。他不爱说话。他是个非常优秀的厨师,里里外外打理得干干净净。在小镇,这样的结合,也许是最佳拍档。
去年5月,我的一个朋友对我说,在国道边上,有一家“范氏酒家”能烧一手好吃的家常菜,价格便宜,分量足,可以去吃吃。我对生活是没什么要求的人,而美食确实能吊起我的兴致。毫无例外的,又是我去厨房点菜。厨师正在切牛肉,我一看就叫出声:“老范?!你以前不是在解放路开湘菜馆的么?怎么到这里开小店呢。”“那是以前的事了。我前年离婚。现在的老婆是市里的。裘榛榛做房产去了。”老范说,“我已经四年没看过你啦。”那次晚餐,我独自边吃边暗笑。时光逆流而上,不经意间,与我在秘密的记忆里汇合。流离的,伤感的,温软的。
前半年,市里逮出一条“硕鼠”,某高层领导贪污了二百七十多万,包养了三个情妇,还与五个女人有染,其中一个是某县里的女领导、一个是女房产商。女领导已经被解职。女房产商被逮进了检察院,不过只关了一个星期,以偷税的名义罚了八十万,放了。她转手了房产,席卷两千多万的资产,去上海发展。她就是小镇上的头号美女裘榛榛。
在1992年,小镇走得缓慢而湍急,它沿另一条河床进入洪流。你也许以为小镇温暖、繁华、纯粹,你也许以为你永远不会离开小镇。我们还没有感觉到春风,而山悄然绿了。春风是潜伏而来的,带来惶惑、迷乱、惊喜。那年初,小镇大部分的年轻人外出打工了。这在以前是没有的。街上突然像潮后的海滩,裸露出原本属于它的属性:商品静静地躺在棚里,卖水果的妇女打瞌睡时拉丝的口水,孤立的电线杆在一团线的缠绕中发呆,浑身“嗓嗓嗓”响的自行车,小孩在跳绳时唱的“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悠长儿歌。这个年份以王丽丽的出嫁为落幕。一个喜庆的彩头却有一丝悲凉。悲凉是难以察觉的,像心里渐渐熄灭的火。王丽丽戴着花帽,火焰一样的披风裹着她在席间飘忽。大家都叫她黑珍珠,而今晚俨然是美人蕉。她的眼里始终有滚圆的东西在滑动,但一直不落下来。她仿佛沉溺于婚宴的长久的感动之中,事实上,那是对命运的怨恨。
酒宴上,客人私下说,丽丽怎么嫁给那样一个男人?丽丽是闪电结婚的。她的老公是市里一家银行的会计师,比丽丽大十二岁,但他一点也不像城市人。他常年患胃病,佝偻着身子,他厌弃似的不去打理头发,蓬乱,油粘。他结婚那天还穿一套皱皱的西服。大家都说,丽丽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而丽丽的家人不这样认为,尤其是她的二哥。她二哥是个小生意人,他说,家族里应该有一个在银行里干活。离开银行谁能致富?丽丽是邮电所的临时工,负责柜台上的事务。工作并不忙,她有时间看看时尚杂志,对着镜子照照发型,偶尔还溜到街上做面膜。因为是临时工,她工作比别人卖力,人缘也好,在外打工的人也常常通过她的电话,把生活的境况和琐事,转告家里。她结婚的宴席上,邻居特别多—充满感激之情的邻居知道,丽丽完婚后,就要离开小镇,去银行上班,他们既感怀又惜别。而更多的人知道,这样的婚姻不会维持太久。
这些人都错了。事实上,丽丽直到现在也没离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