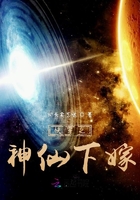看着钱芳耳朵上那只摇晃的耳环,我不由得浑身颤抖。原来安白要报复的下一个对象,就是钱芳!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并不知道钱芳也和杀害安白有关,因为在几次的事故中,直接参与的成员中都没有钱芳出现。
我迅速环视了一下整个客厅,因为我觉得安白此时此刻也许就躲在桌子下面、冰箱后面,或者衣架后面,凝视着我们、聆听着我们。我想到,如果钱芳真的是安白的下一个目标,那么她随时都会面临死亡,不管是突发的、还是离奇的,甚至是惨烈的,都有可能在下一秒钟发生。于是我急忙问她:“关于安白的事,你都知道些什么?告诉我们吧。说实话,我现在也在寻找一些线索,想解开这个谜。”钱芳低着头,缓缓地从左摇到右,从右摇到左,然后声音低低地说:“我……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这件事太可怕了……”我和岩峰对视了一眼,他的脸很紧绷,嘴唇抿得更薄了,这是他正在全神贯注思考的表现。我说:“钱芳,你现在不要有什么顾虑了,张晓斌和胡伟鑫都死了,而且无论从哪一个事件来看,他们的死都和安白有关系,不然也不会出现口罩……”我刚说到这里,钱芳“哇”地大叫起来,把我吓了一跳,她双手捂着耳朵,把头深深地往膝盖里埋,带着哭腔说:“别说这个词!别说!”我能看得出,她的身子抖得厉害,弓起来的后背又瘦又扁。我无奈地看看岩峰,他沉默地看着钱芳,冷峻的面孔上,读不出任何表情,他没有我那么急切,也不像我那么喜形于色、怒形于色,他注视着钱芳,彷佛在用视线扫描她的整个内心世界。
“钱芳,我们这里刚刚发生了一件事”,岩峰开口说话了,钱芳身体一震,彷佛刚刚意识到岩峰的存在似的,吃惊地瞪着眼睛盯着他,岩峰继续说,“安白接下来很有可能会去找你。”钱芳听到这,“啊”的一声没有从她的嗓子眼里放出来,倒被她吸进去了,发出被人突然勒住脖子的声音。“如果你告诉我们你知道的真相,我们就可以解开这个谜题,帮助你不被安白打搅。”岩峰的声音连一点抑扬顿挫都没有,像念播音稿的主持人一样不带任何感情色彩,他冰冷的声音在客厅的四壁上碰撞,犹如玻璃杯中的冰块。
看到钱芳的意志在一瞬间动摇了,我乘胜出击,在钱芳面前摊开手心,看到耳环的一霎,钱芳彻底崩溃了。她双手捂着脸,“呜呜”地大哭起来,我把纸巾盒放到她面前,心里放心了一些,钱芳的最后防线已经垮了,接下来她很快就会说出她知道的真相,也许安白之死的谜底今天晚上就可以揭晓了!我看了看岩峰,他的表情却始终紧绷,甚至比刚才还要严肃,甚至在他的眉宇之间,微微隆起了一个小包。我想用眼神问他:“为什么还这么紧张?还有什么事吗?”但岩峰就是不看我,他皱眉相当于一般人狂怒或者极痛、或者极悲的表情。我以前总是开玩笑说他是不是缺少面部表情的神经,估计就算中了百万元的大奖他也不会动一个嘴角的。他只有在两种时刻才会让我看到他丰富的表情,一种是他生病的时候,一种是睡觉的时候。
在应该感到放心和踏实的时候,岩峰却皱起了眉毛,这让我比晚上见到安白还要震惊。
钱芳哭个没完没了,拿着纸巾不停地擦啊擦啊,嘴里嘟囔着什么,但是一个字都听不清。我有点着急了,叫了钱芳几声,她不知是没听见还是不想听,还是在那自顾自地哭着,我又往岩峰拿看去,岩峰却也不理我,还是一直盯着钱芳,眉头却皱得更紧了,我焦急不安地坐不住了,刚想伸手把钱芳安定下来,手机突然响了,我拿起手机站起来,走到大门附近按了接听键。
“喂?”
“喂!是黎月吗?我是周军武,岩峰在你那吗?我给他打手机打不通。”
“哦,可能我这里信号不稳定,”周军武是我的初中同学,算是班上还算能谈得来的男生,也是岩峰朋友,“有什么事吗?”
“你告诉岩峰,明天早上来钱芳家一趟,钱芳今天晚上出车祸死了……”周军武还在说着什么,但是我什么都听不清了。
钱芳……死了……?车祸……今晚……
那么,现在坐在我家沙发上的这个人是谁呢?
不、不……也许,它根本就不是人……
我僵硬地转过身子,钱芳还在低着头擦着脸,但是已经不哭了。岩峰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从沙发上站起来了,就在我旁边。我凑在岩峰的耳边轻轻说道:“周军武打电话说……钱芳今天晚上……出车祸死了……”岩峰并没有露出惊讶的神情,他点了点头,小声说:“我已经知道了。”还没等我问,他指了指钱芳,说:“你看,她没有影子。”
一股恶寒爬遍了我的全身,在白色的灯光之中,钱芳的身边和脚边没有任何阴影,她低垂的头下方,也没有投影。她就像一个透明的魂魄、或者逼真的影像,静静地坐在那里。“现在怎么办?”我问,浑身止不住地打哆嗦,就这么短短的几分钟,我家的气温好像骤降了40度。“不知道,你看她的衣服。”岩峰说。我再一看,差点哭出来——在黑色皮夹克的里面,露着鲜红鲜红的衬衣,一双同样鲜红的高跟鞋里装着她骨瘦嶙峋的脚。“我们试着往外走走,不行的话再说。”岩峰慢慢往后移动着步子,伸着一只手虚掩着我,我也应他的话往后退。
忽然,钱芳站起来了,她的后背像被插了一块铁板,笔直得让人恶心。“你们去哪儿?”她说,声音幽幽的,从她低垂的脑袋下面发出来,这声音和刚才的声音截然不同,刚才的声音是正常人的声音,现在的声音是病入膏肓的病人快要断气时的声音。她停顿了一下,似乎在等待我们的答复,见我们没有回应,她耷拉着肩膀,双臂在她的身旁晃动着,像系在肩膀两端的香肠,一步一晃地朝我们走过来。如果没有岩峰在前面,我可能早就瘫倒了,钱芳鲜红的衬衣现在大片地从没有系扣的皮衣中露出来,我脑子里有一个声音在说:“那是被血染红的白衬衣!”车祸!车祸!死亡!死亡!这四个字眼像从天而降的暴雨一样降落在我的脑海里,在我们眼前的这个人,不是活人,是一个在几小时前死于一场车祸的死人!
“哇!”钱芳脑袋一晃,吐出一大滩血在地板上,血顺着地板缝迅速流动。她又走了几步,“哇!”又一下,吐出了更多的血,这一次,血里带着很多的血块,变得比刚才浓稠了许多。她没有停步,高跟鞋踩在新吐的血泊里,发出细小的撕裂声和液体声,一股浓浓的腥味儿扑鼻而来,我捂住嘴巴,强忍着反胃的感觉。钱芳此时已经离我们很近了,我们也已经退到了门边,再也无路可退了,这时候,她慢慢地抬起头——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只剩下半张脸的钱芳,左边的脸几乎连骨头都变形了,只是软绵绵地耷拉着,眉毛、眼睛、鼻子、嘴,已经像大拌菜一样混在一起,分不清了。剩下的半张脸,已经完全被血迹覆盖,只有右耳的耳环还在闪闪发亮,而左边的耳环,则在我的睡衣兜里。
安白早就计划好了怎么制造这起车祸、甚至都考虑到了方向和强度,她在发生事故之前神不知鬼不觉地取下钱芳的左耳耳环,也许就在下一秒钟,一辆急速行驶的大型货车就狠狠地撞瘪了钱芳的驾驶室。
“钱芳……你现在想说也可以的,”岩峰的声音响起来,他的脸侧面线条是那么工整平滑,就像被雕刻家精心雕刻过的雕像一样。
钱芳停住步子了,她右边脸的眼珠转了转,白色的眼球是这血红的半张脸上唯一不同的色彩。
“你告诉我安白被害的线索,我们揭开真相之后,可以帮助其他人幸免于难,也可以为你伸冤。”岩峰继续说道,别看他平常话不多,但是忽悠人的本事他比我强多了。
钱芳低下头,嘴里含糊不清地咕哝着一些话,我必须竖起耳朵听才能挺清楚:“安白……被害那天……我……也在……可是……有人……逼我们……”说到这里,钱芳突然痛苦地惨叫起来,她张着嘴,但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跟瓶盖大小差不多的窟窿,冲着天花板哭喊着,接着,我睁大了眼睛,看到她的肚子正在迅速地膨胀,衬衫的扣子一个个地崩飞,有一个弹到了我的肩膀。就在我还没来得及“啊!”地尖叫时,岩峰回身一把抱住我,和我一起面朝着大门蹲在地上。紧接着,一声气球爆炸时的“嘣!”的声音响起来,只不过没有气球那么清脆,而是比较闷和厚重,然后是钱芳“噗通!”倒在地上的声音。岩峰和我蹲了一会儿,再没听到什么声音之后,他起身走回客厅,在地板上发出不流畅的脚步声——他在捡可以下脚的地方。我却始终不敢回头,也不敢站起来,那“嘣”的一下,一定是钱芳的肚子爆炸的声音,我听到很多的液体和东西掉在地板上的声音,那些想都不用想,是大量的血液和内脏……我不敢面对这一切,也不敢面对倒在地上,只剩下半边脸的钱芳那大敞四开的腹腔。
真希望这一切都是梦。
每次梦见难以处理的情况,正在发愁的时候,突然醒来,看到一切还依旧在照常运行,心中顿时放松和欣慰的感受真是美妙极了。
闭上眼睛,然后数“一、二、三”,我就会醒来,地板上没有血迹、没有内脏、没有钱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