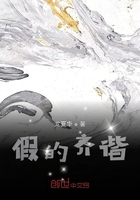对于朱雀街上发生的一幕,斜对面茶馆的二楼,有人坐在窗边,将事情从头到尾尽收眼底。待那辆黑色马车去得远了,临窗的那人长长一叹,语气颇为忧虑。
“映月此去,但愿不会受苦才好。”
另一个人靠在窗边,望着那辆远去的马车,直到再看不见才收回视线,咂吧着嘴,很是向往地感慨:“那马车里的不知是什么人,可真威风。”尔后转过头问,“半月,你知道那是什么人吗?”
那端坐着的白衣少女,可不正是进京救父的李半月,那少年除了冷木溪外还有谁。除他二人,房子里还有两个人,一个瘦长马脸的是成六,一个却是相貌平凡的男子,听到冷木溪问,皆望向了李半月。
李半月不慌不忙地端起桌上茶杯,轻抿了一口,并不放下,以茶盖刮去漂浮其上的茶沫,忽而动作顿住,眼帘低垂,眸色转沉,低声道:“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人,但或许能够猜到他是什么人。”
“啊,那你猜的是谁?”冷木溪瞪大双目,他本是随意一问,半月跟他一样才来的京城,又都是第一次来,怎么会认得这京城里的人呢?
李半月放下茶杯,声音低沉,慢慢吐露出五个字:“当朝摄政王。”
屋里另外几人同声色变,即便是冷木溪这样常年窝在山上做强盗的人,对于这个人的名头也是有所耳闻的——不,应该说是如雷贯耳。
当朝摄政王,这是一个人的头衔,更是整个大夏皇朝的符号!
穆秋,字天传,大夏国摄政王爷,当今天子的嫡亲叔叔,帝称之——叔皇。
说起这位皇叔,那真是权倾朝野,手段通天,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煊赫到极点的人物。论身份,他是先皇的同胞弟弟,是当今皇帝唯一的亲叔叔,大夏朝硕果仅存的正牌王爷;论功绩,十三岁时于宫变之际临危受命,将乱党诛灭保住其兄宝座;十八岁被先皇托孤,扶持年仅五岁的侄儿登上帝位,其后数年,诛逆党,选贤能,镇叛乱,正朝纲。
摄政七年之久,如今二十五岁的摄政王爷,因其尊崇身份,因其整顿朝纲时的雷霆冷酷与镇压乱党时的铁血手段,无论是当朝权贵还是民间百姓,对其都是畏如猛虎,敬若天神,望之可畏可惧,不敢亲近。而他帐下的将士,早年随着他南征北战,破敌无数,从无败迹,立下赫赫战功,对他的敬畏忠诚绝非外人可知,可感,可能体会。因而他们对他的称呼,不是代表至高身份权柄的摄政王爷,却是从一而终永不更改的军中旧称:将军——既表敬服之心,又示亲近之意。
他是当朝摄政王,更是大夏国所有军人心目中的将军!
冷木溪张着嘴,半天才合拢来,轻轻喊了一声,“原来是那个人啊。”
四人中,相貌平凡,也是年纪最大的人眉头一皱,沉声道:“少当家,如今映月姑娘和郑太成被带到京兆府,白原兄弟的事情已如你所计划的一样,在京城传了开来,那我们下一步要怎么做?”
李半月白他一眼,口气略为不善地说道:“大街边上的,你少当家少当家的叫,就怕别人不知道我们是做什么的吗?”
冷木溪忍住笑,他知道半月和小独向来喜欢欺负老实人,他已经被欺负的没有新鲜感了,现在好不容易遇到个比他还老实的人,半月若不欺负欺负,那她就不是半月了。
被李半月抢白一阵,他却没有丝毫恼色,反是再正经不过地点点头,“少当家教训的是,那请问少当家,赵平该如何称呼?”
李半月以手扶额,一声唉叹,这个赵平也是出自虎啸寨,怎么来了京城好些年,说话还是一本正经的,没有学会京城人半点变通呢。
“其实这可怪不得赵大哥,二小姐你一个女孩儿家出门在外,多有不便,又不像大小姐一样有武艺傍身。若二小姐变装,做男装打扮,我们称一声公子,那倒方便许多。”成六可算从小看着李半月长大,虽称小姐,实半月就像他的侄女一般,因而说话时少了几分尊卑亲疏,却更多出一些亲近之意来,偶尔还能开开玩笑。
“是啊,是啊,就像小说里写的,女扮男装,不是很好玩嘛。”冷木溪乐呵呵的点头附和。
“好玩,那你来个男扮女装试试。”李半月闲闲一句,顿时让冷木溪闭了嘴,成六在旁边偷偷的幸灾乐祸。成六毕竟是长辈,李半月假装没看见。
其实,她是不喜扮装,好好的,男女从出生时便已注定,为什么要为了方便就要女扮男装?女孩儿怎么了,女孩儿就不能堂堂正正地在外边行走了?非是她自大不屑妥协,而是认为,既然上天给人安排了男女之别,总有其存在的必要,而人,为什么要和老天过不去,单单换一身衣着就想瞒过世人,欺天之眼。这不是很可笑吗?
非关性别,如果本身强大,别人自不敢来招惹,若身属弱小之流,遮掩一时,到头来一经识破,岂不更自取其辱?
“怎么称呼都行,叫我半月也行,只要我们别再在这个问题上浪费时间就好。”李半月微微一叹,回归正题,“我没想到今天会遇上摄政王,这样也好,大长公主乃当今天子的姑姑,也唯有皇上的叔叔才能与之相抗衡。先不管这两人是否敌对,既然摄政王插手将事情交给京兆府尹,那阿爹的事情便有了转机。”
说到正事冷木溪也没心情再开玩笑,忧虑道:“可是大伯已经被他们判了死刑,如今还不剩下一个月,可大伯人被关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
“放心,他们既然判刑于阿爹,走明正典刑的路子,那么阿爹倒还有一线希望。如今转机出现,只要好好把握时机,我们未必不能从大长公主手里救出阿爹。”
“那,白原大哥呢?”
李半月一顿,语气略为黯淡下去,“我们来京十多天,只能得阿爹片字消息,而白原大哥却音信全无,只怕——已经凶多吉少。”
屋中之人闻言垂首,一时都没有言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