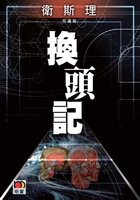原来,张文炳姑侄二人在密室相商时,已有人潜伏房上,窃听多时,当窃听者听到吴友仁活剐熊文弼一节时,不禁猛吃一惊,失手踹下几块屋瓦,一下惊动了张府中人。窃听者何人?不是别个,乃是潜入张府来寻妻的亡命之徒傅德错愕。那夜,月色朦胧,加之他轻捷如飞,众人还来不及看清窃贼为谁,他已逃之夭夭了。
傅德错愕来到重庆府已有多日,他整日戴着一顶竹笠儿,把帽檐拉下,深深地盖住了眉棱。这儿的市井小巷他是熟悉的,而今,城头变换了大王旗,昔日官宦人家的府第,现在已换了主人,高高围墙里面的深深庭院,住着的是红巾的新贵。酒楼茶肆依然热闹,城门外的水码头依然樯桅如林,那嘉陵江平静的江心中,依然停泊着那艘偎红舫。这些日子,他潜入张府窥探已经好几次了,可半点卜朵儿花的影子都不见,这天夜里,他又潜回偎红画舫,这儿,有他的红颜知己兀赛儿在候着他呢。
“傅大官人无忧,嫂夫人曾来过画舫,是红儿送她去张府的。现在怎么说没影就没影了呢?”这位碧眼艺伎不由得也诧异。她回忆着说,半年前卜朵儿花乔装成一个小厮,只身一人搭小划子登上她的画舫的。卜朵儿花说,她一日不在思念夫君,华蓥山的尼庵太冷清,得不到一点外面的消息,她实在憋闷,于是就来重庆,先找到偎红舫,求画舫上的姊妹先打通张府的关节,张府夫人杨氏动了恻隐之心,才同意接她去府上暂住的。
“红儿现在哪里?”傅德错愕抓住线索,想顺藤摸瓜理下去。
“你急什么?先喝盏薄酒暖暖身子,歇宿一宵养养精神,我明日再告诉你。”这色目艺姐以呵护的口气,安排了远客的安寝。第二天,她告知远客,红儿不在画舫,红儿送卜朵儿花去张府后,就留在了张府伺候杨氏夫人。
昔日重庆义兵的都虞候今日已是江湖独行侠,他在兀赛儿的锦帐中做了一夜的温柔梦,又携上他的屠龙剑,匆匆赶去张府。
张文炳是红巾新贵,张府即是被诛的元朝右丞完者都的旧府邸。傅德错愕过去随鲍二爷鲍玉常来此公家中做客,算是熟门熟路了。是夜,傅德错愕再次潜入院内,他在暗处左右绕行,对那些房舍闺阁,山亭水榭,乃至幽篁茂树,又梳理了一次,仍没发现异样。杨氏夫人的寝房,丫环环立,有焚香的,有端茶的,有递漱口水的,但进进出出的侍儿中,却不见红儿。难道红儿忙碌一天,累了,已回房歇息了?红儿的寝处又在哪儿呢?傅德错愕在院内又转了几圈,墙外传来了更夫的梆声,已经是二更时分了,远处有窗户还亮着灯火,他悄悄地梭过去,哦,原来这是张文炳的书房。这佬儿,斜倚在卧榻的靠背上,还拿着一本什么书在观览。“昔日我义父杨汉说张文炳饱读诗书,夸妹夫是军中智囊。看来他这个秉烛夜读的习惯还未改。”傅德错愕不知是欣赏或是嘲讽,他暗自嘀咕一句,正欲转身离去,忽听得文炳唤道:
“红儿,续香!”
哦,红儿原来在这里,她是伺候老爷的添香红袖!
但房内没有回应。文炳掷书于床头,无奈地叹道:“这个风骚丫环,今夜又幽会情人去了。”他边说边起身,给屋角的香炉续上香,不觉疲倦地打了几个哈欠,顺手将书卷移放到几案上,接着便熄烛入睡了。
幽会?红儿会到哪儿去幽会呢?偌大一个院落,这夜深人静的时候——哦,那死鬼鲍玉鲍二爷不是说过,那年完者都娶小妾阿娇,原是新来府上的一个雏妓出身的丫环,她勾引情人就常在山亭下面杂草遮蔽的洞穴中做爱,莫非红儿也相中了那个地方?
果然如此。当傅德错愕借着朦胧的月色摸到那个洞穴处,他隔着草丛便听到了里面传出阵阵淫浪之声,是一个女人喘息着的娇吟和一个男人亢奋着的淫谑。傅德错愕怒不可遏,他一脚踢开草边那堆偷情者脱下的裙裾衣裳,猛喝一声:“淫贼,看剑!”洞穴边一棵碗口大的树儿,顿时被劈作了两段。月光下,两个赤条条的男女惊呆了,趴在地上鸡啄米般连声求饶。傅德错愕一把将这对狗男女揪出洞外,定睛一瞧,不错,这小女子正是红儿,她本能地抱住那对怎么也遮掩不住的玉乳,露着一双惊惶的眼睛,活像一只落网的野狐。那男子为谁?甚是出乎意料,他不是张府中的奴辈下人,乃是文炳的外甥明昭。
这三个彼此并不陌生的故人,分别几年后,想不到竟在如此的境地中相遇。傅德错愕唏嘘几声,把剑插入鞘中,又将那堆零乱的衣裳掷于偷情者面前,待对方情绪稍定,他便冷冷地问:
“红儿,是你送卜朵儿花来张府的吗?”
红儿“嗯”了一声,噢,傅大官人原来是来寻妻的,都是风月场中的人,她已猜到这位重返故地的亡命徒在牵挂什么。她边整理着头上的钗头,边轻拊玉手道:“我说破镜会重圆嘛,卜姐还不相信哩!”于是她说,卜朵儿花到张府后,老夫人怜悯她孤女一人,夫妻失散,老家又没有亲人,也就将她藏于房中,答应让她小住一段日子,待寻访到夫君下落再说。哪知后来老爷得知了内情,他责怪老夫人说,而今卜朵儿花已是罪人之妇,要是红巾官府察知,这祸事不是自个儿揽来的吗?好说歹说,老爷和老夫人商量,已将卜姐转送到了江北那个清静隐蔽的水月庵中,并嘱托庵中老尼悉心照看。末了,红儿说:“明日我就送你过去吧,卜姐等你可等得急哩。”
傅德错愕知道,卜朵儿花与偎红舫中的姐妹,甚是相知相亲。他感激地望了红儿一眼,点头应允了。
“傅德兄长远道而来,你不到姑妈那儿去叙叙旧吗?”明昭自以为乖巧,他在一旁没话找话地讨好道。
傅德错愕瞥了明昭一眼,心中暗道:“哎呀,还有一事我险些忘了!对,此事还须从这小子嘴里,掏得下手的机会。”于是,他顺着话茬反问道:“你月下偷情还嫌不够,是让我做红娘把红儿说给你做小妾吗?”
“小弟荒唐,小弟知错。”明昭沮丧地低了头。
傅德错愕一步近前,扇了明昭一个耳光,恨恨地喝道:“纨绔子弟,浮浪成性,这个我不管。我且问你,明玉珍收你为义子,他们夫妇俩都宠着你,让你做了王府的内府总管,你只须交代,陇蜀王爷平日何时出府?何时归府?日间夜里,起居如何?”
明昭被一巴掌打懵了,他不知此问何意,但又不敢不答:“兄长问起,小弟如实相告。眼下蜀中粗定,官府百事待议,王爷行邸,案牍堆积如山,陇蜀王夜夜秉烛披览,不到四鼓时分,他不会灭烛入睡……”明昭嗫嚅着,不敢隐瞒,他将玉珍平日起居的细节,一一和盘托出。
当明昭意识到自己在慌乱中太不慎,不禁“啊”了一声,有些失态地惊叫道:“兄长此问,莫非……莫非要干蠢事?”
傅德错愕对明昭的失态,不屑一顾。他转过头来,叫住红儿道:“你看这浮浪子,莫名其妙说些什么?红儿,我们约定,明天就去水月庵……”
嘉陵江之北,一条涓涓小溪的深处,两岸是青青郁郁的樱桃树,地名唤作樱桃溪,若是初夏,树上缀满红珍珠般的樱桃,溪风习习,把天上那轮晓月漂洗得淡淡的,浅浅的,像是为这幅樱桃溪风景的丹青水墨画所盖上的一枚名章,故而这里便成了巴渝八大景之一,骚人墨客称之为“樱桃晓月”。但现在时令已入秋,樱桃早被山中雀儿啄食尽净,唯余树林深处藏着的那座尼庵,青灯木鱼,与一溪潺潺的流水寂寞相伴。
尼庵殿堂上供奉着一尊手持月轮的妙龄观音,这尼庵,名唤水月庵。庵中比丘尼一老一少,少者即是卜朵儿花。乱世姻缘,忽散忽聚,卜朵儿花与傅德错愕相会于此,惊喜,落泪,各述相思,共话衷肠,这自不必说,红儿送来客人就匆匆回去了,临行,她问:
“卜姐、傅大官人,你们且安歇几日,几日后会有一位故人前来相访,你们欢迎么?”
傅德错愕明白红儿说的是谁,他含笑点了点头,算是颔首相邀了。
这故人,即是嘉陵江水上花城偎红舫中的歌伎兀赛儿,几日后,她果然卸去红妆,乔装成一个进山许愿的香客,悄悄来到了水月庵。庵中老尼为客人备下几盏香茗,诺诺着退下,小小的殿堂上相聚着这三位天涯漂泊人,他们好不感慨万千。
一番叙旧之后,兀赛儿望着当年踌躇满志、自许屠龙的傅大官人,心下甚是惴惴不安,她叹息道:“自至正十一年红巾造反,至今已有十有一年。十年劫难,天下满目疮痍。眼下中原板荡,江南早失,天道轮回,天意难测呵,唉,唉,这大元的江山,是不是要改换主人了?”
“大元江山?这江南江北,长城以内,算是大元的江山吗?”卜朵儿花来重庆后,没少去偎红舫闲聊,她与兀赛儿同病相怜,不由也附和道:“这些年的颠沛流离,我算是明白了,我们老祖宗从别人手里抢来的东西,是到了奉还别人的时候了。我说夫君呀,天可怜见,这乱世凶年,我们没死在刀兵之下,现在是该为自己打算打算了。”
“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傅德错愕也叹息不止。他恨造反的红巾,更恨大元朝廷那一群不争气的窝囊废,在朝则贪赃枉法,卖官鬻爵,统兵则专横跋扈,膨胀野心。他是蒙古血性男儿,在两个心爱的女人面前,又岂能示弱,于是,他弹着剑铗道:“屠龙剑呀屠龙剑,国运蹇促,时世维艰,你一腔豪气,两刃青锋,为什么伴我久久不去!”
“傅大官人,此次你远游中原,难道没听闻中原部族中人,因厌倦战乱纷纷举族北迁的事吗?”兀赛儿终于说到正题了。
“姐姐说得是。”卜朵儿花瞟了偎红舫姊妹一眼:“听姐姐前日说,襄阳亡父的族亲,曾有人到偎红舫打探我们的消息,意思是要呼亲唤友,邀我们同返塞北呢。”
“你们是说,巴山蜀水凄凉地,容不得我们了?”
“这倒不是。卜妹也知道,红巾打下牛头寨后,明玉珍又颁布了一道法令,是告示过去的庄园耕奴、牧奴,一律免除奴籍编入民户的。告示上说了,红巾官府还要给他们发贷种子和耕牛哪,蜀中百姓,好不欢天喜地。”
“我们不是蜀人,但我们也有自己的家。”卜朵儿花望着她失而复得的夫君,不由含情脉脉:“夫君你知道吗,这些日子我在水月庵夜夜梦见的是什么?是梦见我们双双北归塞外,回到祖宗们生生不息的大草原,有蓝天白云作伴,牧放牛羊驼马远游……”
这对劫后余生,复得团聚的夫妻,他们相顾唏嘘,不由得引得一旁的兀赛儿也伤感地落泪。原来,兀赛儿虽有色目人的血统,但因外祖父早年坐罪而被籍没为奴,少年时就被转卖来蜀沦为船伎,一个天涯孤女,正盼着与昔日情人结伴归乡呢。
三个异乡落魄人,半日计议,终于商定了北归。是日,兀赛儿留在水月庵,她说,待几日红儿将她留在偎红舫中的细软带来,且聊充路上盘缠,到时,他们一行三人便可启程北上了。
岂料是日夜里,两个女人一觉醒来,却发现屋角另一张床榻上的男人没有了鼾声,掀开蚊帐一瞧,哎哟,人已不见了……
傅德错愕并没有沉浸在寻回爱妻又得到情人的喜悦之中,他耿耿于怀的,是要干一件惊动世人的大事,才肯遁世归去。前几日,他从明昭嘴里探得玉珍起居习惯,这天夜里,他便悄悄离了水月庵,三更刚过,他已潜入城中,到了玉珍的行邸。
陇蜀王府远不能同张府相比,不过是昔日旧府衙近旁的一个大院,院子虽大,但屋舍十分低矮简陋,围墙也不高。傅德错愕趁着夜色的掩护,蹑手蹑脚地在院里转悠,东一处西一处的屋子都静悄悄的,大多是茅檐小窗,他分不清哪是主人所居,哪是奴仆的住处。对了,明昭不是说,王爷居室在北面么,他绕过一丛夜风中婆娑作响的竹林,果然发现北面的一个屋子亮着灯,他赶紧梭过去,挨近窗边,一听,屋里果然有人。听窗内的说话声,是两个女人在聊闲话。
“娘娘你听说了吗,嘉陵江水上花城中那个兀赛儿失踪了,听说她碰见了她昔日的情人,叫什么来着?听说是一个蒙古血统的俊俏男人,一个蒙古达鲁花赤之子,听说他俩已双双私奔了。”
“私奔了好。那个偎红舫的风流歌伎,原本就是漠北来的色目姑娘。这些年漠北部族中人纷纷北归故里,玉珍已经晓谕了蜀中各地州府,凡蒙古人、色目人要离开蜀地的,只要他在乡里没有恶迹,官府皆一律放行。”
“唉,兀赛儿少年时就来重庆,她在风尘中苦苦挣扎这么多年,也该有一个走好运的时候了。”
“玉珍也晓谕了各地州府,凡官私歌伎,愿脱乐籍者,都任其去留,可与驱奴脱奴籍编入民户一样看待……”
这儿不是王爷所居,傅德错愕本想离去,但听到屋里两个女人在议论兀赛儿,他又挪不开脚步,不由用舌头舔破窗纸,偷偷往里一瞧,喏,这儿原来是厨房,看来灶下烧火的那一个,是府中厨娘,另一个围了一条蓝花花围腰,用擀面杖在案板上擀着一团面团的是谁?听厨娘称呼这个擀面女人为娘娘,他明白了眼前这个着蓝花花围腰的女人乃是陇蜀王妃彭氏。王妃亲自下厨,为夫君做夜宵馍馍,对了,这也是明昭说过的王府细节。
“娘娘,那兀赛儿出身原本也是高贵的,你知道吗?”窗内厨娘一边往灶孔里塞柴禾,一边继续唠叨:“她的外祖父原是漠北康里部族的头人,早年跟随忽必烈征战中原,也曾屡建奇功,但后来依附叛王,获罪死于狱中。按大元律令,罪人妻女一律籍没为奴为妓,那时她母亲才十七岁,被平叛的元军俘虏而囚于女牢,一个弱女子,每夜都遭到十几条军汉轮番蹂躏,后来送去官衙为奴时,已是身怀大孕的女人了。母亲生下她后,给她取名叫兀赛儿,这是康里语,意思就是没有父亲的孩子。兀赛儿九岁那年,母亲病亡,她被别人拐卖,几经转手,才流浪到蜀地,当年,是偎红舫那个鸨母收养了她……”
也是一副厨娘打扮的彭氏,一边往蒸笼中上馍馍,一边也叹息不止:“苦命的姑娘,愿菩萨保佑她有个平安的归宿!”
傅德错愕心里咯噔一下,难得王妃娘娘有这一声祝福,今日红巾以德报怨,各路关卡都给北归的部族人放行,今夜我却……唉,谁叫我在扩廓大帅那儿领了军令状呢,此行后果若何,那就听天由命吧。傅德错愕正在暗自思忖,忽见有人打着灯笼走过来了,他机警地闪躲在一旁,哦,来人是一个老军卒,这老卒进厨房后,提了一个食盒出来,他明白,这老卒是要给陇蜀王送夜宵馍馍了。傅德错愕不由尾随着这个打灯笼提食盒的老军卒,顺着一条石板小路往前走,绕行到一处泉水形成的水池处,有十几步跳磴涉水而过,左转右拐,前面几棵高大的古树背后,又有一处黑憧憧的屋舍,时近四更,小窗还亮着灯,前面必是陇蜀王的寝宫无疑。傅德错愕急忙猛蹿几步,顿时挡在了那老卒的面前,他手起剑落,“刷”地一声,一下削掉了灯笼中的烛头,老卒还未弄清是怎么回事,那剑锋已直逼他的心窝:“快说,前面亮着灯的屋子,是不是陇蜀王的居处?”
“是,是,——啊,不,不……”老卒惶急,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但傅德错愕已经明白了,他一剑捅进老卒的心窝,老卒来不及惨叫便断气倒地,一个盛馍馍的食盒被撂在了一边。傅德错愕飞步前行,但尚未靠近小屋,路边一棵古树背后,突然闪出一人,挥剑轻喝道:
“来者何人?何事仗剑夜行?”
傅德错愕一惊,王爷警卫,好不森严!他并不答话,只是挥剑直刺对方。二人不由在树下格斗起来,一来一往,闪躲劈刺,各自皆暗叹对方好身手。彼此斗了数十回合,乘着天上星月的微光,傅德错愕时不时打量着对手,咦,此人好生面熟,是在哪里见过?哦,在广安,在广安那小客栈,彼此同住,还闲聊过半日。他叫什么来着?哦,对了,此人少年气盛,负剑江湖,姓陈,名叫陈亨,前几年充当过陈友谅的刺客,也曾有过自己今日之行事。
“壮士!当年你不是奉命行刺过明玉珍吗?”傅德错愕一剑直刺对手前胸,不解地轻喝一声。
“今日之我,已非昨日。”陈亨闪身一跃,斜刺里回剑还击。二人从树下退出,一路对打,不觉到了屋后院墙。陈亨后退两步,轻斥道:“当年行刺,我就是在这儿杀了鲍二爷的!今日你来,莫非是要为此等恶人抱不平?”
傅德错愕收剑在手,往事不屑一提。他一纵身,跃上墙头,愤愤道:“你以为鲍二爷是我的朋友?呸,小人,小人!一个贪赃枉法、卖主求荣的小人,他要是落在我的手里,我也非杀了他不可!”
陈亨也跃上墙头,追击刺客到了墙外。二人边打边走,此时来到了一条僻静的巷子深处,这回轮到陈亨不解地盘问了:“傅德兄,别来无恙,想必你已认出了我是谁。人道蜀中两剑客,一持莫邪,一持屠龙,江湖口碑可坏不得呀!”
傅德错愕也后退两步,欲走未走:“此话何意?”
陈亨左手握剑,右手轻弹着剑铗叹息道:“汲汲乎争名于朝,熙熙乎争利于市,皆非我求。登高一呼,天下响应,亦非我所景仰。莫邪呀莫邪,你只为市井小民,乡里百姓,斩恶济善,除邪扶正!江湖侠义,难道不是尽在这善恶邪正四字之中么?”
“陈亨兄言之有理。但今日之事,你所抱不平者,为何竟是陇蜀王爷?”傅德错愕故意抬出明玉珍今日的身份。
陈亨不由轻笑了几声:“什么陇蜀王爷?在我眼里,他只是一个平民布衣,良善汉子,哪有半点作威作福的王爷派头,呼奴唤婢的老爷影子?”
“你是在为当年行刺之事忏悔么?”傅德错愕已感觉到对方那一口莫邪剑,正气凛然,不可侵犯。
“是的。此等蠢事,岂是我辈所为!”陈亨察觉到了对方神情的无奈。接着他又逼问道:“自从兄长来重庆,我便盯上了你。兄长游蜀中,现已破镜重圆,不知兄长今夜为何不陪爱妻,却来干一桩小弟当日的蠢事,敢问兄长何以任人驱使?”
“噢,原来他对我入蜀的行踪如此了解!我受扩廓大帅所遣之事,能告诉他吗?”傅德错愕暗叹陇蜀王深得人心,竟如此出乎他所意料。他似乎醒悟到了什么,但一时又说不清道不明,他不得不仰天叹息道:“唉,唉唉,罢了,罢了,天不助我,其可奈何!”言罢,也不道别,一纵身跃上屋顶,一阵风似地飘走了。
不消说,慌忙潜出城外的傅德错愕,不敢有片刻停歇,一路急行,又匆匆返回了水月庵。
庵中两个彻夜不眠的女人正在灯下等候,当她们知道这个男人行刺未果时,好不大惊失色。巴山蜀水是非地,岂可再作逗留!是夜,夜色尚未褪尽,幽深的山中传来几声乌鸦的夜啼,昏暗的庵堂上,那尊手持月轮的观世音似乎也转身而去,毫不理睬他们。三个天涯漂泊人满怀凄凉,一腔愁绪,他们来不及向庵中老尼道别,便匆匆上了路。
这位自许“袖里屠龙,埋没青锋”的达鲁花赤之子,只好一路唏嘘,叩弹着他的屠龙剑,携着心爱的两个女人,涌入部族人的难民潮,无可奈何地北归塞外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