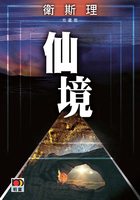李君诚的供词,在天完政权内部,搅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新建立的红巾官府明里摊派苛捐杂税,暗里又勾结山贼打家劫舍,官匪一家,盘剥乡民,这算哪家的王法?
玉珍将此案交戴寿审理,戴寿拿着案卷,他好生犯难。明昭是拘押起来了,但他矢口否认通贼,他的宠妾翠花也串了供,说明将军把她从草贼山寨救了出来,此次去响水桥,绝非通贼,而是要诱贼上钩,以便明将军将其一网打尽。并诬称李喜喜横插一杠子,搅乱了他们剿贼的一盘棋。而番市弄来的那些白花花的银子呢?问案问到这个节骨眼上,张文炳站出来说话了:“这些年明公亲率大军东征西讨,军粮一车一车送到前线,哪一仗让士卒挨过饿?将士们的军饷也从来没有少一个子儿,不都是花的这些银子吗?我这个镇守重庆的粮草官,若有私吞情节,请取我的首级以谢天下好了。”
诸将议论纷纷,各执一词。有说须按军法从事的,有说此事蹊跷,情有可原的。玉珍回到行邸,踌躇不决。彭氏夫人见他半天闷头不语,时不时长叹短吁,她不由排解道:“夫君你刚即位陇蜀王,按理说,今日对天下罪人都宜赦不宜杀,何况还是麾下的将士。”
“明二(万胜)将军要严饬军纪,他已多次责难,说不除败类,难道是顾惜明昭是我义子么?”
“唉,要说明昭浮浪一点,那倒可能。说通贼,又有什么凭证?一个李君诚山贼,他自己死到临头,想拖几个垫背的,乱咬也不是不可能。至于明二兄弟,那好办,我叫细妹去劝劝他不就得了。”彭氏夫人一副顾全大局的口气,倒也很是体察玉珍的犹豫处境。
番市劫案,玉珍斩了山寇贼首,尚来不及深挖根柢,又忽有快马来报:川北巴州失陷,退回陕西的元军又蠢蠢欲动了。军情紧急,玉珍只好释放了明昭,又安慰文炳,并遣万胜率军,前往川北御敌。
攻陷巴州的是舒家寨的田成、傅德错愕,他们原想攻下巴州做桥头堡,接应陕西的元军大部队入川反扑。殊不知中原战事频仍,李思齐的主力已东调入河南,留在汉中的元将,哪敢如约前来。当万胜挥军直抵巴州城下,那舒家寨的乡勇们,困于城中,孤立无援,一个个都抱怨寨主错估了形势。
“现在的蜀中,州官县官,都换成了红巾的官员。过去我们是官军,他们是贼,是匪,而今乾坤翻转,他们成了官军,我们是贼,是匪了。乡勇们最讲逆顺二字,不愿做乱民乱军,眼下军无斗志,咋办,咋办呵?”田成巡城归来,神情很沮丧。
“李思齐背信弃义,答应了入川却又远走河南。都怪我太轻信。唉,朝廷倚重的大帅们,人心叵测呵……”傅德错愕也心意烦乱,他想骂人,但朝廷上下,该骂的奸臣贼子太多,他不知从谁骂起。
“前日哨马来报,红巾一支偏师,已踏平了我们舒家寨的老营盘,今日进无可进,退无可退,奈何,奈何?”田成唉声叹气,已没有了主张。
傅德错愕心里烦恼透了,但他却故作矜持,沉吟一会,很果决地献计道:“田兄,兵法云,三十六计走为上。我看,不如远走汉中,今夜就突围吧!”
是夜,当田成、傅德错愕弃城出逃的时候,他们不曾料到,万胜早已布下伏兵。一场恶战,舒家寨寨主田成中流矢身亡,傅德错愕也在乱军中与卜朵儿花离散,不知夫人是死是活,突围出来,他仅余单人单骑了。
傅德错愕一路马不停蹄,好不容易奔逃到了汉中。但汉中的元将并不接纳他,那守城的元将立在城头,只拿冷眼睥睨着他,觑了他半晌才说:“你就是巴州的败将傅……傅什么来着?本将奉李大帅之令,只迎凯旋的使者,不纳败军之将!”言罢,便转身而去了。
傅德错愕人饥马困,也不乞留,他拨转马头,又折向陇东匆匆而去。
陇东元军屯田使不是别人,乃是从湖广逃来的威顺王爷宽彻普化,当年傅德错愕父亲就在他的麾下效命,并战死在常德府达鲁花赤任上的。但傅德错愕赶到陇东,方知威顺王爷在那儿已是掉了羽毛的凤凰不如鸡。他受不了边地阃帅的冷嘲热讽,早已带了几个贴身怯薛,化装成一行商旅,绕间道去了云南,依附云南的梁王以寄残生了。
傅德错愕难免心灰意冷,国事颓唐如此,倒不如料理料理一下家事吧。于是他思念起与他苦苦相依的卜朵儿花来了,唉,一个女流之辈,被乱军冲散,她可能去哪儿呢?她父母双亡,唯一的去处只能是投亲靠友,哦,想起了,她的襄阳老家,不是还有几个远房亲戚么,傅德错愕顾不得旅途疲劳,又匆匆折回,驱马直奔襄阳。
但襄阳哪有卜朵儿花的影子?傅德错愕问遍了亲友都不知她的下落。百般无奈,他只好去了城外山中一座古刹,求得一位老和尚的相怜,暂且安顿下来。
一日无事,傅德错愕闲步转到庙后,见那里有一座磨房,他推门而入,不知怎的,那拉磨的畜生不是驴,竟是一匹马,而一壁破墙的遮风处,还挂着一副战马披挂的铁甲——哦,这不是当年大战高邮的铁甲重骑吗?
傅德错愕用诧异的眼光询问老和尚:“师父,这山中几时来过贵客?”
“你是询问马的主人?”老和尚看出了这位寄宿者的疑惑,他笑了笑说:“我就是它的主人呀,你想不到吧,我就是当年从大都出发,南下作战的一名铁甲军老兵呀。”
“你临阵脱逃?”寄宿的客人追问。
“不,是无将统兵,士卒自散。”庙中和尚回答。
老和尚说,至正十四年,红巾张士诚占据高邮,截断江南输往大都的运河粮道,那时朝廷倚重的丞相脱脱,亲率五十万大军南征,连营扎塞数百里。铁甲军摧坚陷阵,高邮城被围了个水泄不通,眼看即日可下。哪料想皇上突来一道圣旨,临阵仓促换将,脱脱被谗害,后来谪死异乡自不必说,当时众将士无不寒心,竟于阵前一哄而散。官军中的汉军,纷纷降附红巾,铁甲劲旅之师,也远走襄阳,投奔了当年的北锁红巾布王三。
老和尚叹息着说:“但布王三不用铁甲军,后来答失八都鲁攻破襄阳,灭了北锁红巾。铁甲军众兄弟无将统领,好些人都开小差回家了。我上无父母,下无妻儿,便来这山中庙里过清闲日子。”
“答失八都鲁现在何处?”山中寄宿客又问。
“他死了。”昔日的铁甲老兵口气很冷漠:“他从襄阳进入中原作战,遭到中原红巾重创之后,只图壁垒自固,皇上遣钦差前来督战,又发现他与红巾暗中议和。皇上龙颜大怒,怯懦的答失八都鲁惊恐不已,忧郁万分,已暴病卒于军中。现在,他儿子孛罗帖木尔统领其军,已北上大同去了。”
“铁甲军呢?”寄宿客追问不舍。
“铁甲军今日已走好运了。”这位做了和尚的铁甲老兵,眼中忽地闪过一道亮光,他继续说:“今日那位河南总兵察罕帖木尔,他极能用兵,铁甲军几经周折,转到他的麾下已重振雄风,他善用铁甲重骑,再配合他原有的轻骑,数年来叱咤中原,大破汴梁城,逐走刘福通,已占地数省,拥兵数十万,大元朝廷的局面,全仗他一人支撑了。”
“察罕大帅的威名我早已风闻,只恨我无缘相见!”落魄的寄宿客眼里也闪过一道亮光,他还在希冀有机会以求一搏。
“这有何难,我在铁甲军中有故交,求他引见即可。”老和尚闲聊中的一句话,使这个落魄山中的寄宿客又躁动不安了。
数日后,傅德错愕离了襄阳,带着老和尚的引见信,又去河南另寻新主了。
巴州突围,被乱军冲散的卜朵儿花借着夜幕的掩护,慌忙逃出,不知夫君是死是活,她一时失去了追随的目标。
北行逃命太危险,那容易落入追兵之手,她索性乔装成一个小厮,勒马南奔。不数日,来到渠江边的广安城,她竟寻到了当年她同傅德错愕一起逃难所寄宿的那个小客栈,连日奔逃太疲惫了,她一个孤单女人,哪里是归宿呀?不如在此小住,打探打探消息,再定行踪。
她仍住在当日与夫君同宿鸳鸯的那间小阁楼里,人去物在,她不由莫名地伤感。客栈老板娘见这小厮眉目清秀,举止文雅,也喜欢过来闲聊。她天南地北扯了一些闲话后,忽而很沾光似地说:“客官你知道吗?别看这是小客栈,当年还住过两位江湖大侠呢。”
“广安出过江湖大侠?”客官应酬着,问。
“啊呀呀,那可是了不得的两个侠客呀。一个叫陈亨,他曾一次杀过重庆旧官府的七个贪官。另一个叫傅德错愕,他曾在川北舒家寨烹杀过卖主求赏金的刁奴。他们俩都是英雄出少年,在我小客栈同住过好几天呢。”老板娘述说的往事,一下又勾起这乔装的客官拂不去的昔日情景。是的,夫君一支屠龙剑在手,他独闯江湖,料想别人也奈何他不了。倒是自己一个女流之辈,又如何独闯江湖?乱世苟安,她不想再去那酒楼妓院侑酒卖笑。要避人耳目,眼下最清净的地方,只能是山中的尼庵了。
溯渠江而上,青峰翠峦的华蓥山中,藏有一座小小的翠云庵。这里长年住着一位从中原来的老尼,卜朵儿花得到老尼的收留,换了偏衫,戴上尼帽,昔日的风流娘儿现在成了空门中的比丘尼,她每日的功课,无外乎是菩萨面前诵诵经,余下的时间,便是打扫打扫庭院的落叶。
其实,一座空寂的山中尼庵,又怎能锁住卜朵儿花那一颗原本躁动不安的心!这个昔日襄阳元将的女儿,从少年时代起就遭逢颠沛流离,这些年来的战争苦难,一次又一次地重创着她的身心,一个女人身处乱世,幸与不幸,痛苦与欢乐,希望与绝望,为何如此地来无影,去无踪?这个世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当她得知这个山中老尼是前些年随难民潮入川的,她不由同病相怜,随口问道:
“师姑家住何处?家里还有亲人么?”
这老尼回答说,她是河南沈丘人,但非土著。她祖上是漠北草原部族中人,早年随忽必烈大军南征,后来子孙们便成了中原的探马赤军,平时屯田,战时作战。红巾刘福通造反,她男人随沈丘的部族首领察罕帖木尔起兵,不久阵亡,后来她儿子随察罕打汴梁,在攻城时又死于滚木礌石之下。是战争使她成了一个孤苦无依、四处漂泊的难民,但转篷千里总得有个归宿呀,她说:“我们祖上在漠北,大草原才是我们生命的根。娘子,你知道我每日在菩萨面前许什么愿么?愿能落叶归根,生还故乡大草原呵!”
“不是说察罕大帅在中原已大破刘福通,不日他就将挥军南下,横扫江南红巾群雄吗?师姑,你应该回中原,大元的中兴,指日可待呀。”寄居山中的娘子虽然明白她父亲的根,也在漠北大草原,但她知道生她养她的故乡,已是中原大地了。她不愿看到大元的气数,会如此不堪地烟消云散。
“中兴?阿弥陀佛,佛经里说,昙花一现。察罕大帅的兵威不过是昙花一现呵。”老尼言罢,闭目养神,她欲再说下去,但嘴唇嗫嚅了半晌,不出声,不知她在心里暗自叨念着什么,待她睁开眼来,她那被痛苦煎熬得很浑浊的眸子却忽地明亮起来,又顿悟般地补了一句:“谁说世事难料?佛在菩提树下说,一叶落而知天下秋!”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卜朵儿花不懂佛门玄理,她疑惑不解地望着面前这位看似很村俗却又很明睿的师姑。
“娘子,你初来尼庵时,那日到庵后水泉边汲水,不是有几个乡里地痞小子嬉笑着纠缠你,连呼尼庵出了风月娘子,只可惜拆了尼寮没地方过夜么?”
“师姑还提那件小事干什么,那天不是来了几个巡检司的红巾,已将那些地痞抓去打了板子,我已消气了。不过师姑说的尼寮,尼寮是什么呀?”
“尼寮就是尼庵妓寮。你想想,当年那么多妇女逃难拥入川中,小小的尼庵养不起,这山里男人多女人少,尼姑要求生,只好把佛殿当妓寮了。”
“噢?——造孽,造孽!”卜朵儿花好生惊讶。
“娘子不用担忧。天完红巾入川后,坐镇重庆的那个大帅明玉珍,已明令拆除尼寮,尼姑们都还俗乡里,有家有室了。年老而留在尼庵的,红巾官府也拨了庙田供养,用不着云游化缘了。”
卜朵儿花松了一口气。老尼接着说,山中尼庵见到的虽是一片秋叶,但从这小小的一叶,却能窥见全蜀的大气候。现在巴蜀各州府,乡间无流民,路上无饿殍,民心已归附红巾,这样的地方,察罕的兵马还打得进来吗?
没几天,卜朵儿花再去庵后的水泉边汲水的时候,同在那里打水的一个村姑告诉她,前些日子在川北平叛收复了巴州城的红巾,已翻过大巴山,打到陕南的汉中府去了。卜朵儿花想打探她夫君的消息,便问打水的村姑:“守汉中的,是哪路元将?”那村姑很得意地说:“我们村有好些子弟就在那支红巾队伍中,我阿哥还是那支红巾队伍中的百夫长呢。前几天他已捎信回来说,李思齐逃跑了,守汉中的,是商州过来的毛葫芦军。呃,你知道毛葫芦军吗?前些年他们入川,在我们这个地方糟蹋过多少妇女呀!阿哥信上说,这次打汉中,还杀了毛葫芦军的头儿,叫郭……郭什么来着?”
“叫郭成。这些蟊贼,应该斩尽杀绝才好!”卜朵儿花勾起了那次赶庙会横遭强暴的往事,没想到她夫君赌咒发誓也未曾办到的事,到头来,竟是红巾健儿为她解了这口恶气。但她惊喜之后,又挂念起夫君的安危:“呃,你阿哥信上,没提到从巴州逃出的那个,那个傅德错愕吗?”
那村姑似乎觉察到这新来的尼庵女人有些异样,她携上水罐,回头一瞥,淡淡地丢下一句:“你问的那人,是无名之辈吧,我阿哥怎能提起?”
村姑走了,卜朵儿花也感到了自己有些失态。她伫立泉边,呆呆地望着村外的远山,这时,有一对野雉忽然从草丛中飞起,咕咕地鸣叫着,不知是悲还是喜。她不觉打了个寒噤,自言自语地叹息一声:“怎么这样冰凉,这山涧刮来的风呵!”
傅德错愕投奔察罕并未受到重用。察罕大军猛将如云,谋士如雨,对于这个落魄来归的年轻人,只打发他做了军中管理文书的一个小小的军曹。
整日阴沉着脸的傅德错愕,郁郁寡欢枯坐营中。一天,他闲着无事,午饭后到营门外溜达,时已盛夏,烈日炎炎,士卒们都在树阴下纳凉。树梢上蝉儿的聒噪时停时起,军卒们没好气地骂几声鬼天气,便三三两两地唠叨起这没完没了的战事。
“老哥,都说山东是红巾贼的老巢,当年红巾大帅毛贵进逼京畿,元都大震。旗帜上大书一对联是怎么说来?”一个红脸膛的军士聊起话头。
“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一个头发有些花白的老卒应声道。这老卒当年随芝麻李在徐州起义,后来转战中原,又跟随红巾草头王降附了察罕。这世道风云突变,渠帅们诡诈万端,他又不无感慨地叹息一声,接着说道:“唉,毛贵死了,山东群龙无首。听说花马王田丰归降了察罕大帅,山东全境数十州县皆被攻下,现在只剩下一个益都城了。”
“这个花马王,我看他是花招王。他本是黄衫军万户,一会儿归降红巾,一会儿又归降官军,反复无常,居心叵测。大帅怎么如此器重他?”
“听说守益都的贼将陈猱头就是他的部将,察罕大帅是以毒攻毒,已将他调到益都城下,想用他攻城打头阵呢。”
“老哥听说了吗,前几天夜里,有巡逻的骑卒发现田丰兵营有人向城头放箭,因天黑,未看清。你说会不会是向城里暗递书信……”说这话的是那个红脸军士。他们言者无心,听者却十分在意,当他话音刚落,傅德错愕便一个箭步蹿过去,揪住他的衣襟,厉声道:
“如此重要的军情,为何不禀报大帅?”
纳凉的士卒们都惊愕了。他们知道,察罕待下寡恩,没拿准的情报若送上去,少不了是要挨军棍的。眼下这位新来的军曹如此唐突,打抱不平的士卒纷纷上前劝解,末了,还白着眼奚落了军曹几句:
“你新来乍到,想立功讨赏吗?想升官晋级吗?有本事的,你自个儿去吧!”
说来也是活该傅德错愕倒霉,他丢下那个红脸膛军士,气咻咻地赶到察罕的营帐,当他禀报完听来的紧急情报后,察罕先是一愣怔,气得他腮边特有的那一撮毫毛都直竖起来,但转瞬间,他瞪着的那双鹰隼般的碧眼又狐疑起来,再三追问,这新来的军曹却拿不出一个证据。这不是捕风捉影,不是来扰乱军心么?察罕转身离去的时候,只是从鼻腔里轻轻哼了一句:
“军棍伺候,逐出营门!”
然而,正当傅德错愕在军营中养杖伤的时候,益都城下,一场预谋的兵变果然发生了。第二天,察罕一行十余人去巡察田丰兵营,田丰椎牛酾酒,盛情款待,饮宴正酣之际,伏兵突发,一股脑儿杀了察罕随从,紧接着三通鼓响,益都城门大开,哗变的官军将察罕挟持入城,当夜,察罕因在兵变中伤势过重,也不治而一命呜呼了。
察罕之子扩廓帖木儿攻下益都,下令屠城三日,以泄其愤。花马王田丰被捉来了,赤身绑在木桩上,扩廓要剜其心以祭亡父。
祭台高筑,众将士一片肃穆,傅德错愕带着杖伤,也肃立在队列中。祭奠仪式冗长又沉闷,好不容易念祭文了,一长串谀词美誉把察罕打扮成了一个盖世无双的中兴勋臣,扩廓很陶醉,默哀中微闭着眼睛。谁知此时,那个即将成为祭品的俘虏花马王陡然大叫一声,呸地一口浓痰吐出,竟破口大骂道:“察罕何人?大元奸臣贼子也!汉之奸雄曹操也!阴谋篡天下者,必是……”
这揭老底的牌怎能让人摊出?扩廓惊惶跃起,一瓢冷水泼过去,嚓地一刀,直剜仇人心窝……
许多士卒都默默地勾着头,不知眼前的杀戮究竟有什么黑幕。傅德错愕直愣愣地盯着祭台,看杀人剐人他是不会眨眼的,但有一个他担忧的隐衷现在似乎见到了端倪,唉,朝廷的大帅们,谁不是拥兵自重?看他们逐鹿中原,明里报国杀贼,暗地里却各人都有各人的帝王梦呵。
杖伤痊愈后,傅德错愕仍是枯坐营幕,传递传递军中文书。数月来,他的心情一天比一天沮丧,从四方传来的军报可说是没有一个好消息,察罕一死,大同的阃帅孛罗便举兵南下,气势汹汹来抢夺扩廓的地盘了。兵出潼关的李思齐也搅和在其中,三股元军犬牙交错,互相厮杀得一塌糊涂。有时,他陪末位参加军中幕僚的宴饮,那酒后的闲聊,又多是朝廷放出风声,谁愿意捐多少多少银两,便可到某处某处做官。国事难料,他心灰意冷之中,不由又思念起卜朵儿花,失散半年有余了,现在她还活着吗?她一个漂泊无依的弱女子,难道尚未逃出蜀中?
正当傅德错愕有心返蜀的时候,一个机会突然降临了。
一天,扩廓大帅破例地召他去帐下小饮,寒暄了一会军中琐事后,扩廓从怀中掏出一封书信,示意他浏览浏览。傅德错愕并没有受宠若惊的感觉,他在心下嘀咕一句:“危难之秋,必将有事授命于我了。”当他凑过头去,便看清了这是建康的朱元璋派使者送来的议和书,书信略曰:
阁下先王奋起中原,英勇智谋,过于群雄。不意先王捐馆,今者阁下意气相期,吾深有推结之意。若自今以往,信使继踵,商贾不绝,无有彼此,是所愿也。
“大帅要我去红巾贼那儿议和吗?我可不是擅长辞令的辩士呀。”傅德错愕甚是不解。
“不,我想让你略知今日天下大势。”扩廓将书信揣回怀中,他睥睨着眼睛,很不屑地提到各路元军阃帅,然后话锋一转,蹙着眉头又议论起南方的红巾群雄:“红巾贼号称百万,其实,方国珍乃海盗,张士诚一介私盐贩子,陈友谅是打鱼出身的草头王,他们智短谋浅,不足论矣。日后能与我争雄而逐鹿中原者,唯有朱元璋与明玉珍二人而已。此二人,皆民心归附,将士乐于效命。不过,朱元璋口称仁义,实则一代枭雄,他既有议和之意,我可与他划江而治,以待来日兵戎相见,一决雌雄。至于明玉珍,人言其仁心厚德,节俭爱民,若他日民心深固,兵势厚蓄,此公绝非王衍、孟昶之属,加之巴蜀之地,北有剑阁之固,东有夔塘之险,远攻绝非良策。我意在遣一侠士,取其人头,不战而收全蜀。这些日子我有意委屈你,正是想留在此时一用,不知壮士肯助我否?”
“哦,原来如此。返蜀之行,看来是公干也,亦是私情也,可谓一箭双雕了。”傅德错愕心中暗喜,他那冷如死灰的心境又一下被这突来的火星燎燃了。他接过扩廓递来的满满一杯酒,仰脖一饮而尽,然后慷慨应允道:
“此次入蜀,乃我夙愿也!大帅请宽心,来日我必提人头来见。”
翌日,这位昔日达鲁花赤之子,从匣中取出闲置多日的屠龙剑,不由得星夜兼程,心急火燎入蜀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