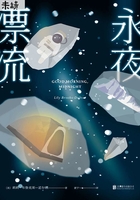原来,玉珍来援嘉定的途中,兵驻泸州的时候,有缘结识了刘祯。
那时,刘祯已弃官归乡,隐居在一个叫方山的山野之处,傍林泉结庐而居,以闲云野鹤自诩,想远避战火,苟安于乱世以了残生。殊不知这平静的生活,却因天完红巾大帅的突然造访而彻底改变了。
那一日,刘祯一大早就在屋前药圃侍弄,日上三竿的时候,他倚着竹篱,闲看山前的青松白云,忽有清风徐徐而起,将山路上清脆的马蹄踏踏声传来。深山幽林,何来贵客?他正诧异,转眼间来客已到了他的茅庐前。
“刘先生,本使久未问安,你看我今日又带贵客来了。”上前打招呼的是泸州宣抚使,他与刘祯既是同乡又是朋友,说话便很随和。
刘祯端详宣抚使带来的客人,来客好魁梧,身材高出常人半头,剑眉隆准,目中重瞳,龙姿虎步,气宇轩昂。但他上前长揖问安,却又十分彬彬有礼。主人瞟了一眼他头裹的红巾,身上的赭服,不由还礼道:“我刘祯何德何能,竟烦劳贵客枉驾屈尊来访,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贵客必是巴蜀民间仰慕已久的明元帅。”
就这样,主客一见如故,他们以一壶清茶代酒,就在这林下的茅舍里,宾主一问一答,促膝纵论天下事。刘祯熟知千古兴亡典故,论及时下豪杰并起,群雄逐鹿,他引古喻今,其说出入三韬六略之中。玉珍恍若置身于当年的卧龙岗,在倾听卧龙先生的隆中对。席间,玉珍暗自思忖:“今日算是逢着孔明先生了,但今日之孔明,不知他心系何处?”接下来,当各自述说乱世见闻,言及生民艰厄处,免不了彼此都有一番唏噓。进山时,玉珍已经知道,刘祯乃进士出身,曾在河北大名府任管理档案文书之职的经历,长期沉沦于官府下僚之中,但此人甚有贤名,深通书史,中原的元军大帅察罕帖木尔曾致厚礼征召他而不就,此次要请他出山,不知此良禽要择何等佳木而栖。
“先生到过重庆的涂山吗?”玉珍撇开闲聊,忽然另提话头。他知道,隐者是不可以功名利禄诱之的,须得剖陈心迹,若志同道合,自可携之而归。
刘祯笑了笑,说他怎么会不去,去了还必得拜谒涂山寺中的大禹王。
“早就听说涂山是大禹娶妻且又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地方。而今天下汹汹,无异于洪水滔天,我想学大禹王的榜样,荷锸执畚,带领众人治服这乱世洪水,不知先生肯跟随否?”玉珍敛住笑容,神情十分真诚。
“明公是说,你景仰大禹当世,天下为公?”刘祯面露欣喜。
玉珍颔首应答。
“明公是说,你景仰大禹王俭约治国,勤政爱民?”刘祯又问。
玉珍神情庄重,又一次颔首应答。
茅舍主人再也按捺不住满心的喜悦,他陡然拊掌而起,朗声笑道:“哎呀,谈了半日,我等待的,就是明公这几句话。读书人不用则藏,用则出。走!跟随明公治水,我今日就出山。”
于是,刘祯随军到了嘉定。这次嘉定大捷,而围魏打赵,奔袭成都,捉女眷,设香饵,这一环扣一环的妙策,皆是出自他刘祯的锦囊。而今,元朝政府在四川的最后三个孤臣已押回重庆,刘祯昔日在官场中混过,他熟悉官场人物,凡蒙古亲贵他都不屑一顾,他此时只想弄明白,赵成这个华夏子孙,口口声声要尽忠元虏主子究竟是何心态?
“赵将军,怠慢了。这寺庙倒还安静,不知近日饭菜是否适合将军的胃口?”赵成被监押在城中治平寺一间禅房里,刘祯寒暄着与他搭话。
赵成先是面壁而立,听见有人探问,他转过身来,瞪着浓眉下一双怒眼,打量一下来人他已明白了几分:“刘先生,我恭贺你现在已升任红巾大帅帐前的理问官了。”他顿了一顿,寻思着如何羞辱对方同时也表白自己。沉默半晌,他好不容易寻到了一个杀手锏:“淮安褚不华死节之事,刘先生听闻过吗?”
刘祯笑了笑:“略知一二。”
“当年扬州青巾作乱,其首领长枪张食人为粮,逐镇南王奔淮安。褚不华守淮安拒寇,历五年大小数百余战,最后粮尽,城中草木、雀鼠、鞍鞬、败弓之筋皆食尽,继之以老稚更相食。城陷被执,宁肯为贼所脔而不变节,千古孤忠,史册留名。今日之事,褚不华在前,后来的赵成岂是亡国的贰臣!”言罢,赵成闭了眼,又转身面壁而坐了。
“哈哈哈,人说我刘祯读书迂,听将军议论忠君之事,想不到更有比我刘祯迂且腐之辈了!”刘祯明白,面前这个囚禁中的俘虏已心如死灰,不可救药,但他还是像村塾先生教训刁顽小儿那样,很轻蔑地申斥道:“亡国?我们的国家是什么?是华夏子孙,是华夏子孙生养休息的这一片土地。历代王朝更迭,千古兴亡,除旧布新,此乃天下大义。要说亡国,实际上不过是亡君,江山百姓不是依然在么!至于说贰臣,哈哈哈,你赵某连三岁小孩都不如呀,谁人不知,这是特指那些投靠异族而奴役我华夏同胞的汉奸卖国贼!赵某你割舍不了元虏故主,那你就自个儿去吧。”
数日后,三辆槛车将郎革歹、赵成、完者都押往城西大十字刑场,在百姓一片唾骂声中,刀斧手手起刀落,剁下三颗罪恶的人头,算是替大元帝国在巴蜀的统治,画上了结束的句号。
玉珍自至正十七年入川,到至正二十一年,已历四个年头了。乱世中的四川百姓,操什么样口音,打什么样旗号的兵没见过?兵耶?匪耶?官耶?贼耶?谁也分不清。只知道他们像梳子一样梳过城邑乡里,搜刮民财,屠戮小民,蹂躏妇女,已成家常便饭。唯独这支操湖广口音的红巾队伍,不杀不淫,不掳不掠,严惩官府豪强,扶助贫苦百姓,他们才喘过一口气来,稍稍有了粗安的日子。但不久又有传言,说红巾大帅正议讨弑君自立的陈友谅,不日便要出川东归。重庆城中,大街小巷,不由人声沸沸,父老无不相与嗟叹,若生民无主,岂不又是豺狼虎豹要重返乡里了么?
蜀中父老告留,各州各府都有文书递到玉珍的行邸。这些天,刘祯侍讲书史之余,已把民间的舆情多次禀告玉珍了。但玉珍总是蹙眉不展,心有忧思地说:“子弟兵想念故乡,此乃人之常情。唉,每当夜深人静,我何尝又不惦念沔阳父老呵。”
“明公差矣!”刘祯叹息一声,先引用了一番当年蜀汉先主刘玄德入川终成大业的前朝典故,接着慨然陈词道:“明公不是仰慕治水的大禹王么,当年大禹降伏洪水,他的足迹可是走遍了九州呀。凡赤县神州之民,地不分南北,人不论老幼,皆是他的乡亲。在下出山之时,明公可是亲口允诺的要效仿大禹王带领众人治水呵!眼下蜀中,旧官府完蛋了,新衙门刚立起来,生民望治,明公切不可卸肩。再说,元虏未灭,国中仍是兵连祸结,犹如洪水汹汹。而今审时度势,舆情难违,今日之事,明公是该就位陇蜀王了。”
玉珍不允,固让再四。
接着,诸将拥戴,为帅者势难冷了将士之心。数日后,刘祯陪玉珍到城南庙祀徐主,庙堂之上,众将在刘祯的引领下,一一重申了红巾举义,志在灭胡的誓言,这一天,至正二十一年十月望日,玉珍即位陇蜀王。当日,即令刘祯草拟文告,晓谕四方,其辞略曰:
元朝运去,中国豪杰并起而逐之。予本乡农,因乱为众所推,殆为自保,岂敢图人。迩者义兵一起,群丑荡平。予奉天诛罪,岂能自安,幸尔殄灭凶徒,坐收全蜀。是乃天意,夫岂人谋!方今图为画一之规,与民共享太平之治,予非争地杀人之师,乃吊民伐罪之举,特昭告天下,尔辈不可安于元人之陋习,自兹当复见中华文明之化……云云。
四方来贺者络绎不绝。一日,玉珍与新任的王国参谋刘祯同览驿卒送来的各地贺表,对那些官样谀词,玉珍看得有些厌烦,他起身正欲离去,忽听得埋头案牍中的刘祯边看边嚷道:“好一个家奴,竟敢在番市肇事。喔,还索财害命。怎么,他的主子是明昭?这可是人命关天呵……”
“出什么事了?”玉珍停下脚步,回头便问。
原来,刘祯撂开贺表,从一大叠邸报中发现了与播州邻界的地方发生的一桩人命案。刘祯说,那儿是番汉杂居的边镇,受害者乃是苗家一小婢。玉珍听罢案情,不由震怒了。稍顷,他指着邸报上标明的出事地点询问了番市情况,知道身边的参谋熟悉那儿的风土人情,于是,他与刘祯商议了种种对策,最后,他似有预感地相嘱道:“先生是主张王道之化,泽被蛮夷的。你已看出,此事虽小,背后必藏着一篇大文章。我看就由你去那儿,相机下笔破题如何?”
刘祯点头应允。但他说,现在是多事之秋,此去蛮夷之地,一介儒生,尚需一位壮士相助才好。
“谁?在我军中,先生看中谁了?”玉珍问。
“李喜喜。”刘祯笑了笑说,“此次了却差事,尚需一个李喜喜相随。”
出事番市名叫芭茅坪,是播州与内地州县互通有无的商路上一大集镇。一条名叫僰溪的水道从镇边流过,蜿蜒数百里进入重庆府地界,然后注入长江。僰溪上商船络绎不绝,许多白花花的银子,便是由这条黄金水道流入重庆城富商巨贾和达官贵人之家的。在玉珍忙于征讨川北川西的时候,坐镇重庆的万户张文炳和他的外甥明昭,借筹集兵饷之名,控制番市,巧取豪夺,搅得苗汉商民苦不堪言。
陇蜀王即位的文告贴到芭茅坪镇上,苗寨风情,照例要跳喜庆的傩神舞。那一天,三溪十八洞的一群傩神载歌载舞走来了,胡头面具形形色色,头上生角的,嘴如鸟喙的,鼻戴铜环的,咿咿呀呀,如诉如歌。内中有一傩神名叫土地小社婆,黛眉粉腮,头绾高髻,斜插步摇,手持雉尾前导而行。紧随其后的名叫太尉马二郎,赤面涂金,头戴银兜鍪,乘马操槊,叱咤群傩。每至一店铺,店主必是全家出迎,群傩一唱众和,歌舞罗拜,吟诵辞,舞祥瑞,一条沿溪五里长街,好不热闹。但当众傩神行至镇上课税司官署门前,一通锣鼓之后,原本步态婀娜的那个土地小社婆,忽然一个箭步蹿上门前石狮子背上,踮起脚尖高声叫骂,左一个刁吏雁过拔毛,右一个滥官狼心狗肺。这小社婆骂得唾沫横飞,有板有眼。一会儿,几个税吏气哼哼地出来了,为首的那个牙侩模样的人,气得瞪眼大呼:“你们是何路歪神,今日竟要反了不成!”
“大人息怒!兄弟我今日登门,嘻嘻,不过是想讨点银子。”骑马的太尉马二郎一边嬉笑一边扔掉面具——哎呀不妙,此人乃是五面山下来行劫的山大王李君诚。牙侩转身欲逃,只见山大王早已驱马上前,挺槊一刺,牙侩顿时倒地毙命。后面的众傩神也一拥上前,扔了面具,从宽大的袍服中拔出暗藏的兵器,见人就杀,见物就抢,狂呼着一把火烧了课税司,接着又挨家挨户洗劫了街上的店铺商号,一直折腾了一二个时辰,十多匹骡子已驮满了财物,他们才一声呼哨,一股旋风似地溜走了。
当刘祯来到芭茅坪的时候,这番市市面上已是一片萧条冷落的景象。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个边地番市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机巧?这一日,刘祯和李喜喜乔装成江湖上跑生意的两个伙计,寻了个临街的茶馆喝茶闲坐,不动声色地打探茶客们如何闲聊。
“老哥,这是啥世道呀,官即匪,匪即官,做小本生意的,怎么活呵?”
“是呀,好不容易积攒点钱财,一场洗劫,坛坛罐罐全砸碎了,谁家不是连本带利,白白送给强盗了。”
“呃,前些天镇上张贴文告,不是说赶走了元虏,迎来了天完红巾,有个叫明玉珍的陇蜀王,他要与民共享太平,一心要革除元人陋习吗?”
“这位老弟太天真了,过去的元军是官军,现在的红巾还是官军,官军能革除官府的陋习吗?你看红巾官府派来的大小官吏,还不是像元虏官府一样,不知世间廉耻为何物,只会明里暗里搞钱。芭茅镇这个番市,最大的衙门是课税司,那个主管的牙侩,官职不大,却偏能搞钱,拜见税吏要拜见钱,送走要人情钱,诉讼要公事钱,办事要常例钱,逢节要拜节钱,逢生日要拜寿钱,平日无事白要,还兴了个名目叫撒花钱。钱,钱,钱!镇上七十二行数百号店铺,一年到头辛苦挣来的银子,再多也填不满牙侩的税囊呀。”
“你知道这个牙侩是什么人吗?”
“不就是一个家奴呗。”
“哎,芭茅坪本是一个银窝子,金窠窟,谁都想把它攥在手里呀。这个充任牙侩的家奴,你们二位不知,我可清楚,他的主子不是别人,乃是这儿的红巾千户指挥明昭呀。明昭是何人?不就是现今陇蜀王的义子么。”
“噢?”
“哦——”
坐在一旁的刘祯和李喜喜,已听出了事情的一点缘由。喜喜抬起头来,想与邻桌的茶客搭腔,刘祯使眼色制止了他。刘祯一边用茶碗的瓷盖刨着茶水面上的浮茶,一边悠闲地说道:“伙计,这苗岭的云雾毛尖,饮头开茶水,才刚刚品出点味道,你慢慢饮,后头还有更浓酽的馨香呢。”
喜喜会意地回了个眼色,将转过去的头又转回来,二人依旧闲坐闲聊,不动声色地继续倾听茶客们的议论。
“旧官府,新官府,官府中人能与百姓共享太平么?前段日子,那个明昭千户过生日,挨家挨户摊派拜寿钱,河街那个满堂春冷酒馆,蚀本关门走了老板,无钱可交,课税司的税卒就把那个老板娘子捉去示众。老板远在他乡无从得知,可怜那年轻小娘子,囚在衙前木笼里,被撕破薄衫,又脱去筒裙,任由那些地痞二流子抚弄嬉戏。这个弄法还有一个文绉绉的名目,叫什么来着?”
“叫‘晾臀’。”
“那娘子虽是苗寨嫁过来的蛮女,但戏侮她的,多是昔日那些赊账醉酒的垂涎无赖子。她怎么经受得了这般污辱?几日不吃不喝,竟惨死木笼之中。这桩人命案子明明是害死了一位良家妇女,官府却说不过死了一个苗寨小婢,明千户按一头驴子的价格,赔偿了就算完事。唉,唉!”
“蹊跷事还多着呢,幺叔。前些天的那次山贼洗劫市井,杀牙侩的马二郎自是山大王李君诚,那个持雉尾前导的土地小社婆,你们窥破了她真面貌吗?我当时挤在人堆里看热闹,就在她的身后不远处,看她的身段、步态,听她叫骂声,我十之八九已猜到,她就是镇上聚宝源樊家的三女儿翠花!”
“别瞎说,大侄子。翠花几个月前已做了明千户的宠妾,你不怕割舌头吗?”
“是呀,是呀,明千户的宠妾,怎么会引着山贼去杀他的牙侩家奴呢?”
“你脑袋瓜真傻!你脑筋转个弯来想想,听说重庆府来了专使巡察,要重审冷酒馆老板娘子的人命案。这个牵扯就太大了,牙侩家奴是一条线索,他要吐出内情不是很危险吗?”
“哦,这叫先下手为强,杀人灭口!”
刘祯依旧低头品茶,又不时抬头瞟一瞟门前的街景,一副全然不理会茶客议论的模样,其实,他每句话都听得仔细分明。李喜喜也学得老练些了,只是时不时唠叨几句跑江湖做生意的事儿,也装出一副并不在意别人的样子。但他毕竟压抑不住内心的惊喜,当茶倌提着长嘴壶冲过开水后,也不由得说道:“我说伙计,这第二开茶水,味道果真更浓更酽了。”言罢,二人会意一笑,又继续倾听下去。
“那明千户是何等厉害的人物,他要干掉一个家奴,不过是摁死一只蚂蚁,还需得着请李君诚出山吗?表兄你恐怕是多疑了。”
“嗨,你又是一个傻瓜,幺表弟。前面那位老伯不是看透了这个世道,官即匪,匪即官,官匪原本是一家嘛。”
“咦——,你是说明千户勾结了五面山的李君诚?”
“官匪一家这个理,你不信我信。你看五面山草贼出来打劫芭茅坪,哪次官兵在场?每次都是强盗打劫完事驮起包袱走了,官兵才赶来佯装追击,杀声震天追了十里八里,却不见抓回一个强盗喽啰,谁能担保他们不是同谋策划,事后暗地分赃呢。”
“唉,唉,新官府,旧官府,说来说去,旧瓶新瓶装的都是同一窖酒。”
“岂止一样?那个明千户,贪财又好色,他搞走了银子,还要搞芭茅坪的女人呢。”
“谁?——哦,我明白了,你是说他新娶的宠妾翠花。可翠花姑娘明明是官兵攻打五面山,明千户从山寨中把她救出来的呀。”
“你这个傻瓜又犯傻了。你想想,那次官兵进山,两军交战无一伤亡,单单就夺回一个压寨夫人,打仗就这般儿戏?不过是做戏障人眼目,这明明是李君诚拱手相送嘛。”
“这么说来,明千户是真的暗通五面山草贼了。但这次重庆府来了办案专使,他又让李君诚下山打劫,这不是太暴露了吗?”
“暴露?暴露了才好哇。借山贼李君诚之手,杀自家家奴灭口,这叫借刀杀人。暴露了那个打家劫舍的山大王,让专使大人自个儿捉他去了案,自己溜之大吉,这叫放虎归山。一计套一计,环环紧扣,你说这是不是一石三鸟!”
“好一条奸人奸计!哎哟,看来那位一头雾水的办案使者,只能白跑一趟空路了。”
……茶客议论,没完没了。乔装成外来伙计的刘祯和李喜喜,摸到了案情底细,线索自然就清晰了。正当喜喜挤眉弄眼,凑近刘祯耳根悄声道:“伙计,这趟生意你掂掂能赚多少银子?你说我们哥儿俩老大远走来,会不会白跑冤枉路?”喜喜话音刚落,未料街上骤然敲响了锣声,几个衙卒操着破嗓吼叫不休:“戒严了,戒严了!绅乡士民听着,良民各自归家,凡有窝藏奸人强盗者,立即缉拿送官!”
顷刻间,街上行人慌忙奔避,茶客们也一哄而散。刘祯连忙携了喜喜,赶紧离开茶馆,匆匆返回了停在僰溪边的一条商船上。这条商船很轻便,船舱隐蔽,航速极快,是刘祯一行离开重庆时,玉珍特意为他备办的。
是夜,僰溪上清风徐徐,一轮明月从东山冉冉升起。因是戒严,江上画舫已没有了往日的艺伎弦歌,只有渔火点点,往来于沙汀水渚之间。喜喜吩咐乔装成船夫船老大的随从军卒,到邻近的渔舟上取来几尾鲜鱼,弄出几样鱼烩酒肴,便在舱中同刘祯先生小酌起来。他们一行来到这个边地番市,市井乡里,陆上水上已暗中察访近旬日了,一篇破案文章的思路现在算是理顺了。俗话说,妙手偶得,是夜,刘、李二人对饮尚未微酣,一个偶然的机会突然闯来了。一个预先安插在明昭驻地的探子急匆匆递来一封蜡丸密信,信中说这些天明昭焦躁不安,从玉珍身边来的使者到了他的地盘却又迟迟不露面,他甚是惶恐心虚,担心他那一石三鸟的名堂会被别人识破,又害怕那位未曾谋面的“钦差”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亮出玉珍手令,领兵前去围了五面山,随便捉几个喽啰逼出口供,他明昭岂不是要露马脚?烦躁的明昭百般无奈,今夜他已派出一个贴身亲信,前去一个叫响水桥的哨卡,密会山大王李君诚。
“先生,事不宜迟,我这就去捉那亲信当活口,以了结这桩公案。”喜喜扔了酒杯,迅疾装束,灯火下,他背上斜插的钢刀闪闪发亮。
“好兄弟,今夜事发唐突,但也在意料之中。”刘祯轻叹道。他探头望了望舱外,江上起风了,朦朦胧胧的月亮不知几时已藏入云絮之中。刘祯再次打量了一下喜喜的装束,轻声叮嘱道:“响水桥那个地方前日我们去过,确有一个哨卡。那儿离此三十里,你走后我们即开船下行,下游十五里处,即是响水溪汇入僰溪的一处无名水沱,待会我就在那里候你归来。我仔细思谋过了,喜喜你记住,此去勿须滥杀,也不要惊动了明昭身边的那个亲信,捉人不捉别个,只捉山贼李君诚!”
李喜喜轻应一声:“得令!”转身钻出船舱,一个鹞子翻身,双脚落在岸上,一眨眼工夫,那轻燕般的身影便消失在茫茫夜幕之中了。
响水桥是一个荒僻隐蔽的去处。山林峡谷中有一条溪流急急淌过,不知起于何时,有人就近伐倒两棵百年古树横卧溪上,这便是出山的一座桥。因五面山出了山贼,这寂静的空谷没有人家,连往日的猎户也迁走了。响水桥哨卡是官军监视五面山的一处前沿哨所,平日发现情况,备有快马传递消息。哨所是一座小院,一圈围墙中有一幢一楼一底的哨楼,立于桥的一侧。对岸则是藤萝缠绕的一片密林。这个夜晚,确有一个青年军校带着两名侍卒,匆匆赶来替换了原来的戍卒,并打发戍卒回军营去了。此行身负特殊使命嘛,不得不避一避嫌疑。
当李喜喜心急火燎赶了三十里路来到桥畔的时候,月儿早已钻出了云层,四周一片朦朦胧胧的月色,看来时辰还不太晚。喜喜钻进丛林,桥西桥东察看了一遍,没发现什么异样。哨楼中三人,一军校在楼上,二侍卒立于小院门前。山中虫鸣唧唧,看来那五面山的来客尚未到达。喜喜隐于暗处,静静地谛听着桥畔的来路有无响动。
“看来那个军校就是明昭的亲信了。先生嘱我勿滥杀,不要惊动他。这军校是谁?他能把山贼李君诚召唤得来吗?”喜喜暗忖着,不由转身挨近哨楼。那两个侍卒已关了院门进去了,喜喜纵身跳入院中,蹑脚走近楼下房间的窗下,忽听得里面是两个女人的声音。
“姐,你说今夜山大王会来吗?”
“明将军约定好了的,他怎会不来。”
“姐,你看明将军怪也不怪,要约见别人,他自己又不来。半夜三更的,在这荒谷中,偏偏叫我们三个女人来伺候一个草头王。”
“你害怕了吗,傻妹子,伺候李君诚轮不到我俩,楼上那位军校,才是他的旧情人呢。”
喜喜心下一惊:“哟,来者三人,怎么会是女兵?”接着他又犯疑,莫非明昭又在玩什么诡计?
“你是说翠花姐?翠花姐不是明将军新娶的娘子吗?他肯舍得?”
“舍得舍不得都是一回事。妹子你知道翠花的来历吗?这个芭茅镇上的富户千金,从小就是一匹不受调教的牝马,街坊中的娘儿们都知道,她十五岁那年,情窦初开,早被街上的浮浪子弟偷偷地破了瓜,父母囚她于闺阁,好不容易磨过了几年难耐的怀春时光,而今是十八九岁的大姑娘了,出落得十分俏丽风骚,一副人见人爱的狐媚模样。这翠花姑娘,自幼惯听街坊娘儿们谈论山贼打家劫舍的故事,她早就暗恋那个剽悍豪俊的山大王了,新来的明将军风流,他俩一见钟情,一下又成了军帐中的鸳鸯。哎,女人风情万种,男人窃玉偷香……好了,不说这些,反正这趟差事该当她来,山大王今夜也不得不来。好了好了,今天赶路太累了,烫了脚上床睡吧。”
喜喜听得一头雾水,他正在理着事情的一些来龙去脉,忽儿吱的一声,窗门开了,一盆水泼出来,水星子溅到了喜喜身上。他连忙闪身离去,一纵身,又跳到了墙外。
喜喜在一处丛林藏身,一直等到午夜时分,桥对岸的来路上终于有了动静。那一片藤萝缠绕的山林里,忽然响起了猫头鹰的叫声,接着,有人钻出密林,在溪边打出一支火把,一左一右摇动了三次。暗号,这是接头的暗号。喜喜回头看时,果然哨所二楼的走廊上,有只红红的灯笼正在回应火把,也一左一右来回晃动了三下。喜喜定睛一瞧,那个人影已飘过木桥,接着翻墙入院,很快便飞身上楼,一头钻进楼上房间里去了。
不消说,喜喜紧随那个人影,也飞身上了哨楼,蹑手蹑脚藏于窗下。这时,屋里有人悄声说话,声音压得很低,但很亲昵:
“君诚,我大老远赶来,是给你带来明将军的一个口信,官军又要进山清剿了。”这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喜喜用舌头舔破窗纸,往里偷觑,哟,那个青年军校已脱去戎装,露出桃红薄衫,好一个玉颈耸乳,纤腰丰臀的小娘儿。
“官军又要撵我走了?翠花。”这山中来贼正是李君诚,个儿不高,乍看像个书生,但他转过身来,嘴上那一撇黑黑的短髭连着两腮的鬓胡,却是一副江湖强盗的模样。
“不就是猫捉老鼠的游戏嘛。——怎么,你怨我不该来报信?”翠花娇嗔着,丢下一个媚眼,又用手指点了点贼人的额头。
“乖乖,当日的压寨夫人回来了,我想你都来不及呢,还怨?”这短髭连鬓胡的贼人,一抬手,捏住小娘子的玉腕,一下将她搂进怀里,心呀肝呀地哼着,边搓揉边褪去她的衣裤,顷刻间,两个赤条条的身子纠缠在一起,就倒在屋角戍卒夜宿的地铺上翻滚起来……
青巾出身的喜喜,对眼前贼人入室奸人妻女的情景见惯不惊,不外乎强贼长枪大戟,女人呻吟不止。但今夜这对男女,似乎又有些异样,一番颠鸾倒凤,几度云雨绸缪之后,那娘子止住呻吟翻身而起,好几次捂着酥胸干呕着,欲吐不吐。一旁的贼人似乎醒悟到了什么,待她转过身来,这才注意到女人的小腹已微微凸起,——哦,她怀上了。
“翠花,恭喜你了。你几时让那千户大人下的种?”贼人也有酸溜溜的时候,脸上布满了嫉妒。
“谁下的种?君诚,别人不清楚,难道你也糊涂?奴家同你相好是什么时候,你送我去做明昭之妾又是什么时候?你这个醋罐子好没良心,这是奴家与君诚你同衾共枕结的果呀!”女人撒着娇,又一下偎进贼人的怀里。
屋里灯灭了,黑暗中时不时蹿出几声女人的娇吟,贼人的嬉笑。喜喜几次想破窗而入,一刀宰了这对狗男女。但刘祯先生行前有叮嘱,他不得不按捺住杀人的冲动,相机等候着如何下手擒贼。
约莫半个时辰过去,贼人终于起身辞行了。
“君诚你记住,下次奴家仍来这儿候你。”这是女人在惜别。
“翠花,你天亮就回去吧,下次我来,下一次……”山贼李君诚要回山了。可是,他哪里料到,他已没有下一次了。
山贼李君诚出了哨所小院,过了溪上木桥,来到密林中,发现他预先拴在这儿的坐骑不见了。他正在诧异,没提防头上突然落下一张大网,哗啦一声,将他罩住,紧接着,便被别人像捆粽子一样将他严严实实捆缚起来了。不用说,这是李喜喜遵照刘祯先生的锦囊妙计,在这个深山荒谷里,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擒拿了五面山的贼首草头王。
坐骑从林中牵出来了,李喜喜骑于马上,顺手将捆缚的山贼置于马后,连夜赶路。是夜,在月儿西沉,残夜将尽的五更时分,他赶到了响水溪汇入僰溪的那个无名水沱,果然,刘祯先生已泊舟水边,船夫船老大一行人,同先生一道已等候他多时了。
人犯已缉拿归案。刘祯将喜喜让进船舱,随即扬手轻喝一声:“船老大,解缆开船!”一条重庆来的轻便商船,泊于番市,未惊动官军的一兵一卒,旬日后便奏捷音,又静悄悄地挂帆急行,星夜兼程返回重庆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