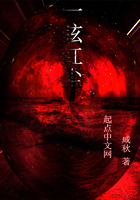嘉定,九顶山大佛崖。
红巾攻打省城的消息传来,元军军寨一片骚然。郎革歹、赵成所部,乃是元朝地方政府的官军,将士的家眷都在锦官城,他们是别了父母妻儿,跟随主将南下嘉定来阻击红巾的,现在失了老巢,家小性命难保,上上下下,谁不军心浮动,垂头丧气?已有士卒弃甲遁逃,赵成巡寨时抓住几个开小差的逃兵,气得亲手将逃卒戮于营门,并把他们血淋淋的人头枭首寨中,以示儆尤。
赵成回到军帐,郎革歹、完者都二将早已等候在那里。
“派往汉中求援的使者有回音吗?”赵成没好气地问。
“有。”完者都一脸晦气,他自知一个丧师败将,说话得看别人的脸色,他偷偷地瞟了参政大人一眼,压低声音道:“回信不太妙。大都朝廷原本派了钦差督促李思齐大帅出兵四川,钦差到时,李大帅已率军南下,可钦差一走,李大帅又按兵不动。使者的密信上说得很清楚,李思齐前次派兵入川吃了苦头,这次他死活不愿入川,他是在汉中同钦差玩迷藏呢。”
“这个老滑头!北面的援军是无望了。”赵成愤愤然。
“黑了北方有南方嘛,二位将军,云南的梁王有使者到了。”郎革歹自恃他乃朝廷亲贵,虽是败军之将但仍端着平章大人的架子,大咧咧地说:“大元江山,乃世祖子孙的江山,梁王本是世祖裔孙,坐镇云南兵强马壮,邻省有危,他能坐视不救吗?”
“来了多少兵?打到了什么地方?”完者都似乎拾到了一根救命的稻草。
“王爷的官军,加上所属溪洞蛮兵,号称十万,已入播南,直扑明玉珍的老巢重庆府了。”郎革歹捋着颔下几根稀疏的花白胡须,干瘦的脸上,露出几分不屑与下僚计较的微笑。
“重庆?重庆距嘉定几千里,何况播州距重庆又有几千里。这些蒙古亲贵,真他妈全是扯淡,你虚张一下声势,那红巾贼就能后撤吗?”赵成在心底里臭骂着远方的梁王和面前这两个蒙古上司,但他毕竟身处下僚,不敢发作。转而还不得不佯装惊喜,捎带也表白一下自己:“想我赵成祖上,也是跟随世祖打江山的奴才,奴不背主乃我赵家的家风。虽说大佛崖已困半年,兵已疲,粮将尽,但有梁王雄兵十万来援,前后夹攻红巾贼,奏捷在即,现在该振作振作士气了。”
元寨三将正议论间,山下又响起了一片鼓噪,红巾又一次前来攻寨了。赵成严令闭寨不战,只以弓弩炮矢还击。数日过去,果然不出他之所料,南面有探子回来禀报,梁王的官军在播南吃了败仗,现已慌忙退回云南去了。赵成烦躁透了,他料想那位从重庆来的逃跑将军完者都,又会向他嘟囔着三十六计走为上了。可这次完者都没来,倒是郞革歹颓丧着一张瘦脸,气喘吁吁地爬上山寨来献计了:“赵将军,乌牛山的覆灭是前车之鉴。眼下红巾草寇来势汹汹,大佛崖虽说峭壁环立,但还有一条路可通山上,你看红巾贼神出鬼没,这条通道现在是非断不可了!”
赵成不解:“所有的上山之路,不是早已断绝了吗?”
“咳,我说的是凌云寺的大像阁,那七层十三重檐的大佛菩萨风雨楼阁,平日香客朝拜大佛,就是踏着那些楼梯上山的。我看,今日就一炬烧了它吧!”郞革歹喘息稍定,回头吩咐他身后随行的亲兵立即动手。
赵成原本一脸阴沉,蹙眉不展。这些日子他衣不解甲,眠不弃戈,昼夜不停地巡察各处哨口,未想到就在他的脚底下,大佛崖防御系统竟有如此一大漏洞。他望了一眼那依山攀岩层层勾连的大佛风雨楼,不禁颓然叹息道:“噢,不是平章大人明察,末将险些疏忽误了大事了。”接着,他扭过头来,声嘶力竭地喝令守寨的军卒:“你们愣着干什么,人都不保,还顾得了菩萨?众军士听着,照平章大人的军令,赶快准备柴火!”
玉珍在嘉定,掐指算着万胜奔袭成都的日子,不久,快马来报,红巾进了省城,不几日即将回师。这一天,玉珍趁着好心情,邀了几位嘉定耆老来江边闲话,几杯清茶代酒,这位红巾赭服的大帅,竟同几位布衣父老聊得十分投契。
“大帅,这些年天下多事,江湖上奇人也多。呃,你听说过嘉定大佛化作布袋僧的故事吗?”一个身着短衣牛犊裤的樵父提起话头。
“布袋僧?那个袒腹如布袋,跛足过市的和尚,你们见着了?”玉珍好生惊喜。
“这个布袋和尚,还爱搭乘我的渔舟,经常往返岷江两岸呢。哦,对了,那和尚每过闹市,总喜欢唱一首歌谣。”另一位白胡子渔翁接上了话茬。
“歌谣?他又唱什么了?”玉珍想起了他入蜀之初,曾碰见这个奇怪游僧的情景。
樵父和渔翁,二位父老几乎是异口同声,一齐轻轻哼了起来——
穷也一笔火,
富也一笔火。
待到日月双双出,
西蜀家家一笔火。
“噢——”玉珍暗自吃惊,好一个谶语箴言,这个“日、月双双出”,不就是个“明”字吗?但那一笔火,又是指的什么呢?
两位乡野耆老,笑了笑说,那年嘉定城门外,一对贫苦老夫妻在自家茅屋前卖茶为生,一位过路的大肚僧人可怜他们寒冬挨冻,挥笔在纸上写了个“一”字,悬于室中,“一”字化作火棍,顿时温暖如春,卖茶生意也兴隆起来。但奇闻传开,城里知县大老爷便将那宝物夺了去,供在他的府上,殊不知,那“一”字竟化作烈火,呼呼一气竟连人带屋烧了个精光。传说那和尚渡江而去,进入对岸凌云寺,便一下消失了踪影。
“火,火!”忽然,眼尖的樵父指着对岸惊呼起来。
“啊呀,大佛崖起火了!”白胡子渔翁也大惊失色。
“狗杂种,官军狗急跳墙了。”玉珍激愤地骂一声,他望见对岸山顶的元寨营盘,如飞蝗般的火把掷向凌云寺大像阁。火借风势,风助火威,可怜那专为大佛菩萨遮风避雨的七层十三重檐的巍巍楼阁,依山傍岩气如凌云的古刹琼楼,刹那间陷入一片兵燹火海之中。烈焰滚滚,大佛崖下的元军水寨也着火了,人影憧憧,一片慌乱。玉珍觑得性起,立时顶盔贯甲,跃上江边的战船,令士卒摇旗擂鼓,向对岸乱军发起又一轮攻击。
红巾战船驶到江心,发现元军水寨已成一座空寨,水面上到处漂浮着断桨残樯,寨内狼藉不堪,官军已弃寨上山了。
江风阵阵,待到面前的大佛崖烟焰散尽,昔日香客云集的古刹,已在这场突来的兵燹中倾覆,七层十三重檐的大像阁,转眼间已灰飞烟灭,余烬中唯一留下来的,就只有那尊凿山石摩崖而造的大佛菩萨了。
“好大一座佛像!”玉珍惊叹一声。但他举目端详时,觉得面前这尊弥勒佛坐像,似乎又很陌生。佛像远眺前方,只见他双目欲睁似闭,神态非常肃穆庄严,一副俯视芸芸众生而自己却高踞云端之上的尊颜。“哦,原来此佛非彼佛,这是一副王者之像呵。”玉珍喃喃自语之后,不由面向大佛,举手长长一揖,算是长揖致礼了。
“大帅,你面前是普度众生的弥勒佛,若要求神祇护佑,你得赶快跪拜,赶快跪拜呀!”不知什么时候,渔翁与樵父也驾着一叶扁舟,尾随而来,他们向玉珍高声呼喊。
玉珍瞥了一眼樵父渔翁,他面朝大佛,又是长长地一揖,算是再一次长揖致礼了。
渔翁樵父生气了,两位耆老齐声责问:“大帅不是弥勒教信徒么,大佛面前,岂能长揖不拜?”
玉珍转过头来,笑了笑,面对扁舟上的嘉定耆老,他只能略做解释:“二位老伯,你们弄错了。此佛乃王者之像,非我明教之弥勒,我们明教有教规,不拜王者,凡教徒从不拜王者!”
“大帅不是敬仰布袋僧么,布袋僧赐我百姓一笔火,他的归宿就在此呀?”两位耆老仍是生气地争辩。
“你们又弄错了,二位老伯。”玉珍仍是谦和地笑着,他比画了一下布袋僧的形象,以熟知详情的口吻继续说道:“我亲眼见过布袋僧,我同他打过几次交道。我看这儿并非布袋僧的归宿,如果他来过这里,但依我看,他一定是又与大佛擦身而过了。”
“噢,这么说来,大帅所拜之佛,非此佛,乃彼佛,但彼佛又在哪里呀?”两位老伯相对而语。老人家似乎听见过民间传言,造反的红巾可不是以往那类只会以钱帛贿赂菩萨的香客,他们心中自有弥勒,但这心中之佛究竟是什么模样呢?
玉珍战船返航的时候,他们是背对大佛远离大佛了。归途中,嘉定耆老仍在唠叨,说那位济贫民惩贪官的布袋和尚,一定是弥勒佛在人世间的现身说法者了。红巾大帅时而摇头,时而又点头。末了,玉珍想了想说道:
“我们红巾将士也拜弥勒佛,不过,他不是昔日庙堂之上的巍巍王者。要是日后我为他塑像,这弥勒佛是个什么模样儿呢?其实父老们都很熟悉,他常在我们身边,这么说吧,他慈和又睿智,亲切又大度,要说他的模样,不就是我们天天都见到的那些慈祥宽厚笑口常开的邻家翁么?弥勒,邻家翁也。二位老伯,你们信不信,邻家翁才是弥勒佛呢……”
明玉珍的嘉定之战,可谓打得从容又潇洒。攻下州城,得了省城,剩下的元军残部烧了大像阁,退缩在孤立无援的九顶山上,收拾这赵成、郎革歹一伙,不过是兵锋所向,风卷残云而已了。
但现在元军弃了江边水寨,藏身九顶山中,犹如鱼归深潭,眼下,还有什么香饵能诱敌就擒呢?不消说,红巾在省城生俘的元将家眷,自然就是楚河汉界刀兵相见一盘棋上,能攻心为上,出奇制胜的一颗棋子了。虽说路途行船,平章夫人已投江自尽,好在参政夫人汪氏母子换乘一辆小车,总算一路顺利,到了嘉定。
汪氏安歇馆舍,红巾以礼相待,不辱不欺。她先是诧异,后来终至感动了。官府不是说这是一群杀人放火,抢财物抢女人的青面獠牙之徒么,城破之日,吓得多少官眷悬梁自尽,幸亏她在红巾军中多呆了些日子,亲眼目睹了这些造反的红巾,不过是一张张年轻而又淳朴的面孔,他们说话客气,待人礼貌,彼此间宛若兄弟姐妹。消除了恐惧,她又想,我一个弱女子,他们把我带来,又派得上什么用场呢?
“你夫君也是华夏子孙,你愿意让他去为元虏卖命吗?”玉珍慰问她一番后,和气地问。
汪氏低下头去,嗫嚅着说:“夫君糊涂呀。”
“红巾从不嗜杀。现在我给他两条路,赵参政若能弃暗投明,反戈一击,我明玉珍愿同他共驱元虏。若赵参政厌倦仕途,想远离是非之地,我也可以网开一面,让他携妻带子,回他老家去过清闲日子。女人的心比男人精细,夫君糊涂夫人可不糊涂呢。明日阵前,我想请夫人把这些话捎带给他,不知夫人肯帮忙否?”玉珍说得很诚恳,毫无催逼的意思。
汪氏抬起头来,感激地盯着面前这位红巾大帅,大胆回答道:“大帅开恩,罪妾敢不从命!”
翌日,是女人在山下撕心裂肺的哭喊,使山上的元将再也沉不住气了。他们倾巢而出,鼓噪着要来个鱼死网破,决一雌雄。
两军摆开阵势,各以弓箭压住阵脚。赵成与郎革歹,并辔立于元军阵前,他们都以焦灼的两眼,紧盯着对方旌旗招展处,迎面而立的汪氏母子。
“参政大人都看见了,红巾大帅待我母子,不杀不侮,礼为上宾!”汪氏携着她身边的幼子锁儿,隔阵大声呼喊。
赵成认出来了,喊话的女人确是他的结发之妻,女人身边的小孩儿,确是平日嬉戏于他膝下的锁儿,他正想搭话,忽听得身旁的郎革歹抢先喊道:“汪氏,我问你,与你同来的平章夫人何在?”
赵成瞟了一眼郎革歹那张青筋暴凸的瘦脸,心如猫抓一般烦躁起来,他见汪氏一时语塞,不得不圆睁怒目,喝问道:“贱妇,你要为红巾贼当说客么?”
汪氏伤心地哭泣着,陈述了红巾给的两条出路后,不由号啕着大呼:“我们回家吧!老父老母还在高堂,老人家哪一天不念着你解甲归田呀!”
“爹,爹爹,我要到奶奶那里去!”锁儿也号啕着,哭喊不休。
立在赵成、郎革歹身后的完者都,忽听见阵前有人抽泣哽咽,他偷偷侧目一瞧,糟糕,那些手持弓箭的官军士卒,一个个耷拉着脑袋,好些人已泪流满面了。是汪氏母子的哭喊牵动了士卒的思乡之情,军心已动摇,再任这女人哭喊下去,官军将不战而溃了。他连忙上前,给郎革歹使了个眼色,便大声责问道:“汪氏你玩的什么把戏,你自己归顺了草贼,还想骗人上当么。听着,我问你,平章夫人投水了,你却成了草贼中人,一死一生,一殉节一苟活,此为何故?”
赵成焦躁难抑,他闷喝一声,立时挽弓在手,从箭囊里连抽两箭,扣上弓弦。这时,他听见郎革歹又发出一声讥笑:“恐怕这娘们早已是他人的压寨夫人了,赵将军,你还存妇人之仁吗?”
赵成再次闷喝一声,“嗖,嗖!”两箭连发,只听箭羽响处,一箭直射汪氏心窝,可怜这结发娇妻,顿时毙命,另一箭直向锁儿咽喉飞去,红巾士卒蜂拥而上,以盾牌挡住来矢,总算把这小孩儿救了下来。
元将杀妻灭子的暴行,将战阵两边的士卒都一下激怒了。玉珍看得分明,他大喝一声,一马当先冲向敌阵,红巾将士如排山倒海一般杀了过去。早已埋伏在敌军侧背的万胜,也鸣炮挥军掩杀,前后夹击,元军立时大溃。奔逃的元军三将,不知是被红巾的流矢,还是元兵的乱箭所射中,三将先后落马,被捆缚在马后,拖回了红巾的军营。
营门前,盛怒的红巾大帅唰地抽出佩剑,他要亲手戮了这元将“三凶”,以谢民愤军怒。但正当他喝令“推出去”的时候,却有一个人匆匆赶来,见着玉珍便连呼:“元帅息怒,元帅息怒!现在不是杀人的时候,此三人即使罪不可赦,罪不容诛,也须押回重庆,布告天下,数其罪而明正典刑!”
玉珍抬头看时,来者不是别人,乃是新近所得的泸州儒士刘祯。玉珍叹息一声,向立于营门的行刑队摆摆手,他转过身来,不由得将自己抽出的宝剑,又缓缓地插回了剑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