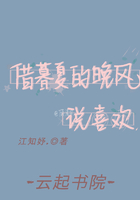(1)陌生又熟悉的人
小时候走亲戚基本就是去外公家。在山里边,环境与我们家大相径庭。我怕踩不稳那窄且滑的田埂,一不留神或掉水田里;怕时常出没的狗、猪、鸡,还有羊;怕沿着一路列着队的陌生坟墓……
就像我爸妈慈父严母的组合风格,外公外婆亦如是。外婆与我的交集很少,外公对我来说却很有亲切感。实际上,他们有八个子女,孙辈更多,且农村老人血缘意识浓厚,他们的宝贝孙女自然是心头肉,我在他们心目中,当是那个“别家的孩子”,那个对孙女而言应该学习的榜样。
我很理解外公的偏爱,就像婆婆唯独溺爱我一样,也都是不理性的。
我每次去镇上赶集都会去茶馆找他,我跟别人说,我外公在里面打牌,是那种我一点也看不懂的长牌。
前几年我多次去探望年迈的外公,他与我说:洋洋,你应该去当空姐,或者老师/洋洋,你学习很好/洋洋,你什么时候毕业?……我考上大学时他给我包了六百红包,我感动了很久,猜想我在他的外孙行列里算是比较被疼爱的么?
那叠钱,是外公给我的,庆贺我考上大学的,而我,从小就口口声声说过我长大要还外公——煤油钱。
(2)永远欠着的煤油钱
与外公的故事,是关于一盏煤油灯。
去外公外婆家,晚上我从来都是与外公睡。他们家是四合院土房,U形布局,外公的床铺在后门小房间里,只有一架床和一个柜子以及上面的一台黑白电视机。
帐子漆黑、夜晚漆黑,我睡不着觉。
“外公,我要点灯,我怕黑。”
“洋洋不怕,有外公在。”
“不嘛,我要点煤油灯……”
外公无奈,只得笑呵呵地遵照我的指示,将灯点燃。要知道,农村那会儿很穷,如果被外婆发现说不定我俩都会被批斗。
不过每次我都要夜里点灯,煤油灯火光清亮,照得整个房间都亮堂不少,伸手还能比划各种剪影。
外公每每都与我说:洋洋,你可又欠了我好多煤油钱……
我笑盈盈地回道:等我长大,我会还很多很多煤油钱给外公的!哈哈哈
(3)曲终人散
外公独自住在层高十几楼的房子里,一推门,浓烈的叶子烟气味扑面而来,混合着不知名的过期食物的臭味。
妈妈二话不说去整理,洗衣做饭,偷偷扔掉搁置许久许久的剩菜。我站在唯一有新鲜空气的窗口,身侧外公躺在床上认真地看电视,那张沟壑纵深的脸,那副固执的脾性,以及那杆叶子烟……他时常说新闻联播前要放天气预报……实际上他的老花眼根本看不清画面。
什么时候外公与我们之间的对话都变成了客套?他问我学习怎么样,问我妈工作辛苦吧,非常客套生疏的表述。讲到他的两个儿子,气不打一处来。我时不时会忍不住说一大堆他根本无法理解,或者不在同一频道的话。
当然,我耐心的劝导也能起到短暂的作用,他笑呵呵地望着我,点头答应,好像一个小孩。
但转眼说到心中郁结,又是唉声叹气。难道人老了都这般执拗?都非弄得自己不开心?年轻时大度开朗的外公已经随时间越走越远……
那日,他直挺挺躺在地板上,全身被白布包裹着。我眼眶一下子润湿了。儿女们在说什么,好像与他无关,但很吵闹。
我搀扶着妈妈,跟着人群去观火化仪式。外公的身体被推进熔炉……许久之后,出来一堆白色骨骸,工作人员戴着口罩,熟练到漠然地用锤子将其敲碎,装进骨灰盒里。那个我曾熟悉的人,在那一刻永远的离开了,彼此的记忆越来越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