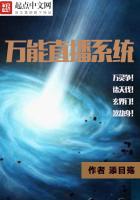望江楼上又是一番觥筹交错,诗词歌赋,不用细说。此刻私塾成立,贾迪当晚就回到白话堂住下。
第二天一早,贾迪爬起来,匆忙洗漱,打开大门,把早已准备好的木牌搬出来立在门口。然后,贾迪在对面的路口买了两个包子,一边吃着,一边看着木牌上自己写的招生启事:
本私塾专以教授大众白话为宗旨,
如有愿学者,无论男女老少,皆可随时前来听讲
无需任何费用
贾迪现在对自己的毛笔书法还是稍微满意的,以前在后世练过,现在更是一有空就写一些,反正古代娱乐节目也不多,权当消遣。贾迪相信,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或明或暗的宣传,自己办私塾教授白话文这个消息在这小小的黄州几乎是妇孺皆知了,原本不打算写什么启示之类的,但转念一想,私塾的地方估计知道的人还不是很多,而且是第一天,总得弄点气势出来,所以就找了木板随便写了几句,立在门前。
正如贾迪所料,黄州的老百姓都知道今天私塾开业了,除了偏远的,那些有小孩但又无力供其读书的人家,大多带着小孩过来看。就连那些富家子弟,或一干闲杂人等,也跑过来看热闹。不一会儿,门口就聚集起一群人。贾迪,吃完包子,就好像小贩一样,对着街道开始吆喝了,一见人多了,更是大着嗓门,将招生启示一遍又一遍的读出来,不时解释一番。
众人都仿佛听说书一般,津津有味,有那想把孩子送过来的,却又一脸踌躇,不肯做这个出头鸟。
这时,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牵着自家七八岁的孩子,挤过人群。细细的打量了贾迪一番,才上得前来,先朝贾迪拱拱手,然后又命小孩跪下给贾迪磕头。慌得贾迪急忙扶起小孩。一问,才知道这杨姓老汉,是从十里之外的杨家村赶来,前几日听到了消息,天还没亮就爬起来,带着孙子,来入学的。贾迪望着眼前这个怯生生的小孩,细细端详。小孩约莫五六岁了,又长又浓的眉毛下面,一双圆圆的大眼睛。大概贾迪刚才亲切的举动,消除了小孩的一丝紧张和腼腆,一边抓着爷爷的手,一边伸真脑袋往门里眺望,还不时偷瞥着贾迪。
贾迪一看这孩子长得眉清目秀,人又显得机灵,顿时大生好感,又见这是“吃螃蟹的第一人”,是自己的第一名学生,和老人交谈几句之后,笑呵呵的蹲下身,对着小孩问道:“小朋友,叫什么名字啊?想读书么?”旁边的围观者一听,虽然是头一次听见“小朋友”这个名词,但也猜测得到是“小友”的意思,不由一阵嬉笑:老师称学生为友?看来这位贾公子太可爱了,可爱得有点疯疯癫癫了。怪不得一天“不务正业”,搞这么个私塾。那小孩一听众人嬉笑,又看见贾迪这个大块头蹲着在自己前面,一阵紧张,磕磕绊绊的说,“我,是杨村的,我叫杨晔,小名,小名狗儿。”这时,贾迪也忍不住,和众人一起笑起来。伸出手,一把抱住小孩,然后站起身,当着众人的面,对杨晔说,“小晔,不要怕,老师以后好好的教你念书识字,好不好。”那杨晔几时见过这样的,在来的路上,自己的爷爷可是千叮万嘱的,却没有料到贾迪不但不是板着个脸拿这个戒尺,而且还采用如此和蔼可亲。一时半会不知道怎么回答,只是一边看着爷爷,一边羞答答地点着头。
贾迪本来就站在门前的高处,众人在下面看得是清清楚楚。这些人,何曾见过来自后世的如此“温情作秀”,顿时全都被征服了!有几个本来是被大人牵着来的小孩,此刻竟然拉着大人们的手,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似乎也想上去“表扬”一下。
。。。。。。。
一天下来,贾迪坐在灯下,兴致勃勃的看着学员名单,包括那个杨晔在内,总共九人,恩,黄州人口本来就少,一开张就能有这九个,算是很不错了。贾迪心中高兴的安慰自己,“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全都是小男孩,自己那个什么不分男女老少,似乎是一种奢望。”。。。。。。拿起前些天自己编写的课文,绞尽脑汁的揣摩起来。。。。。。最后不知不觉,竟伏在案上睡着了。
当贾迪正沉浸在宋朝从事教育工作的美妙情景之时,一阵“咚咚”的敲门声将其惊醒。当贾迪慌乱的穿好衣服,急匆匆的跑出来打开大门的时候,才发现,门前站着的正是自己的学生。这些在田间长大的孩子,本来就淘气,加上昨日贾迪的温言细语。几个人在一起,也不只是谁拾掇,就“放肆”的敲起私塾的大门来了。贾迪一阵汗颜之余,又胡思乱想到,自己当初不做戒尺的决定是不是有点仓促了?那时候,不会像那样,老师被学生戏弄吧?。。。。。
就这样,贾迪在元丰六年的一个懒觉之后,和一群呀呀学语的小孩子开始了白话堂的教授生涯。
由于,是从最基础的教授起,贾迪倒也轻松,无非是些后世的看图识字之类的东西。那些小孩,虽然比较顽皮,但一当贾迪走上讲台开始讲课时,都规规矩矩的坐在那里,目不转睛的盯着贾迪,不时一边嘴里念诵着,一边照着“黑板”在桌子上的“沙盘”上用树枝,歪歪斜斜比划着。贾迪对这些孩子非常和蔼亲切,从不打骂,有什么事情,也是好好的讲;平时在课堂上,不时的讲一讲小故事,逗孩子们笑。用不了几天,就和他们建立起亲密的师生关系。
这些孩子年纪不大,但聪明好学,又因为贾迪教授的是那些自己日常生活中简单常用的白话文,一个多月下来,进步不凡。大都学会了三百多个字左右,杨晔更是掌握了五百多个字,最不济的也能读能写二百多个字。贾迪不由一阵欣慰,不觉的在平时课堂课堂上将一些后世的思维方式和观点也流露出来。这些孩子,因为还不曾深受宋朝封建思想的毒害,一个个听得津津有味。那一张张幼稚的脸蛋上,充满了好奇和向往。
这段日子里,除了推脱不了的应酬,贾迪总是白天授课,晚上备课,几乎就生活白话堂这片小天地里。周围的街坊邻居或行人,只要一听到那些孩子们大声朗诵着贾迪编写的白话课文的时候,都不时用手指着白话堂笑道,“板板先生,又在授课了”、“木炭先生,又在教那些顺口溜,口头禅了”。原来,贾迪是用黑色木炭在木板上书写授课内容,常常是满手炭末,有时一个不小心衣服上、脸上都弄得黑乎乎的,老百姓由此戏虐地称之为“板板先生”、“木炭先生”。那些文人雅士听得孩子大声朗诵,什么“吾不日归家,高堂勿念”,什么“好好学习,日日向上”之类的课文,都取笑为“顺口溜”、“口头禅”。贾迪对此付之一笑,有时候更是学着众人,自称“木炭先生”,自得其乐,乐在其中。
一日,贾迪发觉往日总是第一个到学堂的杨晔到上课了还没来!之后一直到贾迪讲完“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吩咐下课放学之时,他的座位仍是空空如也,心里不由暗自着急:“不这孩子,一直都是自己一个人来上学的,不会是路上出了什么事情吧?或者,家里不让他来学这白话文了?”
正在担心,却见一孩子蹦蹦跳跳的跑回来,“老师,外面有三个老爷拜访。”贾迪走到院子里,只见三个读书人模样的人,正站在门外,对着自己的对联指指点点。
哦,不会是来“踢馆”的吧?贾迪整整衣袖,缓步来到门前。那三人相互对视了一眼,其中一个年轻稍长的人上前一步,施礼道,“阁下,可是贾迪贾公子?”贾迪忙回礼应道,“正是在下,不知诸位有何指教?”。“我等游学至此,听闻贾公子才学出众,连东坡居士和涑水先生也是交口称赞,是以慕名而来。”哦,远方学子,贾迪不由心中暗暗松了一口气,忙侧身将众人领进去。
边走边寒暄,贾迪才知道:那开头说话者,叫蔡卓文,子纯笙,杭州人士,另一位身穿青袍的,叫陆雍,子屛华,密州人士,最后一位高额头的,叫孙维古,子顾敏,来自蜀地。去年科考,三人各自来到汴京,本以为自己一身所学,当可高中,不想却都名落孙山,在酒馆相识,自觉无颜回家,又不愿待在汴京,商量了一番,决定四处游学,拜访名家。前日,三人拜会了苏东坡,听苏东坡谈到了贾迪,读了贾迪的几首诗词,顿时大为倾倒,听说贾迪在办白话堂,教授白话,又是觉得颇为有趣,是以,今日专程前来拜访。
三人随着贾迪来到院中,围着石桌坐下之后,与贾迪一番交谈,都面露惊讶之色,原以为贾迪年纪轻轻,受人称道,也只是诗词写得好,谁知见面之后方知,其学识见解上更是让人望尘莫及,渐渐收起那文人相轻的陋习,诚心诚意的请教起来。贾迪见三人是认认真真的读书人,不比自己平日里在黄州所碰到的那些,也存了结交之意,也收起了平日里应酬的那一套,就读书、作文方面谈了一些自己的真实观点。
蔡卓文,陆雍,孙维古,都是年轻人,思想本来就比较活跃,对一些新观念不但不排斥,而且充满了好奇和兴趣,不时随着贾迪的思路提出自己的疑问和看法。贾迪仿佛在溺水的一瞬间抓住了救命的稻草一样,站起身,不停的做着各种手势,热情的向眼前的三个同龄人宣讲自己内心当中关于关于文化的看法、关于文化的追求。
以前,在那些酒宴、诗会上,尽是些酸腐至极的文人,只知道喝酒、掉文,自己仿佛是带着死人面具参加化妆晚会;至于苏东坡,其在古文学上的造诣深不可测,或者说深深的沉醉于其中,每次谈到这些,苏东坡都可以轻易的化解,很怀疑自己是否成了唐吉柯德。而现在这个白话堂,里面都是些刚刚开始学习认字的孩子,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沟通,整日教授一二,其实是一种潜意识的抗争和精神上的寄托。。。。。。今日,碰到几个有兴趣听,还提出问题的,贾迪怎么不欣喜若狂,怎么不一吐为快!
“贾公子认为,现今的文人多是读死书,用死字,困在了古人的词语和思维里。这一点,在下倒是颇有同感。奈何,若不用古语,行文有时难免显得拖沓和不雅。而且若是用白话文的话,文章的典雅,诗词的韵味,尽皆荡然无存。”期间,蔡卓文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疑问。
贾迪于神侃中,听得此问,强止住心底发泄的yu望,坐了下来。
苏东坡也提出过这样的反诘。但这个问题实在是牵扯太广。而且,文言文,在宋朝就相当于后世的书面语,是唯一能代表由古至今文化精髓的语言体系。贾迪一时之间还真的难以回答。但这个问题却是无法回避的。
贾迪端起茶杯,微微喝了两口,看着眼前三人,沉思片刻,说道,“这其实并不矛盾。我所说的读死书、用死字,困在古人的词语和思维里,指那些不分情况,无视实际,处处借用古代词语指代今日事物,用古人思维来阐述问题。举个例子来说,一形容女子长得貌美,不管当时到底是何容貌,往往就是什么“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什么“蛾眉如黛,肤如凝脂”,看似文字极美,对仗押韵,其实是不经过大脑思考,只知道拿前人的早已用烂了的词汇往上套。还不时加上用典,典故虽然可以起到言简意赅、回味无穷等作用,但试想一下,用这个典故之人是否就是和古人情景、感触完全一样,有没有不同之处?有没有自己的感情,有没有自己的个性?。。。。。如果尽是这样一些东西,与其说是你写的,倒不如说是古人写的!至多,你只能算是堆砌辞藻,玩弄文字,只能算是一个文言文的搬运工!”
蔡卓文等三人听得这话,脸上不由一红,自己平时这样的事情可没少做。贾迪看了看,心里暗叹道,“无需自责,千年之后,很多人还是这样,而且还没有你们专业和敬业。就是偶,也难免滴。”
贾迪当然不会把这话说出来,停了一下,接着说,“而且,不知道诸位发现没有,那些用文言文所作之策论,往往学那唐代杜牧的那篇《阿房宫》,追求文采斐然,气势圆足,这就容易导致抒情优于议论,容易导致先入为主,围绕早已拟定的结论,常取其一点,多以偏概全,极尽夸张之能事,却往往于关节之处,三言两语,一笔带过,不见论证的过程,即使有,也是大而化之,于精细处不见丝毫。”
杜牧的《阿房宫》是一篇赋,虽不是策论,但确实以议论之理为讽喻之基础。所以贾迪这样说,三人倒也不能指责。
“听贾公子如此一说,在下才明白为何去年名落孙山了!”陆雍沉思片刻,想到自己科举时所做的策论,写作方式和内容几乎和贾迪说的分毫不差,不由一声长叹。蔡卓文和孙维古也是若有所思,一脸的恍然和怅然。
半响,蔡卓文站起来,对着贾迪一个长辑,说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等今日,承贾公子指教,受益匪浅。方才在下细细思索,也觉得贾公子所言之弊,确是当今多数文人的病根。但在下觉得,这似乎可以经由我等读书人,于自身的修学之道上慢慢改正,与那白话文有何干系?还请贾先生教我。”
贾迪忙请蔡卓文坐下,给众人斟满茶水,考虑了一下措辞,缓缓说道,“因刚才所言,在下苦苦思索之后,以为,一个时代应有一个时代的语言和文化。我大宋承平日久,有许多物事,有许多思想,乃前朝所没有,那前朝有的,很多到了如今,或其内容或其称谓也已改变,是以,今日之语言也应该有所变化。白话文虽然是在村野之口流转,但确实为一种不同于文言文的语言,也往往最先根据新物事、新思想变化发展,如果能够在人数众多的民众当中推广、普及,假以时日,经过规范和提炼,当能够对新语言和新文化的出现起到一个很大的推动作用。”这套理论显然对这三个宋朝的文人来讲太过奇异,所以贾迪在最后又补充了一句,“当然,这是在下的一点设想,是否正确,能否成功,在下心底也不敢说。”
“呵呵,贾公子此番言论,倒像是个新党人士。有此豪情壮志,顾敏钦佩不已。”孙维古一阵笑道。
“呵呵,在下哪里算得上什么新党人士。在下才疏学浅,不懂经世治国,只是作为一个文人,希望为在文艺方面略尽微薄之力罢了。”贾迪,知道,士子中有一部分年轻人,是推崇新党,推崇变法的,如今新党还是在明面上,孙维石说此话也算是一番恭维和推崇了。
蔡卓文等听了贾迪最后这段话,心里颇为震撼,虽一时不能接受,但因为观点和论调太过新异,即刻也想不出怎么提问,又见天色已晚,就起身告辞。
贾迪本想再继续进行这种难得的“穿越时空之对话”,但见人家要告辞,也只得悻悻作罢,不禁有点暗骂自己莽撞,一时激动,交浅言深。
待到送客至门前话别之时,三人言语之间流露出改日还将登门的意思,贾迪笑着说,“今日,和诸位一番畅谈,贾某实在是幸甚。诸位以后还请常来,贾某于这白话堂翘首相盼。”
蔡卓文等三人当即应承。
贾迪看着三人远去的背影,脸上破天荒的露出一丝奸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