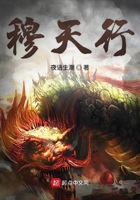很久以后,水莲住进精神病院,我才意识到自己是多么无知和幼稚。因为这种无知和幼稚,我和程皓像得了受虐狂一样,定期到精神病院看望水莲,希望也能像水莲一样在精神折磨中忘记过去。我们愿意陪她一起受苦,这样我们的心里反而会好受一点。
时间真能冲淡一切似的,我和程皓在各自的事业中每日里喜笑颜开。他的广告公司门庭若市,当然得益于他有一个很不错的合伙人,可以仅用胖胖的食指按电话就为他招来不少生意。程皓常常在电话里哈哈大笑。我在一家报纸主持一个叫做“心情驿站”的版面,同事们都说我小小年纪好像经历了不少切肤之痛似的,我只是报以亲切而神秘的笑。
然而所有的笑容在精神病院戛然而止,我们谁也不是装。连我们真实的爱情都在陪聊中破灭了,我们彼此没必要装什么快乐。记得一个病人在医院的急诊候诊室墙上写过一句话:那些相信时间能治愈一切的人,准是没在这里等待过。因为空话谁都会说,而真正置身于一个必须悲伤的环境中时,你只能是恨不能让时间倒流,让一切重新开始。其实从陪聊的一开始,我就知道这是一个危险的行当,我就希望我们三个人都能全身而退。比如那次,当水莲被孟进军强奸后,我本来是想捉弄一下孟进军,再把他投入监狱,没想到却造成了水清流的重病,我为此后悔不迭,一直希望对水莲能有所补偿。
刘一德的出现使补偿成为一种可能。经过水莲的事以后,我对许多人说过一句话:你给予一个人爱的时候,你给予的是爱,可他接受时,却不一定是爱。这多少有了一点基督的味道。然而事实上,爱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容易变形的液态物。就像我们想了很多次的自以为天衣无缝的话语,刚刚从我们嘴里迸出去的时候,错误已经无可挽回地发生了。
好像注定,这种补偿最终还是走向了反面。当陪聊生涯中的悲剧一件件来临时,我惟有痛悔不已。
我常常有许多一厢情愿的想法,这些想法害人不浅也害自己不浅。比如说,现代人进入冷冰冰的机器时代和容易产生智障的信息时代以后,变得出奇地变态,程度较重的自杀或者住进精神病院,程度较轻数量也较大的就是感到空虚寂寞无所适从的人群。陪聊作为一种职业,本是为了缓解这种状况,让人们活得轻松点,谁也没有想到,陪聊非但救不了别人,反而害了自己。而且,到最后,陪聊和许多新潮职业一样,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歧路。在后来,陪聊这一行当,在有些城市甚至成为被取缔的对象,让我们大感意外。
这也说明,人类社会的某些毛病,也许并非人类自己可以救治的。
从那时起,我们的陪聊生涯一步步地走向了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