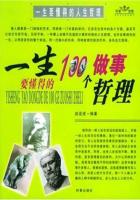我们把他们送到了温邦站,离开的时候,我一直望着窗外,看到小女孩抱着她的新洋娃娃。
我知道,十几年前那个跟在卡车后面跑的孩子,其实应该是我。
弟弟的爱
●佚名
每当我坐在全市最豪华的写字楼里,看着街道上忙忙碌碌的人们,都会有种特别的感觉。谁能想到,不过才十几年,我就从一个山沟里背着干粮上学的孩子,变成这家独资公司的白领,开着新买的“赛欧”,西装革履地出人高级场所。而这一切,其实都缘于一场灾难。
我13岁那年,一场大水毁了老家整个山村,等我被人从树上救下来后才知道,全家只剩下我和同父异母的弟弟两个人。父母和家里那座破房子,早被洪水不知冲到了什么地方。
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绝望。以前虽然家里穷,但是我学习好,完全有可能到大山外面去上学,然后飞出这个穷地方。可现在一切都破灭了。而我那个同父异母的弟弟,从小就粗野鲁莽,不爱学习,却因为后母的偏心能得到更多疼爱。我一直不喜欢他。
不久,乡干部带来一个中年人,说是父亲的一个远房弟弟,我们的叔叔。我感觉一下有了希望,叔叔一定会把我们带出去。谁知,叔叔却说自己家没有多大的能力领养我们兄弟俩,只能带一个走。我心里刚燃起的希望一下又破灭了。弟弟长得又高又壮,假如让叔叔挑选,八成不会选我。可第二天,叔叔却给弟弟留下一点钱,要带着我走。弟弟哭着跟我们走到村口,我也哭了,可自私的心理让我不敢回头去看,我害怕叔叔会改变主意。
卡车开动了,透过灰蒙蒙的后窗,我看到弟弟跟在后面边哭边跑。卡车越开越快,他的身影也越来越小,最后终于看不见了。
跟着叔叔到了省城,日子过得并不好。虽然他家没有孩子,可是婶子经常在家里指桑骂槐。不只是我,叔叔也一样整天被她骂。不管怎样,我都一直忍着,只要能让我上学。
我终于顺利考上了北京一所重点大学,因为成绩优秀,还没毕业就被现在的独资公司抢先聘用。很快,我在市中心按揭贷款买了一套大房子。那时婶子已经去世,我把叔叔接了过来。
就在我对生活充满希望的时候,弟弟突然出现了。当我看着眼前这个穿着黑棉袄、满脸胡子,已经完全成了农民的弟弟时,心里忽然涌起很多愧疚。虽然这么多年我没怎么想起过他,可看到现在俩人的差距,我还是觉得对不起他。
弟弟住下了。
他吃饭时蹲在地上,说话扯着大嗓门,并把我刚装修的家搞得一塌糊涂。最糟糕的一次,我喜欢的一个女同事来家做客,他居然盯着人家看半天,还一边傻笑,吓得那女孩夺路而逃。第二天,全公司都知道我有一个山里来的兄弟。而那个女孩再也不肯答应我的约会,她说她无法想象怎么能和有这样一个弟弟的人交往。
我意识到,自己已无法再习惯有一个弟弟,更别说是这样一个弟弟。于是我问叔叔,弟弟打算什么时候走。可叔叔却告诉我弟弟这次来不准备走了。我忽然想起,叔叔家以前的老房子现在正是开发商眼热的地带,听说可以卖很大一笔钱。难道叔叔要把旧房子分给弟弟?我准备和弟弟好好谈谈。
谁知还没等我开口,弟弟说话了:“哥,俺这次来,是叔让俺来的。说要分给俺一套房子。”我心里“咯噔”一下,果然让我猜对了。弟弟继续说:“俺没想着要那房子,本来俺也不想来,可心里想着你,这十来年,俺从没忘了你,心里想着咱哥儿俩怕是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了。”说着,满脸胡子的弟弟居然有些哽咽:“俺也看出来了,你不喜欢俺……俺过两天就走啦。”
弟弟的话一点都没让我感动。我只是想,假如他留下,家里还会这样乱下去;我还要给他找工作,娶媳妇,而且,叔叔的旧房子还要分一半给他……于是我没接弟弟的话茬儿,心里想着只要他离开,我宁肯给他一笔钱。可叔叔坚决不让弟弟走。我连反驳的理由都没有,叔叔什么都给了我,比起弟弟,我的命运已经好太多。
由于叔叔的挽留,弟弟终究没有回去。不过他不再像开始那样和我说话了,谁都能看出来我对他的抵触。每当看到他蹲在地上吃饭,在花园里晒太阳抓虱子的样子,我就生出一种厌恶的感觉。
我决定再和弟弟谈。同样,没等我开口,弟弟却说道:“哥你不用说,俺就要走了。这阵子也麻烦你了,现在天冷了,俺……”没等他说完,我马上接着说:“没问题,给,这是2000元钱,你拿上,回家买几吨煤,花完了再找哥要。”弟弟说什么都不接,我以为他嫌少,又添了1000元,可他依然不接。我越发相信他是为了那旧房子,于是拉下脸说:“你怎么这样!哥挣钱也不容易,就算你嫌少,我也得慢慢给你才是。”
弟弟的脸一下涨得通红,不认识一样看着我:“你说啥呢哥,俺不是嫌少,俺是嫌你把俺当外人。”我随口说:“你不就是想着那套旧房子吗!我知道你这次来是想分拆迁费,告诉你,那钱没你的份!”
弟弟瞪大了双眼看着我,满是风霜的脸上一片愕然。听到争吵声,叔叔走过来,用哆嗦的手指着我:“你,你简直是混蛋,你怎么能这样说你兄弟!你不该这样啊,你们是哥儿俩,他在老家已经够苦的了,这么多年一次都没找过咱们,你不觉得有愧吗?”
我自知理亏,只好硬着头皮说:“这是各人的命运,我也不想这样。”
叔叔再次气得喊道:“各人的命运?我告诉你,当年我去找你们的时候,根本没想带你回来,是你兄弟说你身体差,吃不了苦,非让我带你走不可。现在你居然这样对待他!”
我待在那里,一下想起多年前弟弟在车后面跟着跑的情景。叔叔指着我的鼻子继续骂:“这么多年,我一直想把你兄弟接来,可他不干,说怕连累你。告诉你,那套旧房子就该是他的,你想都别想!”
自己的私心被戳穿,我从后悔变得恼羞成怒,也喊道:“我是你的养子,那房子就该是我的!”叔叔挣脱弟弟的拉扯继续喊:“他是我亲侄子,比你亲!”
我吃惊地愣在那里。叔叔继续说:“你根本不是你爹亲生的,你是他第一个老婆带来的!论到天上我也不该把你兄弟扔在老家,你和我们家没一点血缘关系!”
房间里死一般地静。我只觉得血液全部涌到头上,小时候婶子骂我的话在耳边回响起来:领回个白眼狼,不知道什么时候养大就跑了!
叔叔渐渐平静下来。弟弟蹲在一边抽着烟说:“哥,俺也是后来才知道你不是俺亲哥,可俺一直当你是亲哥。”他站起来对叔叔说:“算了,俺还是走吧,俺哥有文化能挣钱,以后全靠他给你养老啊。”说完,他从腰里拿出一个布包:“这些年俺赶大车拉石头挣了钱,俺不缺钱,这1万块钱给叔吧,俺哥起早熬夜的,挣钱也不容易。”弟弟说。
我流着泪扑过去,一把搂住了弟弟……
我终于没能留住弟弟。我送他上了长途车。车开了,我跟在后面跑着,看到弟弟在里面向我挥手。车开得越来越快,我却不想停下来。我知道,十几年前那个跟在卡车后面跑的孩子,其实应该是我。
当你无私地给予,你便会加倍地得到精神的欢愉!
分享甜蜜
●韩杰
赵慨与李升两家相邻,只有一墙之隔。赵家种了一棵枣树,挂着红楞楞大枣的枣枝伸进李升院内;李升种着一株苹果树,结着红艳艳大苹果的苹果枝也“越境”伸进赵慨院中。
实际上,各家只要将果树的枝条往自家院内撇一撇或用绳子将果枝勒住枝就不会“自由发展”。但赵慨想:李家很爱吃枣,就让他家尝尝鲜吧!李升也想:赵家喜食苹果,就让他家尝尝苹果的美味吧!
于是两家互告邻居,过墙的果子随便吃。
由于互送甜蜜,两家都品尝到了滋味鲜美的水果;由于都惦着邻家,两家便亲如一家。
智者说:“将一个痛苦分给别人,便得到两个痛苦;将一个快乐分给别人,便能得到两个快乐。”
当你无私地给予,你便会加倍地得到精神的欢愉!
没有哪一个人真正了解自己的父亲,但是,我们大家都有某种推测或某种信任——米南德
疤痕
●周海亮
她长得很漂亮。可是左边的眉骨上,有一道深深的疤痕。
那时她还小。父亲推着独轮车,把她放在车筐的一侧。田野里到处是青草的香味,她坐在独轮车上唱着歌。后来她听到山那边响起“哞——”的一声,她站起来观望,车就翻了。
那天很多村人对她父亲说,怎么不小心一点呢?这么小的孩子。
她喜欢唱歌和跳舞。小时候在村人面前唱唱跳跳,便有十大人夸她,唱得好哩,妮子,长大做什么啊?她就会自豪地说,电影演员。
她慢慢地长大着。长到一定的年龄,便意识到自己的脸上,有一道难看的疤。从此她不在外人面前唱歌。因为她怕别人问她,长大后干什么。
后来她去遥远的城市读大学。她读的是与“演员”毫不相关的专业。但有那么一个机会,她还是去试了试某电影学院的外招。结果,和她想像的完全一样,她被淘汰了。
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道疤痕。
大二暑假回家的时候,父亲为她准备了一个小的敞口瓶,瓶子里装着一种黄绿色的黏稠的糊糊。父亲说,这是他听来的偏方,里面的草药,都是他亲自从山上采回来的。听说抹一个多月,疤就会去了呢!父亲兴奋着,似对自己的话,深信不疑。
她开始往自己的疤上涂那黏稠的糊糊。每天她都会照一遍镜子,但那疤却一点儿也没有变淡。暑假里的某一天,有几位高中同学要来玩,早晨,她没有往眉骨上抹那黏糊。父亲说怎么不抹了呢,她说有同学来玩,父亲说有同学怕什么,她说今天就不抹了吧。可是父亲仍然固执地为她端来那个敞口瓶,说,还是抹一点吧。那一瞬间她突然很烦躁,她厌恶地说不抹了不抹了,伸手去推挡父亲的手。瓶子掉到地上,啪一声,裂得粉碎。
父亲的表情也在那一刻,变得粉碎。还有她的希望。
以后的好几天,她没有和父亲说话。有时吃饭的时候,她想对父亲说对不起,但她终究还是没说。她的性格,如父亲般固执。
回到学校,她的话变得少了。她总是觉得别人在看她的时候,先看那一道疤。她搜集了很多女演员的照片,她想在某一张脸上发现哪怕浅浅的一道疤痕。但所有的女演员的脸,全都是令她羡慕的光滑。
她变换了发型。几绺头发垂下来,恰到好处地遮盖了左边的眉骨。她努力制造着人为的随意。
那一年她恋爱了。令她纳闷的是,男友喜欢吻她的那道疤。
大三那年暑假,她再回老家,父亲仍然为她准备了一个敞口的瓶子,里面盛装的,仍是那种黏黏稠稠的黄绿色糊糊。父亲嗫嚅着,其实管用的……真的管用。父亲挽起自己的裤角,指着一道几乎不能够辨认的疤痕说,看到了吗,去年秋天落下的疤,当时很深很长……现在不使劲看,你能认出来吗……我这还没天天抹呢。
看她露着复杂的表情,父亲忙解释,下地干活时,不小心让石头划的……小伤不碍事。却又说,可是疤很深很长呢。
她特别想跟父亲说句对不起,但她仍然没说;她特别想问问当时的情况,但她终归没敢问。她怀疑那疤是父亲自己用镰刀划的,她怀疑父亲刻意为自己制造一个和她一模一样的疤。她害怕那真的是事实。她说不出来理由,但她相信自己的父亲,会那么做。
整整一个暑假,她都在自己的疤上仔细地抹着那黏稠的糊。她抹得很仔细,每次都像第一次抹雪花膏般认真。后来她惊奇地发现,那疤果真在一点一点地变淡。开学的时候。正如父亲说的那样,不仔细看,竟然看不出来了。
可是她突然,不想当演员了。
星期六晚上她和男友吻别,男友竟寻不到那道疤痕。男友说,你的疤呢?
她笑笑,说,没有疤了。
其实,她知道,那道疤还在。
疤在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