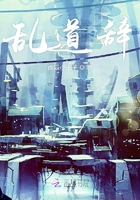幸运之神很快光临到他头上了。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家乡也是贵溪。司令部里要扩充人员,派人回乡招选优秀学子。消息传开多少人都想挤进入围。虽然是去司令部做事,不过是小小的干事,可相府的丫环也是吃香的呀,报名的学生真多。孙先生也报了名,他觉得这是通往官场的一条捷径。家乡早就流传着一句俗话:跟了桂永清,就能把官升。谁去了谁就可以告别穷困,过富日子了。正因为大家都这么想,才引起校园里不小的波动。先是考试,他占了绝对优势;再是体检,强壮的体格又让他闯过一关。他终于被选中了,成为学校惟一的。
那一天,他是披红戴花离开学校的,同学、先生鼓掌为他送行,大红花是校长亲手给他戴上的。平日不苟言笑的校长,笑得脸上也开了一朵花。他张着口大声地说:孙同学被选中,是我们学校的光荣!他就这么荣光焕发地离别学校,走进了军营。
从军后,有了吃,有了穿,不再用兄长推车送米送菜送炭了。他长长吐出了一口气,即使还不能挣钱,可是总比上学花钱要强。紧张地训练完毕,又是紧张的军务。紧张奔波一天,青春勃发的他也是浑身困乏,不过,年轻自有年轻的优势,头挨枕头就睡,睡过一气,眼一睁,轻松了。每每轻松下来,他就会看见兄长推车远行的背影,就会听见兄长那当官享福的嘱托。他任劳任怨,为的是以求一逞,光门耀祖。这一日,他升了班长,别看班长不大,可也是往上爬的一道门槛。凑巧有件公务差遣他办,而办差的地方离他的家乡不远。他是飞跑着办完公差的,节省下的时间绕道奔回家里。他推开门,看到母亲,一下跪倒在母亲的跟前,笔挺的军装显示着他的得意。他得意地告诉母亲,他当了班长,还要当排长、当连长,要把母亲接出去享福。母亲眼中的喜悦只忽闪了一瞬,双眼一眨,又显现了忧虑。对着母亲的忧虑他忽然想起了兄长,兄长呢?他问。不问还好,一问,问出了母亲的泪水,母亲说:
“他跟共产党走了。”
啊!他一下惊呆了,惊诧得几乎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兄长啊,小弟每日每时记着你的嘱托,要当官,要享福,要接母亲去享福。我发愤读书,拼命做事,不就是为了给你一个圆满的答复么?你何苦要走这一步?
回到军营,他仍然苦闷不安。躺在床上,他头一回尝到了失眠的滋味,反来复去,就是入不了睡,闭上眼睛,眼中的静物也亮如白昼。好不容易暗黑下去,进入了梦境,却看见长长的枪筒指到了自己的胸前。猛抬头,正对着一双喷火的眼睛,而那亮睛竟是兄长的。他长呼一声,惊下床来,再也难以入眠,坐在桌前,走笔涂画,笔底一遍一遍出现的都是曹植那滴血的诗句:
煮豆燃豆箕,
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历史不容他沉思多虑了,一阵急风暴雨,他流落了到了台湾,不用说,当官接母亲享福的愿望成了永远的梦幻。这时候,他才又有所悟,突然发现兄长比他早一点悟到了世理?多年来,他稍稍宽慰的是兄长留在大陆,能在母亲身边常常相守。他时时不安的是,他们兄弟俩还能不能像先前那么情同手足?
踏上归途前,孙先生便得到悲痛的恶耗。母亲已在3年前仙逝了。孙先生不由得捶胸顿足,跪头滴血。他在家里设灵祭祀,每日叩拜,整整恩念了七七四十九日。守七完毕,孙先生还是走不出悲痛,如此拖延,当局还不知什么时候才开禁,说不定和兄长也成了人天两隔!孙先生咬牙决断,要回大陆去,去看望自己的兄长。几经周折,孙先生终于成行了。
孙先生到了泰国,归心似箭,哪有心思看什么大象表演,人妖现世?立即换乘飞机直抵香港。在香港,也无心浏览这世界贸易大都市,转换一架飞机,飞广州,飞南昌。飞到南昌,已是下午4点多钟了,当天没有去鹰潭方向的火车。在客栈住一晚上,简直度日如年。孙先生干脆租了一辆“的士”,径直奔往家乡贵溪。
近乡情更怯。的士车在原野中驰过,青山依旧在,禾木遍地绿。然而,物是人非,他姓孙的已不是先前那位风流倜傥的后生了,早成了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兄长呢?兄长会是怎样一种模样?又会怎么对待他这位曾经被喊为蒋匪军的罪人?孙先生有些惶惑了,但是,渐近故乡,顾虑再多也迟了。转而又想,就是死在故里,也没什么,正好应了叶落归根的古话,一挺胸,一抬头,痴望着前面好像熟悉却又陌生的田园。
孙先生到家的时候,家里平静得如一池春水。他走进院里,门里出来一位老者。他正把老者和那推车远去的背影对接,老者开口了:
“你是小弟?”
孙先生扔了行李,兄长已扑了过来,两位不同垒营的兄弟紧紧拥抱在了一起。40年了,悠然的历史终于走过万水千山,走过险阻波澜,走到了一起。
孙先生归里的消息不胫而走。闻讯,县里对台办的领导赶来了,握住他的手,亲切地欢迎他回来!县长也赶来了,热情地问他住不住得惯,吃不吃得好?还说,他开了一个好头,贵溪在台湾的乡亲不少,欢迎他们都回来看看。
孙先生如入梦境。在他的记忆里,共产党冷如寒霜,不讲人情,动不动就会厉声断喝。可是,亲眼目睹,怎么和多年宣称教化的不是一回事?
孙先生又和兄长躺在了一个床上。世事沧桑,岁月匆匆。两位青年已成了花甲老人。他问兄长:
“还记得你要我读书、做官,接娘享福的嘱咐么?”
兄长沉默了一会儿,低低地说:
“我是忽然才醒悟的。咱做了官,不等于人人都做了官;咱娘享了福,不等于谁的娘也能享福。我是想让天下人都享福呀!”
孙先生说:可我是照着你的说法走的,却走到了你的对面。
兄长不说了,顿一顿,笑了:我们不是走到了一起嘛?
孙先生笑了。屈指数来,40多年了,孙先生没有这么朗声笑过。兄弟俩的笑声融合为一体,飞出老屋,在故乡的静夜里分外响亮,亮得和启明星一样耀眼。
53
谁也不会想到,何先生这么个小人物把一场返乡探亲活动搞得热潮澎湃!谁也不会想到孟女士、孙先生会用这种不显山不露水的手法冲破当局苦心设置的樊篱!一切的一切不是谁精心地安排,是一种水到渠成,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晶。何先生的行为在台湾当局引起了轩然大波,若不及时注意,不顺应潮流,这波澜会冲溃固有的堤坝。显然,孟女士、孙先生的举止,跨越了障碍,使堤坝形同虚设。倘一个、两个人违规也还罢了,问题的实质是一旦有人从荒野穿过,随后的人就会络绎不绝,没有路的地方就会成为羊肠小道,继而被更多的人踏成平坦大道。台湾当局面对此状,进退两难,举棋不定。
就在这当口,新闻部门又暴出了新闻:台湾《自立晚报》记者李永得、徐璐抵达了北京。1987年9月15日凌晨1时10分,二位记者出现在北京首都机场。
如果说,孟女士、孙先生的行动尚可以宽恕的话,那是因为他们虽然踏上了大陆,却是暗渡陈仓,没有新闻媒体将这事炒得沸沸扬扬,台湾当局自可稳坐营帐,以并不知晓的表情去继续高唱禁止回大陆的腔调。然而,晚报记者的行动却撕破了台湾当局的脸面。二位记者一踏上大陆就亮彻在世人面前,与其说是记者在世人面前亮相,还不如说是把台湾当局推到了亮相的前台。
此刻,在台北官邸蒋经国和其幕僚难免有些手忙脚乱。趁此机会,不妨让我们追踪一下李永得、徐璐成行的足迹。
1987年的秋日,台湾岛上还迷漫着惯常的燠热。细心的人似乎可以看出,在这气候的燠热中还夹杂着返乡探亲的热浪。一般人尚在琢磨这股热浪的流向,善于审时度势的新闻人早已“春江水暖鸭先知”了。台北《自立晚报》社长吴丰山悄悄打定主意要站到这股热浪的前端去。他与总编辑陈国祥会商,完全赞同他的认识和决策。他们立即择定李永得和徐璐为最佳人选,一条令国人惊诧、令世界关注的新闻孕育成型了。
9月11日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自立晚报》赴大陆采访的记者启程了。中午12时30分,李永得、徐璐搭乘日航EG204班机,从台北起飞,前往日本。飞机降落时,夜色临近,东京昏暗,日本人忙碌的节奏随着傍晚的到来逐渐减缓。然而,两位记者的节奏却紧凑得胜过任何时候。一出机场,他们便直奔中国驻东京大使馆。
在大使馆,李永得、徐璐见到了马连印。马连印是专门负责台胞签证工作的。二位记者直言相告,他们要以正式记者的身份进入大陆采访。马连印听了喜上眉梢,又觉得此事关系重大,请他们稍候,立即和国内有关领导进行联系。
在联系的空隙间,台湾已经满城风雨了。《自立晚报》抢占潮头,分秒必争。两位记者踏上征途,他们立即在报纸刊发了消息。消息轰动了台湾,台湾民众奔走相告,称为奇事;台湾当局甚为震怒,采取措施,企图中止这次行动。内政部入出境管理局和行政院新闻局通告《自立晚报》,他们的行动违犯了《国家安全法》施行细则第13条以及《大众传播事业派遣人员出国、采访审核办法》,责令立即召回记者。但是,总编辑陈国祥在接受《中国时报》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未有召回记者的计划。
次日的《中央日报》就此事发表了评论,题目是《何必急抢滩》。从《自立晚报》的行动看,是急了些,是超前了些,是有些抢滩之嫌。可是,两岸分裂38年了,与这漫长的时间相比,这种抢滩不是急了,而是急得尚且不够。因而,社长吴丰山在接受合众国际社记者采访时,态度坚决,表示要按计划进行下去。
威胁来了,当局一位高级官员明令,如果《自立晚报》一意孤行,记者一旦赴大陆采访,将“绝对依法处理”。
传言来了,台湾一家电视台报道:李永得、徐璐赴大陆采访,遭到中共拒绝,搁置东京。
……
然而,一切都已为时过晚,9月14日下午3时30分,中国民航CA930客机在东京机场腾空而起,机上承载着让世界关注的消息。次日凌晨1时10分,一个划时代的行程开始了,李永得、徐璐降落在了北京首都机场,他们踏上同台湾岛一样坚实的大地,却觉得大陆的大地比台湾更为坚实。
三位中国新闻社记者在首都机场迎候着他们,第一句热切的话语是:
我们等了你们38年了!
两岸记者的手在明亮的灯光下握在了一起,地球上的人们很快看到了不同凡常的握手。
更热闹的场面在等待着他们,四、五十名记者簇拥在首都机场。他们一出门,大家蜂拥而上,将他们围裹在中心。一时,李永得、徐璐成了新闻中心,来自各个国家新闻机构的驻北京记者,都把镜头对准了他们。台湾记者用自己的坦率行动,存留下了闪光的风景!
接下来,李永得和徐璐进行了为期11天的新闻采访。他们去了杭州、广州、深圳、厦门,还走进了福州有名的寡妇村,在那里看到一个个思亲盼归的憔悴容颜。他们见到了好多新闻人物,还看到了从台湾回到大陆的王锡爵、李大维、侯德建、张春男,看到他们在大陆安居乐业,由衷地欣喜。
二位记者在大陆轻松自在地采访,但他们的轻松自在却搅扰得台湾当局无法轻松自在了。台湾安全机构的秘书长蒋纬国召开专门会议研究此事,内政、外交、防卫、安全等等,几乎凡能涉及到的部门都通知了,高层官员,济济一堂,意见却难以一致,会上分为了强硬派和缓和派。
强硬派认为,李永得、徐璐二位《自立晚报》记者,冒犯禁令进入大陆采访是错误的,应采取强硬手段,以防其他报社再派人进入大陆。
但是,“新闻局”和“文工会”则代表了缓和派意见,认为不要将此事作为政治事件看待,应看作一起单纯的新闻事件。
两种意见争执不一,各有各的理由,蒋纬国端坐主持席,洗耳恭听,一言不发。发言时候,谁都承认这位蒋家王朝的后人确实棋高一着。因为,强硬派和缓和派的意见分歧在于如何处置此事,然而,对于事件本身的错误却是高度一致的。谁也没有想到二位记者私闯大陆,贸然采访,还会有正面意义。但是,蒋纬国说有,而且,冠冕堂皇罗列出四点:
1、记者具有敏锐观察力,可在采访过程中,发掘许多不为人知的生活状况,而不受党派立场影响;
2、记者采访发表的文章,有利情报搜集;
3、记者进入大陆采访,可试探中共官方的反应及其接待情形;
4、可作为未来修正“大陆政策”的参考。
听蒋纬国如此一说,则好像二位记者是当局派回大陆采访了。与会者无不觉得,秘书长先生着实继承了家族中善辩的传统。这样一来,缓和处置也就有了下台的阶石。当然,蒋纬国也要顾全当局的面子,他重申:
维护法治的决心不宜改变,对《自立晚报》先予以“口头”警告,迨二位记者回台后,再行公布惩戒之道。
9月27日,李永得、徐璐结束了在大陆采访的全部行程,满载收获由香港转机,飞回台北。当日,新闻局发表处分《自立晚报》的声明:
两年内不准该报人员申请出国,社长吴丰山与两名记者“移送法办”。
移送法办,法律将如何惩办吴丰山及二位记者?台湾人民拭目以待。然而,法律惩办却进行的十分缓慢,秋去冬来,没有结果,一直到第二年春暖花开,法律才做出宣判:
《自立晚报》社长吴丰山及两名记者无罪。
曾经发表处分声明的“新闻局”只好顺水推舟,表示“尊重司法审判权的独立”,对于此一判决自应尊重。
《自立晚报》记者赴大陆采访的事情到此结束了,然而,其产生的影响却没有结束,仍然推进着两岸接触了解,实现一统的进程。继二位之后,台湾记者接踵而至,踏上了大陆的土地:
1987年10月26日,台湾记者皮介行来到北京,采访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1月2日下午,新当选的政治局常委胡启立接受了他的采访,微笑着说:“你是第一只燕子,以后还会有更多燕子陆续飞来!”皮介行成为采访中共全国代表会议的第一位记者。
1987年11月13日,《台湾时报》副总编辑张自强申请到大陆探亲,并且采访。他成为台湾当局开放探亲后,第一位经台湾红十字会批准探亲的记者。
1988年3月25日下午,台湾《人权论坛》杂志社社长周幼非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同时出现的还有《台湾时报》副总编沈国均。他们是40年来首次采访全国人民代表会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台湾新闻人士。
……
一批又一批新闻人士,飞抵大陆,抢滩采访,大陆新闻日日激荡着台湾岛。归心似箭的台湾老兵,更为坐立难安,吁请开放探亲的呼声,波击着台湾的每个角落,台湾上下震动了!
54
1987年,是去台老兵,是两岸离人想忘也忘不掉的日子。
10月15日下午,台湾“内政部”部长吴伯雄举行记者会议,宣布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
除现役军人及公职人员外,凡在大陆有三亲等内血亲、姻亲或配偶的民众,均可于11月2日起向台湾红十字会登记赴大陆探亲。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一年以一次为限,除有特殊原因外,每次停留不得超过3个月。
这消息惊诧台湾海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