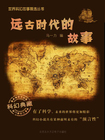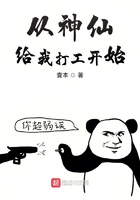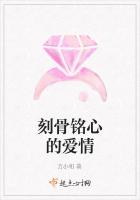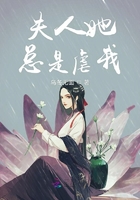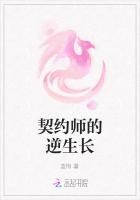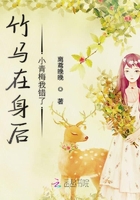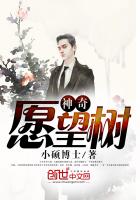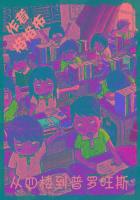我说了,我并不想唤起你们对他的不快回忆,而且,重要的是我下面的叙述。我会详细记录整个十昼夜的审判过程,我们陪审团在其中做了哪些事——这些事都涉及我个人的离奇经历。我正是希望通过这些来吸引读者,而不是那个杀人犯;我也希望读者注意这些事,而不是纽盖特监狱的案子。
我被推为陪审团主席。开庭第二日早晨,听了两个钟头证词后(我听到教堂报时的钟声了),我无意间瞄了一眼在座陪审员,却发现人数不对。我数了几遍,都数不出来。总之,人数总是多一个。
我碰了下旁边的人,低声问他:“请帮我数一下,我们有多少人?”他对此请求颇为吃惊,但还是回头数了一遍,“怎么回事?”他突然疑惑道:“我们怎么是十三个——不,不可能。不。我们是十二个人呀。”
我们又反复数了几遍,逐个数总是十二人,算总数却多出一个。
没有谁——没人——能解释其中原因。但我有一种直觉:肯定那个人来了。
陪审团被安排住在伦敦客栈。我们睡在一间大屋里,里面摆了数张单人床,每日二十四小时都有官员照顾,并监视我们以策安全。却不必隐瞒这位官员的真姓氏。他聪明、儒雅、待人体贴,在城里颇受敬重。
他生得眉目和善,还长了令人艳羡的络腮胡,说话声音洪亮温和。他就是哈克先生。
晚上,我们都上床睡了,屋里一共十三张床,哈克先生的床在门口。到第二日夜,我却没有睡意。看见哈克先生坐在床上,我便走过去,坐在旁边,请他吸鼻烟。哈克先生手刚碰到我的烟盒,就全身颤了一下,问道:“是谁?”
我便顺着他目光看去,果然看到了那个人——就是皮卡迪里大街那两人的后面一个。我便立起身,向前走了几步,又停住,回头看哈克先生。他却自己笑起来,愉快地说:“刚才我还以为看到第十三个陪审员呢,他没床位。现在我知道了,那是月光。”
我却没有如实相告,只是请他和我一起走到大屋尽头,这才看清了那人在干什么。他在其他十一人枕边各站了一会儿,而且总站在床的右侧,然后绕过床脚,走到下一个床。他似乎只是歪着头,仔细看了每个人睡熟的脸,却没注意我和我的床。我的床离哈克先生最近。他走到一个高处的窗户,月光从这里照进来——似乎腾空飞走了。
第三天早餐时,除了我和哈克先生,其他人几乎都说夜里梦见那个被害人了。
现在我可以肯定,当时走在皮卡迪里大街的两人中,后面那人就是被害人,他直接在法庭上做证向我示意。但即使如此,我依然未全部明白。
开庭第五日,原告的控诉已近尾声,有人出示了一个物证,却是一枚被害人的小肖像。这肖像本来放在他卧室里,案发时却失踪了,后来又在凶手的藏身处找到了,有人看见犯人当时正在挖掘。证人指认完毕后,肖像被呈给法官大人,然后又传给诸陪审员看。一名黑袍官员正要递给我,却突然从人群中跳出一人——正是皮卡迪里大街的后一个。他一把夺过肖像,亲手递给我。我还没看清楚那盒子里的肖像,他却低沉了嗓音,空洞洞地说道:“那时候我年轻,脸上不像现在这样没血色。”
他走到我和下一个人中间,然后又走到那个人和下一人中间,如此转了一圈,又回到我旁边。尽管如此,却没人发觉他。
每日审判结束,我们都由哈克先生隔离监护。吃饭时,我们总会议论当日诉讼情况。控方陈情第五日结束,我们才对案情有了全面了解,议论也就更加激烈、紧张和肃然。
我们中有一个教区代表——这厮简直是我见过的最傻的白痴,他总是胡搅蛮缠,否认显而易见的事实,另外两个没有骨气的教区寄生虫也在一旁附和;当下三人大放厥词,吹嘘自己已经参加过五百多起谋杀案审判了。几个蠢货只是吵吵嚷嚷,好生热闹,不觉夜幕降临。我们中已有人准备去睡了,我又看到那个被害人出现了。
他冷冷地站在三人身后,向我招手。我一走过去和他们辩论,他便立刻退下。之后,他屡屡出现,却总是不离这间方形大屋了。只要我们中有人聚头说话,他就在他们中间出现;只要他们核对笔记的结果于他不利,他就十分紧张,向我招手。
有一点要记住,直到开庭第五天,被害人肖像出示时,我从没在法庭上见过那人。现在已进入辩方诉讼阶段,到此为止,案情出现了三个变化。且先说前两个。此人现在频繁出没于法庭上,却不再对我说话了,而是对当时的发言人说话。比如,被害人咽喉处有一道平直的刀伤。辩方发言说,被害人可能是自己割断喉咙的;这时,那人就出来了,站在发言人胳臂旁,露出那道狰狞的刀伤(以前也露着),一时用左手,一时用右手,在咽喉处比画,极力对发言人证明,他自己的手是不可能弄出这种刀伤的。再如,有个女证人说,这个凶犯为人慈善。那人便出来,站在她面前,直勾勾地看着她,张着手臂,伸手指着那个面目凶恶的犯人。
再说第三个变化。三个之中,这个印象最深。我并不想借此得出什么结论,只求准确地描述。每次这人靠近对方时,尽管对方察觉不到,却必然会发出一阵战栗,面色不安。似乎有一条法律明文约束我,使我守口如瓶,他却在无形中悄然对他们施加影响。
辩方律师陈词说,被害人极有可能是自杀,那人便站在他面前,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开裂的喉管,样子很可怖,那个有名的律师就开始结巴,雄辩口才一时全无,只是用手帕擦着额头,脸色苍白至极。那女证人看着他时,眼睛也随他所指落在被告人脸上,充满疑惑和困窘。
我不妨再举两例说明。开庭第八天,下午例行有几分钟休息时间。
休息完后,我回到法庭,等待其他陪审员归位。我坐在那里四周打量,以为那人不在。刚看到走廊上,却见他向前倾着身体,靠在一位很体面的妇人身上,似乎想看清法官是否回席。那妇人突然尖叫一声,昏倒在地,被人抬了出去。本次审判的主持法官是个受人敬重、贤明的人,却不料也和妇人一样,直到案子结束,才恢复常态。他手拿卷宗,开始对本案总结陈词,那受害人却从法官入口处进来,径直走到大法官身后,从他肩上探过头去,急切地要看他正在翻看的记录。法官骤然色变,突然停住了手,全身战栗,结结巴巴说道:“对不起,诸位,请稍等片刻。空气污浊,我有些受不住。”然后要了一杯水喝完,才缓过神来。
这十天审判实在单调又漫长,有六天时间,同样的法官坐在长凳上,同样的被告站在被告席上,同样的律师坐在桌案边,同样语调的问答萦绕屋梁不绝于耳,同样的引座员进进出出,乃至法官写字的声音也一样。每天同一时间亮起同样的灯;白天有雾时,那些巨大的窗户外,同样雾气沉沉;下雨时落一样的雨滴;狱卒和犯人踩着同样的锯木末,留下同样的脚印;同一把钥匙打开和锁上同一扇门——我感觉我已经做了很久陪审团主席了,外面皮卡迪里大街上的繁华恍若隔世,而那个被害人却一直萦绕不去,片刻不曾消失。但有一点不能遗漏,实际上,我从未见到被害人看一眼那个凶手。我想了一遍又一遍,“为何他不看呢?”但他始终未看一眼。
而且,自从有人出示他的肖像后,他也没再看过我,直到审判结束前几分钟。那时已是晚上九时五十三分,陪审员开始退席讨论。那三个教区蠢蛋却让讨论麻烦不断,我们不得不两次回到法庭,请求大法官重读笔记的某些段落。我们九人都对之毫无疑问,我相信,法庭上其他人也不会有疑虑吧;但是,那三人却故意捣乱,扯住一个问题纠缠不休。
最终,我们占了上风。到十二时二十分,陪审团重回法庭。
那被害人正站在陪审席对面。我刚坐定,他就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他似乎很满意,手里拿着一大块灰色面纱,举过头顶轻轻挥舞。他好像第一次把胳臂举过头顶。我们做了“有罪”的裁定。再看时,只见那面纱落下来,消失了,他站的地方空空如也。
按惯例,在判决死刑前,法官会问犯人还有何话说,他咕哝了两句。第二天,报纸头条却报道说是“几句含糊、混乱、听不清楚的话,很明显,他是在抱怨此次审判的不公,因为陪审团主席蓄意反对他”。
实际上,他这番饱受争议的原话如此:“我的主啊,那陪审团主席走进陪审席时,我就知道一切已成定局。我的主啊,我知道他不会饶过我,因为,在我被捕那晚,他曾走到我床边,叫醒我,然后将一条绳子勒在我脖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