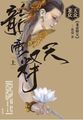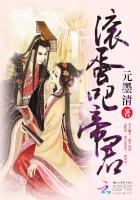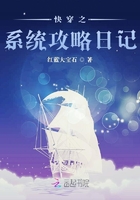我向来爱观察人,发现人们普遍缺乏一种勇气,就算那些智力超群且极有教养的人,也不敢袒露自己内心的许多怪异体验。人们害怕自己不被认同,或不为听者的内心所感动,反而招来怀疑和嘲笑。一个诚实的旅行家,若是见过类似海蛇的怪物,肯定会津津乐道;但是,这同一个人,若是产生某种奇怪的预感、冲动、臆想、幻象(所谓的)、梦境或其他显着的心理印象,承认之前总会犹豫再三。我以为,这些话题如此晦涩,也主要归因于人们对其讳之莫深。我们从不乐于交流彼此的主观经验,就像我们尤其擅长交流客观创造的经验一样。结果是,这些本应是大众的心理体验,却成了异常的现象,若这些体验极不完美,更是如此。
在以下的叙述里,我并不打算建立、反对或支持任何一种理论。
我了解那个柏林书商的故事,也研究过最近某位皇室天文学家妻子的案例,和戴维德·布鲁斯特爵士所言一致;我也听过一位私人好友有关鬼怪幻觉体验的细节描述。最后一件事我不妨交代一下,受害者(一位女士)和我并不沾亲带故。她的某个幻觉可能有助于解释我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但这只是一部分,整个事件则毫无根据。发生这样的事,倒并非因为我有怪癖,我以前没经过这样的事,以后也无类似经历。
英格兰曾发生一起谋杀案,至于发生在多少年前,或如何罕见,都不重要。谋杀犯的恶行不断被公之于众,我们早已听厌倦了;我会尽量隐藏暴行的细节,罪犯的尸体现在早已埋在纽盖特监狱下了。我也会尽量避开直接描述罪犯的个人身份。
谋杀案最初披露时,还没人怀疑罪犯——或者应该说,我当时还不完全了解事实,还没有公开怀疑后来被逮捕的人。当时报纸从未提及过他,而且也不可能有人公开描述他。我所知的基本事实就是这样。
那天早餐,我照常打开晨报,报上首次报道此案,我饶有兴趣,集中精神读完了文章,读了两遍或三遍。案发地点在卧室,当时我放下报纸,心里咯噔一闪,我好像看见那卧室从我屋里穿过,就像一幅画,画在奔腾的河上。尽管转瞬即逝,但是非常清晰;我好像活生生地看见尸体从床上消失一般。
这感觉突如其来,惊异至极,要知道,我住的地方一点都不传奇,房子在皮卡迪里大街上,离圣詹姆斯大街拐角很近。我以前也没有这种幻觉。那时,我坐在安乐椅上,椅子上仿佛生出一阵怪异的战栗(但有一点要说明,这把椅子脚上有小轮,极易转动)。我便走到一扇窗前(房间在三楼),想看看皮卡迪里街上的市景,放松一下眼睛。
此时秋光明媚,街上人群熙攘,一片生机。风很高。从窗户看出去,只见公园里一阵疾风拂过,卷起许多落叶,如漩涡一般飘舞。风过后,树叶又散落在地上。路尽头有两个人,正往东走去。两人一前一后,前者不时回头往后看。后面那人约在三十步外跟着,一直举着右手,像是在威胁什么。一开始,他在人群里举着这手势,一动不动,吸引了我;后来,我却发现并无人注意他,更加奇怪。两人在人群里穿行,却走得很稳,仿佛旁若无人;也不见有人让路,或碰到他们,或看一眼。经过我窗下时,两人都抬头盯着我。两张脸看得很清晰,我相信,若是在别处遇到,我也能认出来。倒不是我有意注意脸的特征,只是走在前面那人个子极矮,后面那人则面色蜡黄。
我是个单身汉,家中只有一个男佣和他妻子。我自己在一家银行分行做事,任部门经理。我倒想这工作能如人们想的一样轻松。那年秋,因为出差滞留于小镇上。没生大病,但健康也不太好。读者可能以为,我只是心理疲惫,生活过于单调压抑,并且患了“轻度胃弱”——这是我咨询医生时,那个名医生写在病历上的,这倒让我感觉,我那时的健康实在好得不能再好。
再说这案子,随着案情明朗,公众关注度增高,街头巷尾议论纷纷,我只能尽力不闻不问,避开这案子。但是,我还是知道了,嫌犯已定罪为蓄意谋杀,押送到纽盖特监狱了。另外,因为偏见,辩方需要时间准备材料,中央刑事法庭已确定延期审判。我应该还知道,大概在何时法院会开庭审理此案。
我的起居室、卧室和盥洗间都在二楼,去盥洗间必须经过卧室。实际上,盥洗间曾有一个门和楼梯连通,但我用洗浴设备堵住了——已经堵了很多年。后来就把门钉上了,挂了布遮着。
一天夜里,很晚了,我站在卧室里,想着在用人睡觉前吩咐一件事。我正好面对盥洗间唯一的那扇门,门关着,用人则背对着门。我正要吩咐他,门却突然开了,只见一个男人伸头张望,急切又神秘地和我招手。此人脸色蜡黄,正是我在大街上看到那两人的后一个。
那人招了手,便退回去关了门。我急忙拿了一只蜡烛点燃,进卧室,打开盥洗间的门。我预感那人不在里面——我也确实没看见他。
定神回来,才发现用人一脸讶异地站在我背后,我便转身和他说:
“德里克,你信不信,我刚才清楚看见了一个——”说话时,我的手放在他胸前,他却突然浑身战栗,只叫道:“哦,天啊,是的,先生!一个死人在招手!”
德里克是跟我二十多年的老仆,很忠实,若他也说看见了,肯定是在我碰他时看到的。我碰他时,他的变化令人吃惊,我完全可以相信,在那一瞬,他以某种神秘的方式从我身上得到了这个印象。
我便吩咐他拿些白兰地来,也让他喝了一口,自己也喝了些。但对此前的事,只字未提。思来想去,我可以肯定,只有皮卡迪里大街那一次,以前绝对没见过那张脸。上次是我站在窗口,他抬头看我,刚才则站在门口和我挥手。我仔细比较了两次的表情,我猜他第一次是为了让我记住他,第二次则是确认我是否能立即认出他。
一夜不适。我有个莫名的预感:那人不会回来了。到天亮,我才睡沉了。不久,却被德里克唤醒,只见他手里拿了一张纸到床前。
刚才我似乎隐约听到,用人为了这张纸,在门口和送信人争执。
这是张通知单,中央刑事法庭将在老贝利街开庭,请我加入陪审团。以前却没人叫我加入陪审团的,约翰·德里克自然清楚。他认为——我也不能肯定这是否有理——陪审员的资格都是比我低的,所以开始拒绝接受通知单。送信人却很强硬,只说,我去不去和他无关,他只是通知送到,我怎么处理是我的事,和德里克没有关系。
开始两天,我也犹豫不决,不知该不该去。有一点我能肯定,即我对任何人都无偏见或偏爱,也不会影响他们,正如我在此所说的话一样真实。最后,我决定去,就算是聊做排遣吧,有些变化总是好的。
开庭时间是十一月的某天早晨。那时皮卡迪里大街浓雾弥漫,坦普尔栅门东口还是一片漆黑。我到了法庭,只见走廊和楼梯上都亮着瓦斯灯,显得灯火通明,法庭里也是如此。官员一直将我领到“大法官庭”,却见里面人群拥挤,才知道当天要审判的正是那个杀人犯。但是,我也并不完全肯定,这两件事我都记不太清了。
我在陪审员等候席上坐定。大厅里烟雾缭绕,我只能尽量环视。法庭的大窗户外依然雾气沉沉,像是罩着一副深色窗帘;有时车轮碾过大街上散落的麦秆或空罐,吱吱嘎嘎作响;大厅里则人声嘈杂,偶尔还冒出一声尖哨声,还有人在大声唱歌。不久,两名法官走进大厅坐定,法庭立即安静下来。轮到犯人出庭了,他刚一出现,我就猛然认出他来,正是那天在大街上走的两人中的前一个。
当时若有人点我的名字,我怀疑自己是否能立即答出。法官点了陪审员名单,我大概排在第六个或第八个,到这时,我才答了一声“到!”
再说那犯人,就在我走进陪审席时,突然焦躁起来,和他的律师招手——他本来在四处打量,并无注意。他显然对我抱有敌意,我甚至看见,律师双手撑着台子,摇头对他耳语了几句。被告的敌意这才暂时打消了。
后来,这绅士告诉我,犯人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要不惜代价反对那家伙!”律师骇了一跳。但是犯人并未做任何解释,他承认说,在点到我名字前,他都不知道我叫什么。律师当然没有照他的话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