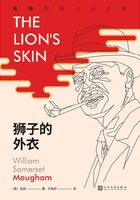“没有。我又往里面跑了一段,五百码左右吧。停下来,把灯举过头顶,却只看见标量距离的数字,斑驳潮湿的洞壁,水从拱顶上渗下来。我实在受不了这黑洞了,便很快跑出来了,比进去时跑得快很多。
我又打着我的红灯照了那盏红灯周围,又爬上铁梯看了上面的走道,然后下来,跑回这里。我向两边都发了电报:‘收到警报,不知何事?’
两边都回复说‘一切如常’。”
他用一根冰冷的指头划过我的脊背,我只好勉强忍着,给他解释说,那个身影只是一种视觉上的幻觉;可能是用眼过度,某种脆弱的功能神经障碍引起的。据说很多病人都饱受其苦,甚至有的人已经被折磨得十分敏感了,在自己身上做实验。“至于那个尖叫的幻觉,”我说,“我们说话小声一点,你不妨听一听这个奇异山谷里的风声,吹得太狂了,像是在电报线上弹奏竖琴。”
我们便坐着听了片刻,他回答说,那倒是不错,他本来就知道风吹电线的声音,他冬天晚上经常在这里守夜,一个人,彻夜看着。他仿佛央求似的说他的话还没说完呢。
我忙说抱歉,他便碰了一下我胳膊,接着慢慢说道:“那影子出现不到六个钟头,铁路上又发生了许多难忘的事。那十个钟头内,不断有死人和伤者从隧道那边送过来,从那个身影站的地方通过。”
我不禁战栗起来,浑身犹如虫爬,厌恶至极,只好极力克制,但毫无效果。我只是回答道,这大概纯属巧合罢了,想加深他的印象。不过,像这种巧合事件确实时有发生,处理事情时必须考虑在内。但是我必须承认,我补充道(我似乎看见他马上要开始反驳了),有常识的人在计划日常生活时是不允许有太多巧合的。
他又央求让他把话先说完,我只好又为自己多嘴说了句抱歉。
“这个,”他说着,又把手搭到我胳臂上,用那双深陷的眼睛往自己肩后瞥了一眼,“都是一年前的事了。又过了六七个月,我才从那次惊吓中恢复。一天早上,天刚破晓,我又站在门口,朝那盏红灯看,竟又看到那怪物了。”他顿了一下,直勾勾地盯着我。
“它喊了吗?”
“没。它沉默着。”
“那它挥手了吗?”
“没。它只是背靠着灯柱,用两手挡着脸。就像这样。”
我又看着他做动作,这次却是哀悼的动作。我在一些古墓的石像上见过这种姿态。
“你过去了吗?”
“我却进屋坐下了,一半是因为想集中精神,一半是因为我感觉眩晕。我再出门去看时,天光已经大亮,鬼影早不见了。”
“然后没什么事吗?接着没发生什么吗?”
他却用食指在我胳臂上点了两下或三下,每次都惊惧地点点头:
“就是那天,有一辆列车驶出隧道,我注意到我身边一节车厢,似乎有许多手和头绞在一处,像是什么在挥舞。我见此情形,立即打信号让司机停车!司机关了发动机,拉住刹车,但列车还是滑行了一百五十多码。我便赶上去看,正在这时,听见一阵恐怖的尖叫和哭喊。才知道其中一个隔间里有位年轻美丽的女士当场死了。然后便抬到这里,就放在我们之间的地板上。”
我不由得推着椅子后退了几步,看着他指的那块地面。
“是真的,先生。真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我就怎样告诉你。”
我一时大脑空白,不知道说什么,只觉得口干舌燥。风吹着电线,仿佛带着一种长长的哀号,诉说那个故事。
他便接着说道:“现在,先生,你应该知道了,我为什么苦恼得很。那怪物一周前又回来了。然后就时不时出现,很骇人。”
“在那盏灯边吗?”
“就是那个信号灯。”
“你看见它做了什么没?”
他又重复做了之前的手势动作,这回却更加激情和猛烈了,“拜托,天啊,快闪开!”
然后继续说道,“我简直一点也没法安宁了。它一直叫,叫了我好几分钟,那声音十分痛苦,‘下面的人!当心!当心!’还不停挥舞着手。甚至摇响了我的铃铛——”
我见缝插针。“昨晚我在这边时,它也摇了你的铃铛吗?然后你才出门去?”
“两次。”
“啊,是了,”我说道,“你完全被你的幻觉误导了。那时候我眼睛一直看着铃,耳朵也听着,我也是个活人,却不曾听见铃声响。
不,应该说除了你和车站联系的时候,其他任何时候都一切如常,不曾响过。”
他摇摇头。“我却从没有犯过一个错误,先生。况且我也不会把人的铃声和怪物的铃声混淆。那鬼物的铃铛发出一种极怪异的震动,仿佛凭空传来的一般。我可没有说那铃铛是在我眼前响。我一点不奇怪你没听见。但是我听到了。”
“你往外面看时,真的好像看到那怪物在那里?”
“千真万确。”
“两次都在?”
他断然答道:“两次都在。”
“你现在就和我一起去门口看看怎么样?”
他咬了咬下唇,似乎有些不情愿,但还是起来了。我开了门,站在石阶上,他却只立在门口。只见外面那危险信号灯闪烁着,隧洞口黑沉沉的。峭壁岩石又高又湿,再往上看却是一片星空。
“看到它了吗?”我问他,仔细看他的脸。他睁大了眼睛,紧张地张望着,我也朝他的方向巡视,似乎他看到的也不比我多。
“没有,”他答道,“它不在那边。”
“我也一样。”我说。
我们便进了屋,关上门,各自坐下。我正想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如果这算是的话——他却先说话了,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似乎我们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严肃的问题,我发现自己已经落了下风了。
“现在你应该明白了吧,先生。”他说道,“困扰我的那个可怕的问题就是,那怪物究竟意味什么?”
我不确定,我告诉他,尽管我能完全理解。
“它在警告什么呢?”他说着,盯着炉火陷入了沉思,或有时看我一眼。“危险是什么?在哪里?这条铁路线哪里有危险吗?有什么可怕的灾祸要发生?经过前两次事件后,这无疑已经是第三次了。它死死地缠住我,可怕极了。我怎么办?”
他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头的热汗。
“要是我发电报报警,无论一边,还是两边,我都找不到理由,”
他继续说道,一边擦着掌心,“我只会惹一身麻烦,一点好处没有。
他们会以为我疯了。要是我发电报过去——说:‘危险!注意!’他们问:‘什么危险?哪里?’我只能说:‘情况不明。但是天啊,注意!’然后他们就把我撵走了。他们还会做什么?”
他只顾在那里纠结,实在惨不忍睹。一个本分人,因为职责压力过大,感觉生活不可理喻,不堪忍受,便生出这样的精神折磨来。
“它第一次站到危险信号灯边时,”他继续说道,用手往后拢了拢黑发,两手按住太阳穴揉着,显得痛苦万分,“既然真的有事故要发生,为什么它不告诉我要发生?既然事情可以避免,为什么不告诉我怎么避免?它第二次来为什么又遮着脸,为什么不告诉我危险,‘她要死了。叫他们让她待在家里’。要是它两次来,只是为了暗示我警告不虚,让我为第三次做准备,那现在为何又不明说?呵,但愿主保佑我吧!何苦为难一个偏僻小站的穷信号员!为什么不去找那些有声望又有权势的大人物?”
我见他如此痛苦,突然意识到,看在这可怜人的份儿上,也为了公共安全,我必须设法即时安抚他。因此,我便把我们之间那些似是而非的问题都撇开了,只是对他说,无论谁在这位置上,都要恪尽职守。
他至少可以明白职责如此,有所慰藉。尽管他无法弄清楚那些混乱的表象。我这样做,远比说服他放弃自己的罪恶感有效果。
他镇静下来。在这个岗位上,必须慎之又慎,尤其到了深夜,更加考验注意力:于是我到凌晨两点便先走了。我本来提出要陪他守一夜,他却不肯听。
我爬上那石阶,不止一次地回望那盏红灯,我不喜欢它,如果我的床放在下面,我一定会睡不好的。我没理由隐瞒这些。我也不喜欢那两次事故,那个死去的女孩。这些都无可隐瞒。
但是,我现在考虑最多的是,既然我已知道事件的前因后果,我应该怎么做?我已经确定了这是一个勤勉踏实、聪明又机警的人;但是他还能坚持多久,照他现在的心理状态?尽管职位低下,但却握着最大的信任,就算我愿意陪上自己的性命(假如),他能做到继续恪尽职守吗?
如果我把他说的话都告诉他公司上级,却不先与他坦白,商量一个中间方案,我又忍受不了那种背叛的罪恶感。左思右想,最后决定先陪他去看这方面非常厉害的一位医师(我先暂时为他保密),征询医生的意见。他先前通知我了,次日晚上他会倒班,日出后一两个钟头他下晚班,等到日落时再上班。我便约定了去的时间。
次日傍晚却是十分可爱,我提前出发了,边走边看风景。那时候太阳还未落完,我信步穿过荒野小道,一直走到峭壁附近。我心下暗忖,还可以再走一个小时,半小时去,半小时回,回来的时间刚好去信号所。
在去散步之前,我不由走到了峭壁边缘,探头往下看,我第一次正是在这里看见他的。一看不要紧,只见隧道口旁边一个人形,用左边衣袖遮着脸,疯狂地挥舞着右胳臂,我顿时感觉被抓住似的,惊恐不已。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稍定住神,因为那时我确实是看见一个人影,的确是一个人,另外还有几个人站在不远处,看起来他像是在和他们排演手势,但危险信号灯没有亮。在靠灯柱的地方,用木头和柏油帆布搭了一个小棚子,完全是新的,而且还没有一张床大。
我强烈预感到出事了,猛地闪过一丝内疚,害怕因为我撇下他一人,又没有告诉其他人去照看他或纠正他的行为,以致酿成大错。我便以最快的速度冲下那条小道。
“出什么事了?”我问那些人。
“信号员今早上被杀了,先生。”
“是那个信号所里的人吗?”
“是的,先生。”
“难道是我认识的那个?”
“你应该记得他,先生,要是你认识他,”其中一人说道,还郑重地脱了帽子,揭开柏油帆布一端,“你看,他的脸死得很平静。”
“哦,这都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小棚子盖上后,我问道。
“他是被机车轧死的,先生。全英国没几个人比他更懂这种工作了。却不知道为何他没有及时离开铁轨。当时已经是大白天了,他还点着灯,提着灯盏在手里。那机车从隧洞里出来,他正好背对它,车就轧过去了。那就是开车的司机,他会告诉你经过。汤姆,你告诉他吧。”
那人身着粗布黑衣,正站在隧道口边,听见有人叫,便回来了。
“我刚从隧道里绕弯出来,先生,”他说道,“就见他站在路尽头,我好像用望远镜看见的。但已来不及减速了,他平常工作很谨慎,但这回他却好像没听见汽笛声似的。所以,火车冲过去时我便关了汽笛,用最大的声音喊他。”
“你怎么叫的?”
“我就喊,‘下面的人!当心!当心!天啊拜托,快让开!’”
我大吃一惊。
“啊!当时真是糟透了,先生,我不停地叫他。我实在不忍看见,便用这只胳膊挡住眼睛,另一只胳膊用力挥舞,一直到最后;但是无能为力。”
这件事的离奇之处实在一言难尽,为了避免赘述,在结束前,我想对诸位指出,司机的警告只是一种巧合,不仅包括不幸的信号员纠结不休的那些话,而且我自己——不是他——添加的话,乃至他模仿过的手势,都只是我脑中的虚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