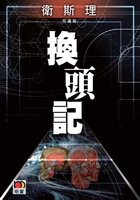“老三,我也听说你病得挺重,趁你人还在,趁我还愿意跟你坐下来谈,”小尾巴说,“赶紧帮你儿子做好主,走了也能安心,你现在是可以逞能,但是你想过没有?等你人没了,你儿子咋办?债还得一样还,而且一分还不能少。”
苏敬钢拿起面前酒杯,喝了一口酒。
苏敬钢,现实就是这么残酷,你无能为力,你必须认输,你已经是将死之人,尊严和骨气对你已经毫无价值,你不能把它们带进棺材,也不能把它们刻进墓志铭,可是舍弃它们却可以救你的儿子,让他免受屈辱的折磨。苏敬钢在心里对自己说——这是一桩只赚不赔的买卖。
“能放过我儿子吗?”苏敬钢看着小尾巴,“我不可能让他这辈子都在还钱。”小尾巴扬起眉问:“放过?啥意思?好像现在是我勒索你们爷儿俩似的!”苏敬钢说:“我知道你不差这点儿钱,别让我儿子还了。”小尾巴抽了一口烟,说:“你得给我个理由。”
苏敬钢说:“算我求你。”
“啥?”小尾巴略微偏过头,“我没听清,你再说一遍?”
“算我求你。”苏敬钢一字一顿着说。
“老三,你说谁能想到?你也有求我的一天!”小尾巴长舒一口气,心满意足,又点燃一根烟,回忆着说,“老三,我比你大两岁,按理说你应该叫我一声郭哥。算一算,咱俩认识也有三十多年了,可不算短!年轻那时候我就瞧得起你,本来咱俩可以做兄弟的,可你就是他妈太嚣张,太不识相!就我这条瘸腿,人家当面叫我郭总,背地里都叫我郭瘸子,还不是拜你所赐嘛!这件事儿我后来有再找你算过账吗?你别以为是因为一直有周国大护着你,我才不敢动你,因为你郭哥我不是小心眼儿的人,冤冤相报何时了?当年我答应了两清,就是两清,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你对大昆不就是报复吗?”苏敬钢打断小尾巴,他想骂娘,可还是忍住。
“都怪你那兄弟太不识相!”小尾巴一副怒其不争的表情,“当年我真没想过要废他,就是想吓唬吓唬他,可是这种事儿谁都说不准,遭了就遭了——苏老三,你知道为啥你和你兄弟混得不如你郭哥我强吗?知道我比你们强在哪儿吗?我识相!在社会上混,你必须得识相,就是要知道啥时候该逞能,啥时候该服软,像你们这种光知道逞能从来不会服软的,就算你们是猛虎恶龙,也早晚被抽筋扒皮。”
“你们啊——”小尾巴用手戳点着自己的太阳穴,拧着唇角说,“太傻!没脑子!”
八幺子在一旁附和说:“过去的恩怨都过去了,郭哥是大度的人,老三也不是不懂道理,他这不就学会服软了嘛!这不是在跟郭哥求情呢嘛!”小尾巴像模像样地问苏敬钢:“你这算是在跟我求情吗?”苏敬钢说:“是。”——“这钱——”小尾巴犹疑片刻,掸掸烟灰说,“我可以不要了,你儿子也不是成心的,看在你我多年交情,我就当一回冤大头!不过,钱虽然不用还,但是礼节还得还,否则传出去让人知道了我被人弄丢一批货,还忍气吞声咽下来,那以后再跟我做生意的人还不都敢私吞我的货啊?我对手底下的人也交代不过去啊!老三,你说是不是?”
“你说话算话?”苏敬钢干脆地问。
“当场立字据!”小尾巴信誓旦旦。
“你要啥交代?”
“给我跪下。”
苏敬钢从椅子上缓缓起身,站在原地,双膝微曲着下降。
“爸——”苏凉也从椅子上起身,哭号着。
“苏敬钢!你他妈给我站直了!”
包间的门被推开,周晓燕三两步走到苏敬钢身边,伸手撑起他屈膝向下的身子。苏敬钢一下子回过神儿来,惊讶地说:“你来干啥?”——“给我站好!”周晓燕一使劲儿,拉直了苏敬钢的腰和背,又用手背轻抽在苏敬钢的脸上大骂,“你他妈给我清醒点儿!”
“燕子姨!”苏凉哽咽地唤着,他从未见过如此凶神恶煞的周晓燕,但是此刻的周晓燕却令人感到强大、温暖、安全。周晓燕见到呆立在一旁的苏凉,眼圈儿微微泛红,一改对苏敬钢的大吼大叫,语气温柔地安慰苏凉说:“凉凉不怕,有燕子姨呢!”
“燕子啊!”八幺子表情费解地说,“老爷们儿之间的事儿自己解决,你个女人来蹚这浑水干啥?”——“八幺子,你不是人!”周晓燕破口大骂,“你他妈也算是老爷们儿?你他妈还不如一条好狗!你当年差点儿就去要饭那时候,三儿是咋帮你的?我哥是咋对你的?你他妈就是没良心的狼崽子!有奶你就认娘,有钱你就认爹!你他妈就是个王八犊子!”——“周晓燕!你他妈给我嘴干净点儿!我看你是女人,不跟你一般见识!你哥人都没了,别老把他搬出来吓唬人!周大哥是好人,对我也不薄,我心里念着!可以前的交情跟今天这事儿不沾关系!生意是生意,钱是钱,我好心帮老三讲情,反倒被你骂个狗血喷头,我他妈冤不冤啊?”八幺子猛敲了两下桌子,冷不防被周晓燕骂了个无地自容,大气直喘。周晓燕像一捆被点燃的干柴,浑身散发灼人的怒火:“你们这帮不要脸的孙子!我哥要是还在,你们谁他妈敢这么仗势欺人?谁他妈敢硬碰硬地拼一把?一个个穿得人模狗样,全他妈是缩头王八!”
小尾巴终于说话:“燕子,你骂够了没?骂够了咱就说事儿!你要是能替老三出一百二十万,我随便你骂——你能吗?”周晓燕大骂:“小尾巴,亏你也是出来混的!你为啥非得要老三跪?不就是因为当年老三撅了你的棍儿不服吗?你他妈现在乘人之危,你还是不是人?”——“你闭嘴!”苏敬钢喝止周晓燕,转而对小尾巴说:“你现在立字据,我儿子不欠你一分钱,我现在就跪!”
“好!”小尾巴跟身后壮汉要过纸笔,潦草签了一张,指着苏敬钢说,“跪下!”
苏敬钢甩开周晓燕钳住自己的胳膊,单膝着地,另一条腿也在慢慢地向下弯曲,高大的身子向着地面亲吻,他嘴里喃喃地说:“放过我儿子……”
“我操你大爷——”
只见周晓燕在眨眼间冲到小尾巴跟前,还没等四个壮汉来得及阻拦,一把短枪已然从她腰间拔出,顶在小尾巴的太阳穴上——“我他妈要你命!”周晓燕嘶吼着。她手中的枪,正是苏敬钢当年造的那把、还有一颗钢砂残留其中的枪。周晓燕用枪管戳着小尾巴的头大喊:“谁他妈也别上来!”小尾巴摆手示意壮汉退下,斜眼看了一眼周晓燕和她手中那把他熟悉的短枪,想不到的是时隔多年,在他久经大场面、历经无数风雨后,居然还是被这把土枪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周晓燕一只手摁在小尾巴刚刚立好的字据上,另一只手上的枪始终抵在小尾巴太阳穴上,恶狠狠地说:“签字!”小尾巴沉默不动,周晓燕把枪抵得更死,重复道:“叫你签字!你知道我有胆子崩了你!”
“燕子!”苏敬钢站起身叫着。
“不用你管!”周晓燕头也不回地喊。
“你为了这爷儿俩跟我拼命?何必呢!”小尾巴镇定地恐吓周晓燕说,“你也不为自己想想?”
周晓燕瞪着小尾巴的眼睛说:“我豁出去了!”
小尾巴在逼迫下签好了字据,被周晓燕一把夺过揣进口袋。“我可真替你不值!”——“少他妈废话!”周晓燕紧紧攥着枪,命令小尾巴,“叫你的人让开!”小尾巴笑而不语。周晓燕冷不防抓起桌上的方便筷子,插在桌面上撅折一半,手握折断的尖刺顶在小尾巴喉咙,尖刺只扎进去浅浅一点,血从小尾巴脖子上渗出。“他妈的是你们给脸不要脸!”周晓燕手中一使劲儿,尖刺被转得更深,疼得小尾巴龇牙咧嘴。周晓燕朝苏敬钢喊:“带凉凉先走!”苏敬钢立在原地不动,苏凉冲过来拉住父亲说:“爸!走吧!”周晓举枪对着小尾巴的头向后退着,嘴里说:“谁也别动!反正我的命不值钱,跟哪个抵命都不赔本!”
三人急匆匆回到家,苏敬钢让周晓燕跟苏凉赶快收拾东西离开。苏凉惊魂未定地说:“报警吧。”苏敬钢说:“要是报警有用,他们也不能那么嚣张。你带着燕子姨先去别的地方待一段时间,你们互相照顾好,我知道就放心了。等我想办法解决,否则就算我死了也不踏实。”周晓燕和苏凉被苏敬钢强行送下了楼,正当他们手里提着行李还没走出院门时,早上绑走苏凉的面包车急速拦在他们面前,车门“哐当”一声被拉开,四个壮汉冲下来,人手一把片刀。
苏敬钢看见了,小尾巴就坐在副驾驶位。
苏敬钢一把推开周晓燕和苏凉,从腰间拔出短枪——这把枪被遗忘在苏敬钢的床下三十年,枪身上的白银雕花上生了一层氧化的黑斑,木制的枪托已经发霉开裂——苏敬钢不知道这把枪是否还能像三十年前一样血气方刚,他左手举枪,贸然朝前扣动扳机,“轰”的一声,钢砂飞散,冲在最前面的壮汉应声倒下,胸前黑糊一片,胖圆的脸像一颗烤焦的猪头。这把枪完成了它一生中最后的使命,枪身随着轰鸣声炸裂开来,碎烂的木屑深深嵌进苏敬钢的手掌中,他的左手血肉模糊,垂了下来。
“爸——”苏凉发疯似的冲向又一个壮汉,他含胸低头,箭一样把自己射出去,头狠狠地撞在壮汉的胸口——这是父亲教他的“撞羊头”。壮汉面露痛苦,却纹丝未动,抬脚把苏凉踢出老远。苏敬钢冲过去扑倒壮汉,扭打作一团。壮汉的力气大过苏敬钢,几次把苏敬钢压在身下,长长的片刀垂直砍下,苏敬钢用小臂挡,他似乎已经感觉不到所有疼痛,两只废手合力扭断了壮汉握刀的手腕,夺过片刀,劈头盖脸就是一通乱砍。壮汉挨了几刀,飞也似的跳起躲开,苏敬钢双手撑着起身,又冲过去砍,他的头上是血,身上是血,手上也是血,他嘴里在大骂,他的眼睛在喷火——这是周晓燕眼中那个当年在大西菜行横扫千军万马的拼命三郎;这是苏凉今生从未见过的父亲。
一把弹簧刀干净利落地插进苏敬钢的左肺。
太阳已经斜斜地朝天边的云层后移动,血腥的火烧云映在空中,像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被这个灿烂的男人点缀上了突兀的一笔。苏敬钢仍然直挺挺地站在原地,他不由自主地转过头朝周晓燕和苏凉回望,他们惊恐的眼神令他心酸,可是他哭不出来,也说不出话。他的耳朵里响起一种悦耳的声音,来自一个邈远的方向,那声音像是一个声线柔美的女人在对自己低语,他的身体软了下来,他的手撑住白色面包车的车门,一个血红的大手印赫然可见。可是他突然两眼一瞪,当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突然一把拉开副驾驶的门,抬手举刀,朝小尾巴砍去,小尾巴猝不及防,第一刀就被砍中脖颈,头直接趴倒在车前。苏敬钢紧接着又是几刀,刀刀砍在小尾巴后脑。他挥舞着手中片刀时,弹簧刀还插在他的身上,露在身体外的短短的刀柄随着他一高一低的胳膊上下晃动。两个壮汉回过神儿来,上前对苏敬钢狂砍几刀,苏敬钢终于倒下了,刀从他的手中滑落,他的手掌还在无力地朝小尾巴倒在血泊中的头上拍打着。
救护车赶来时,小尾巴一帮已经开着面包车将小尾巴送往医院。苏敬钢躺在血泊中双目发直,周晓燕和苏凉双双跪在地上,用膝盖撑着苏敬钢昏昏欲睡的头。
“需要抢救,车里地方不够,只能跟一个人!”
救护车里,三个急救员加上苏凉四人合力把苏敬钢抬到担架上。
救护车直奔陆军总院。三个急救员给苏敬钢戴上氧气面罩,打止疼针,绑紧出血口。苏凉坐在一旁握紧苏敬钢的手,泪流不止。他看着从苏敬钢肺里流出的紫红色的血一点点减少,苏敬钢的眼皮频繁地闭合着。“爸!你坚持住!”苏凉哭喊着催促司机再开快一点儿。
“堵车啊!没办法!”司机头也不回地说。
苏凉突然打开救护车后门,不顾阻拦跳下车,眼前东西和南北两条交叉路口处塞成死路,两个顶在一起的私家车主正站在十字路中央对骂。“我操你们妈!都给我让开!”苏凉像个疯子一样对他们叫骂。“他妈的有你啥事儿?”其中一个车主指着苏凉的鼻子骂,气哼哼地绕过面前横七竖八的车辆朝他走过来。“快回来!”两个急救员跳下车,强行将丧失理智的苏凉拉上救护车。
苏凉不知如何是好了,他年轻的生命仿佛也随着父亲苏敬钢身体里不断流淌出的血滴一点点在消逝。此刻,时间对他来说是最奢侈也最残酷的东西。
度秒如年。
“左拐!拐进青年公园!绕过去!”
“青年公园不允许进车!”
“我求你了!快他妈开进去!”
司机把救护车向左一转,开进了青年公园的大门。
苏凉的手心里感觉到,父亲的手指尖微微地动了一下。
“前面过去不了!”
苏凉跳下车去看,几根半人高的拦车柱立在面前,死路一条。
“只能倒回去。”
苏凉的耳朵里嗡嗡地响,他迷失在儿时最熟悉的地方。他的双脚踏在青草地上,身后的假山有涓涓细水从孔洞里涌出,山下的小池塘中有金色的鲤鱼在游。
救护车的车后门大敞着,落日的余晖斜射进去,温暖了苏敬钢的身体。苏凉看见,他的父亲苏敬钢微微抬起了头,拼命用眼底的一道残光向车门外望着,他的右手极其缓慢地抬起,攥成了拳头,“咚、咚、咚”连续而又沉闷地敲击在身旁的氧气瓶上。“躺好!别乱动!”急救员想要摁下苏敬钢的手,却怎么都摁不动。“等一下!”苏凉一个箭步蹿回车里,握紧苏敬钢的手问,“爸?你是不是找我?是不是有话想说?”苏敬钢的大手在苏凉的手中轻轻摇晃着,仿佛用尽了浑身的力气,他的头依旧微微地抬着,苏凉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苏敬钢盯住不放的,是那座假山。
苏敬钢露出了一个释然的笑。
那笑容,多年前苏凉曾在他的脸上见到过。那是在母亲离开家的两三年后,苏凉已经上初中,有一天当他回到家打开门,邓丽君曼妙的歌声萦绕在老房子的客厅里:
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
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
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
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
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
苏凉再仔细听,那并不是邓丽君。他轻悄悄地脱了鞋,光着脚走进客厅。被夕阳映照成金色的客厅比平时宽敞了许多,尘埃飘浮在斜光下,安静地飘浮着。父亲苏敬钢仰面躺在老沙发里,双手垫在头下,闭着眼睛,悠然自得。他的身体太长,两只脚丫子延伸到了沙发外,随着节拍慢悠悠地晃动着。苏敬钢显然没有发觉儿子进门,苏凉蹑手蹑脚地走近一些,他不确定父亲是否睡着了,只见他的睫毛在微微地颤动,嘴角挂着罕见的笑容。苏凉站在原地,静静地欣赏着父亲脸上舒适的表情,静静地听着老三洋录音机里传出的那动听的歌声——他终于听出,那是母亲的歌声:
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
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
“爸……”苏凉紧握起苏敬钢越跌越深的手,两只手之间隔着父子二人的血。
苏敬钢缓缓闭上了眼睛,头也渐渐沉下,躺进儿子的臂弯,他的脸上依旧带着难以磨灭的笑容。他的嘴巴再也发不出声音,他的耳朵再也听不见吵闹,浮现在他眼前的最后一幅画面是那座假山。苏敬钢在画面中看到了自己,十九岁的自己,身穿一身笔挺的中山装,踏着洒满夕阳的石板路,脚步轻盈地朝假山走去。假山下,一个十八岁的年轻女孩回过头,露出灿烂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