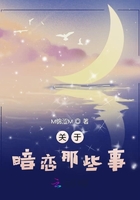我进入初中学习是一九七六年,也是中国多灾多难、动荡不安的一年。这一年,******、朱德相继去世,紧接着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唐山大地震,二十多万人在刹那间被夺去了生命。当人们还处在恐慌之中时,******也离开了人世。随后,“******”被打倒。
“******”的倒台标志着“**********”的结束,但“****”遗风尚存,大喇叭里的革命歌曲换成了常香玉的河南豫剧:“大快人心事,揪出******。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粱……”我们赶上了大字报热潮的末班车,老师从学校里领来了笔墨纸张,发给学生,写批判“******”的大字报。对于十三四岁的初中生来说,怎么了解那四个经常在电影放映前加映的《新闻简报》中威风凛凛的中央领导的罪行呢,我们只好从报纸上抄录一些一知半解的批判文章交差。不上课写大字报,在平时没有这样的机会,同学们异常兴奋,一个个龙飞凤舞,过足了瘾。班长拿着这些写得歪七扭八的大字报,带领同学们贴得到处都是。
因为唐山地震的影响,全国陷入恐慌之中,不时传出哪天有地震的小道消息,家家户户在院子里搭建起防震棚。我家把一张大木床抬到院子中央,在四条床腿上绑上木棍,撑起一个棚子,在上面搭块塑料布,一个简易防震棚就这样建成了。一家人挤到里面睡觉,倒是感到新鲜、有趣。一个下雨天,哥哥的同伴聚在我家打扑克,我则坐在门口看小说,为了防震,把一个酒瓶头朝下、底朝上放在桌子上,只要有震感,瓶子就会倒下。打扑克的吵闹声也没影响我读书,他们正在争执中,瓶子“啪”的一声掉在地上摔碎了。“地震啦!地震啦!”人们大喊着向天井里跑。当惊慌失措地站在雨里时,我竟然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出来的。大家似乎都没感到天在下雨。过了一会儿,也没见房屋晃动,这才突然醒悟:“是谁碰倒了瓶子?”
学校不敢在教室上课,于是,各班级由班主任带领,分散到没有房屋的树林中上课,换了环境,同学们都很新奇,学习并没有落下。冬天到了,家家都挖了半地下的防震棚,在院子里挖一米多深,就像新疆的地窨子,便于保暖。我们也不能在室外上课了,学生们又被圈回教室,老老实实地读书学习。
我在小学期间养成了读小说的习惯,到了初中更是胃口大开。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只用几天的课余时间就可读完。周日更是雷打不动的读书时间,一天下来,常常是读得头晕眼花,天昏地暗,沉浸在书中,半天也不能回到现实。我的各门功课成绩都在上游,有时上数学课感到内容简单,就开始走神,被课间读的小说情节所吸引,就悄悄地拿出小说,放在抽屉里偷偷地读。因为实在太投入,就连老师走到跟前了也没发觉,当然,小说被没收了。整个初中期间,我到处借书,先后读了《青春之歌》《红楼梦》《创业史》《播火记》等数十部长篇小说,还偷偷地读了当时被称作********的《苦菜花》,那是一个“左”得令人哭笑不得的年代,连苏联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也被称作********,但同学们都悄悄地学会了,经常聚在一起合唱。后来,学校破天荒地购进了一批图书,成立了一个小小的图书室,对我来说真是如鱼得水,再不用为了借书四处求人了。
初中只有两个班,两位班主任争强好胜,暗自较劲,同学们也受到影响,每次考试都要比一番,如果我们一班胜过二班,全班振奋;如果成绩低于二班,都感到脸上无光。为了鼓励学习,老师出招,每次考试奖励第一名一个练习本,我得到的本子最多。班主任是语文教师,一次,他说,下周的语文考试,谁考一百分,就奖励一个黄书包。当时,同学们大都是用的黑布书包,拥有黄书包就像现在开上了宝马车一样让人羡慕。于是,大家都拼命地复习,星期天我也没有读小说,一心一意地要把黄书包拿到手,结果考试成绩出来,我和几位同学都得了九十九分,全班没有一个一百分。直到多年之后,才明白过来,当时的黄书包只是一个诱饵,在语文试卷上减掉一分实在是太容易了。
初中生活即将结束时,同学们进入了紧张的复习阶段,参加中考对每位同学都非常重要,学校抓得紧,同学们也十分自觉,天不亮,就自动去学校复习。一次,天蒙蒙亮,已经在教室里学习半天的同学们走出教室休息,准备新一天的课程,刚走出教室,就见一位同学屁股上搭着一样东西,一走一呼扇。有同学上前一把给扯了下来,原来是他把内裤挂在了腰带上,惹得同学们哈哈大笑。
初中时写作文,喜欢用“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些词汇,现在才真正体会到这些词汇的含义。转眼间,三十年过去了,同学们各奔东西,老师们也进入了耄耋之年。很少有机会聚在一起。每当与老同学和老师见面,聊起初中生活,恍惚间重新回到了美好、充满欢乐的少年时代,整个身心都感到年轻了。
阿滢,原名郭伟,曾用笔名秋声。男,一九六四年九月生,山东省新泰市人,九三学社社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十大青年藏书家之一,专栏作家,《新泰文史》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