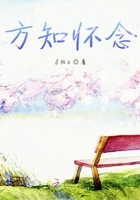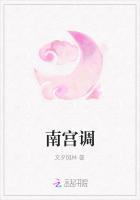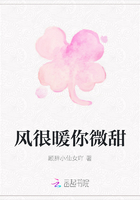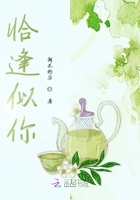一般而言,中国史上开始对乡村建立有系统的管理制度,始于周代。《周礼》称周代之中央地区为“国”,地方区域为“野”。在“国”中设六乡制来管理人民,六乡是:“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周。五州为乡,使之相宾。”又设比长、间胥、族帅、党正、州长等,以便管理。在“野”的地方设六遂制:“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赞,五赞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又设令长、里宰、邻长、鄙师、县正,以管理之。
但是《周礼》是汉代所出的伪书,书中所谈的多为儒家的政治理想,未必真正在周代实施过。我们现在对于周代的乡村组织所知不多,大致上,周代的农民多半居住乡村,除了交纳租税之外,在乡村从事生产,自给自足。他们住的地方叫里,里的负责人称里尹、里正、里君或里宰。里是一种极端封闭的社会,但为了共同防御外侮、防洪及灌溉之需,几个里乡之长官称为乡父老,简称乡老。
到了秦代,我们才对县以下的乡村组织有进一步地了解。秦分全国为36郡,郡下设县,万户以上的大县置县令,不及万户者设县长。县以下的组织,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这种乡、亭、里的组织,就是秦汉的乡村组织。
乡是县以下乡村组织中最大的单位,秦代之乡,大小如何,已不可考。汉代之乡,比后代之乡,面积较大,人口较多。就《汉书》“百官公卿表”及《汉书》“地理志”中所载西汉盛世的民户看来,西汉时代的一个县,约有四乡,东汉则有三个多乡,平均人口约二千户弱。乡有乡吏,如有秩、啬夫、游徼及乡佐等。乡户在五千户以上者置有秩,不及五千户置啬夫。因为五千户以上的大乡很少,所以啬夫是通制,有秩之名逐渐消失。啬夫负责地方上的讼事及收税,职权甚重。游徼掌地方治安,地位在有秩及啬夫之下。乡佐则协助有秩、啬夫收税。这些乡吏是郡县属吏,是地方政府之行政属吏,与乡官出身的乡三老不同,不可混为一谈。乡三老之乡官,有位无禄,是由政府在地方上选任,领导人民参政。三老始于战国时代,是由一些地方上年高德勋、经验丰富的长老中选出,以掌管地方之教化。为了辅佐三老教化之任务,在汉代又设置孝悌、力田及乡官。
乡之下设亭,亭有亭长。亭是介于乡与里中间的行政区划。有些学者认为亭并不是秦汉之乡村组织,而是一种军事性的设置。他们认为“十里一亭”之里,应解释为距离之单位,所以亭不能与乡、里相提并论。不过绝大多数的学者,都认为亭是一种乡村组织。亭有两种:一种是亭舍的亭,就是为军事运输所设之亭;另一种是地方区划的亭,谓之亭都,就是说乡分辖单位的亭。
秦之亭数,已不可考。西汉平均每乡有四个多亭,东汉有三个多。亭有亭长、亭佐、亭侯、求盗、亭父等亭吏。亭长负责禁盗贼、理辞讼。亭长之下有亭佐及亭侯助理亭长;再下有两小卒,一为亭父,负责开闭扫除;一为求盗,掌捉捕盗贼。但因为职卑位下,各地之称呼不同,有的地方称亭父为亭公或亭部,有的地方称求盗为弩父。
亭之下为里,有些学者以《后汉书》“百官志”为根据,认为一里百家,而一乡即为千家。事实上,《后汉书》“百官志”是根据西晋的制度而推论的,并不符合秦汉时代的实况。秦汉时代的乡村组织,还是以面积为划分的标准。
除了里之外,又有聚与落的乡村组织。聚是王莽时代设立学校时所划分之乡村组织;落之组织在文献上亦可见到。但这两种组织,都不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