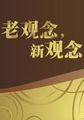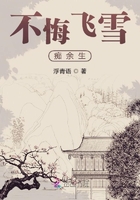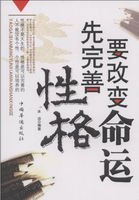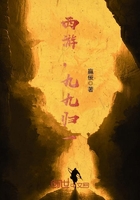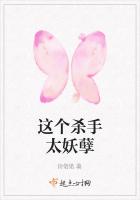“唐型家庭”不但人口比汉型多,成员关系也远较复杂,在唐代相当普遍,故名。它的来源可以追溯到魏晋南北朝。
《宋书》“周朗传”曰:
今士大夫以下,父母而兄弟异计,十家而七矣;庶人父子殊产,亦八家而五矣。
仕宦人家父母健在而兄弟同居共财者并不多,平民父子分异财产者也不少。《隋书》“地理志”云,四川“小人薄于情礼,父子率多异居。”江南“父子或异居。”这是不是说明魏晋南北朝的家庭结构和两汉没有太大的差异呢?
魏晋南北朝全国户口总平均数比东汉略微提高,数字虽然有限,但如果以家口人数分布与汉代总平均户口数相较,魏晋时期每户六七口者已相当普遍,8口的人家也不稀奇,显示家庭结构已经逐渐改变。
伦敦不列颠博物馆所藏西凉建初十二年(416年)敦煌郡敦煌县西岩乡高昌里户籍残卷,编号斯○一一三,著录10家户籍,只有8户完整,计34口,平均每户3.25口。单就数据而论,与汉代没有显著的差别,但每户人口数的分布,5~7口者占一半,尤其成年兄弟同居,却为西汉时期极罕见的。譬如裴保一家,兄弟同居,包括祖孙三代,构成“共祖家庭”,而裴保的身份不过是极普通的兵卒而已,并非士大夫。《颜氏家训》“止足篇”四:
常以为二十口家,奴婢盛多不可出二十人。
所谓20口之家,或不止限于士大夫而已。
到了盛唐,全国户口平均数大大地提高。若以府州为单位,每户平均7口已不足为奇,甚至也有高达8.35口的;于是每家口数之分布自然上扬,一般情形可能在5~10口之间,它的成员结构自然就与汉朝大异其趣了。
清人陆耀逾所纂《金石续编》卷五著录“周村十八家造像塔记”碑文一件,建于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年),位于怀州修武县。该碑刻录斥资建造佛塔的18家家庭成员,平均每家7.39口,家口分布从5~12不等,而以6口至8口占绝大多数,计15家;但碑文记载的人数并不完备,女口可能有所缺漏。关于成员结构,祖孙三代同居者12家,四代者4家,父子两代者只有两家而已。这些家庭,有的成员或官拜县令,或任职都尉,无官职而能斥资造塔者可能也多属富贵,代表地方中上阶层的人家,故家口平均数比全国总平均大,在州户口平均数中也偏于上限。
敦煌户籍卷最著名的“天宝六载敦煌郡敦煌县龙勒乡都在乡里户籍残卷”,分藏三处,在巴黎者编号伯二五九二、伯三三五四,在伦敦者斯三九○七,在中国者为罗振玉旧藏,主要资料是伯三三五四。这分残卷有完整人口记载者17户,159口,平均每户9.36口,与《旧唐书》“地理志”所载天宝时代沙州户口平均数3.81差别甚大,但和瓜州的10.45却很接近。有人怀疑这份残卷伪滥不实,不过户籍与授田的地籍并列,每户人口记录应该相当可靠。从残籍的个案来看,已婚兄弟及其子女同居共财者颇不乏例;兄弟亡故,伯叔与子侄依然同居共财者也大有人在。唐代法律高度地反映这种社会现象。
《唐律·户婚律》“子孙不得别籍”条曰:
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
原注:“别籍、异财不相须。”只要别立户籍或分割财产,皆构成三年徒刑的罪名。长孙无疏议曰:“曾、高在亦同。”那么上代犹在,子孙便不准别异。《唐律》同条又曰:
诸居父母丧……兄弟别籍异财者,徒一年。
斩衰丧期之内也是不准别异的。《唐律·户婚律》曰:
若祖父母、父母令别籍……者,徒二年,子孙不坐。强令分户,罪及父母。
“唐型家庭”的特点是尊长犹在,子孙多合籍、同居、共财,三代同堂是很自然的,于是共祖父的成员成为一家。否则,至少也有一个儿子的小家庭和父母同居,直系的祖孙三代(主干家庭)成为一家。《仪礼》“丧服传”所讲的家庭,经过秦汉四百多年后,才逐渐体现,而以盛唐为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