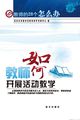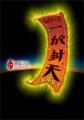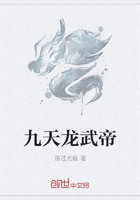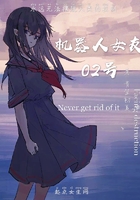20世纪70年代初期,湖北江陵凤凰山出土一批文景年间的简牍,其中10号墓的贷毂账详记家长之名、能田人数、全家口数等项目;资料齐全者24家,共计112口,平均每家4.67口。每家口数少则一二口,多则七八口但都是特例,最常见者为3~6口,不论家数或口数几乎都占全部家、口数的80%,充分说明当时每家3~6口者居绝大多数。然而,即使是6口之家,恐怕也容纳不下两个以上结过婚的兄弟,顶多包括上一代的父母与下一代的子女而已。
劳翰先生编辑考释的《居延汉简》有“戍卒家属在署癛名籍”的记录,可以窥探戍卒的家庭结构,计26简;另外有筹资簿一简、符传二简,也记录家庭成员,共计29简。一简一家,共102人,平均每家3.52口,口数分布主要集中于2~4口,比凤凰山稍微偏低,也许是戍卒年龄尚在青壮年之故。这29家中兄弟姊妹同居者极少,即使有之,女性同产出嫁以前尚与兄长同居,如果是男性,稍能自食其力就独立门户。这也说明汉型家庭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小家庭。
西汉家庭兄弟分异的情形至东汉并未有太大的改变。东汉全国的户口平均虽然略微提高,但增加得很有限。宋朝洪适编撰的《隶释》著录“金广延母徐氏纪产碑”,记父子兄弟分家的。同书也有“舜子巷义井碑”,碑阴锏刻斥资人名,很多称为“分子”。洪适考释曰:
义井碑阴称五大夫者三十一人,称分子者六十人,摩灭者数人……景北海碑:“鹗枭不鸣,分子还养。”盖用“家富子壮则出分”之语,谓恶逆之鸟钳喙无声,外灶之息归奉三牲也。耿勋碑:“修治狭道,分子效力。一谓正丁已备差徭,分子亦来助役。此碑分子似指土豪出分之子”。
洪适的考释当无疑义。二碑一建于灵帝光和元年(178年),一建于光和三年(180年),已经是东汉晚期的现象了。
不过东汉以来风气渐变,即使兄弟不同居,父子异灶“生分”的现象可能逐渐减少。也就是说,至少有一个儿子与年老的父母同居共灶。所以到曹魏时,乃
除异子之科,使父子无异财。(《曾书》“刑法志”)
废除嬴秦以来的法令。家庭结构逐渐从“核心家庭”转为“主干家庭”,但还不是“共祖家庭”。后半截的转变发生在两魏到隋唐这300多年之间。“唐型家庭”于焉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