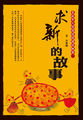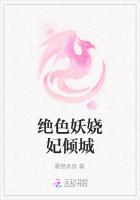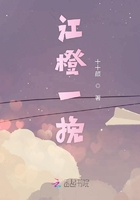公元8世纪中叶安史之乱以后,人口流离,所谓“唐型家庭”便很难维持了。尤其将逃户的负担硬摊给见在户,恶性循环,流亡之风更炽。《唐会要》卷八五“逃户”条曰:
今色役殷繁,不减旧数,既无正身可送,又遣邻保只承,转加流亡,日益难弊。
正足以说明人口流离的严重现象,关系较疏的族人要长相厮守也就更困难了。两宋户籍资料的数据和隋唐便截然不同。
两宋有80多次户口普查的记录,全国平均户口数最高没有超过2.57口,最低仅1.42口。这种数据当然不可信,学者乃提出丁口说、漏口说和诡户说来解释。丁口说者认为户籍调查的口数只登录丁数,即表示成年男子数,而非全家人口数。漏口是少报人口,诡户是虚报分户,皆求减少每户口数,以降低户等,减轻负担。我们考察宋代的户数,多有1000万以上者,最高时期超过2000万户,远比唐明两代为多。宋徽宗时的户数比唐玄宗时高出2~3倍,几乎是明神宗时的2倍,可见诡户是相当严重的。然而地方性的差异也极大,《宋史》“地理志”所载徽宗崇宁年间各州户口资料,有的平均每户高达七八口,有的只有1口而已。这么悬殊的差距至少反映各地的家庭结构颇不一致,平均每户8口之地大概犹存“唐型家庭”之风。
不过,两宋普遍的家庭结构既非核心小家庭,也不可能是“唐型家庭”。南宋朝廷安置流民,办理赈灾的户口资料大概比较能够反映当时的普遍现象。根据散存的12条史料,每户平均口数从3.72~8.39不等,5口以上居3/4,6口左右占一半,总平均每户6.06口。可见,南宋又回到东汉的水平,已婚兄弟同居共财的家庭减少,但置年老父母于不顾的核心小家庭也不多。
《宋刑统》对于家庭结构的规定完全抄袭《唐律》,实际上形同具文,与现实情况不能配合;《元典章》就比《宋刑统》切实多了。《元典章》卷十九“家财”“同宗过继男与庶生子均分家财”条曰:
唐桢(证之误)自行主意,与亲族唐刚大等议令二子均分家产,赴官执法,连判所立分书,于内明白,将实有田土品搭均分。
既然“赴官执法”,大概别是立户籍了。《元典章》卷十七“分析”“父母在许令支析”条说得更明白:
随处诸色人家,往往父母在堂,子孙分另别籍异财……唐律:祖父母父母不得令子孙别籍。又旧例:女真人其祖父母、父母在,支析,及令子孙别籍者,听。又汉人不得令子孙别籍,其支析财产者,听……若依旧例,卒难改革,以此参详,隋代沿革不同,拟合酌古准今,自梭,祖父母、父母许令支析别籍者,听;违者,治罪。
元代涉及家庭结构的法令摒弃不合时宜的唐律,而以女真习俗为准则,故祖父母、父母虽在,子孙不但可以分居、异灶,而且可以别籍。
明律虽不完全承袭元法,但对唐宋法律有所修正。因为宋元以来父子兄弟分异,逐渐习以为常,不得不承认这项现实。《明律集解附例》卷四“别籍异财”条曰:
凡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一百。(原注:须祖父母、父母亲告乃坐。)若父母丧而兄弟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八十。(原注:须期亲以上尊长亲告乃坐。)
这两条刑罚比唐律之徒三年、徒一年者大为减轻,而且还有附带条件,前者须祖父母、父母亲自告诉乃论,后者须祖父母、伯叔父母和在室姑母等期亲亲自告诉才受理。但分家已成为风气,近亲尊长提出控诉的情形恐怕很少。清律亦多沿袭明律,《大清律例增修统纂集成》卷八“别籍异财”条条例曰:
祖父母、父母在者,子孙不许分财异居;其父母许令分析者,听。
这些律令和条例大抵是因应实际情况而作的调适。
明代官方的户口统计,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黄册记载平均每户5.68口。《大清一统志》记载嘉庆十七年(1812年)的户口普查,14省,每户平均口数5.33,与明代的数据相当接近和民国初年学者所作的调查也没有太大的差别。金陵大学卜凯(JohnLossongBuck)教授和李景汉在河北定县的研究,显示一般农村家庭3~6口者占最大多数,说明近世以来中国的家庭结构系以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为主,已婚兄弟同居的共祖家庭大约只有一成,这就是本文所谓的“汉型家庭”与“唐型家庭”的折中。学界一度流行中国是大家庭的说法,并不正确。
在中国社会里,存在着一些世家大族;他们为乡里所熟知、所尊重,他们的地位,也为世人所共认、所肯定。当然,世家大族的形成背景、发展过程以及家族结构互不相同,而其环境和地位、扮演的角色,也有着绝大的差异。本文以历史发展为线索,作一概括性的剖析与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