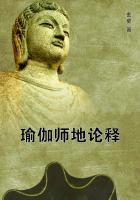能够一脚踏进吴元厚画室,是纪学览没有想到的一件事儿,也是他后来逢人经常挂在嘴巴上炫耀吹牛皮的一件事儿。
听他的说法,朱红过去到吴府拜访是“登堂”,而他则是“入室”了。
这个有区别:前者是面子;后者是面子、里子全有了。那个时候在市面上做字画生意的商人,就说哪个字号门面的生意做得再大,老板做得再牛,也没人踏进过吴元厚画室。那些到吴元厚家里请教的,求字画的,最多走到吴家客厅。能够上楼到吴元厚画室里看一眼,坐一会儿,那是社会上很有身份的人。光有身份还不行,还要有交情,有感情。这一点纪学览在道上混久了听说过;他还听道上的老前辈说过,吴家收藏可观,历代有名头的字画数量最多,其次是明清两朝的家具,接着便是官窑瓷器。吴元厚的父亲吴绍庭用的画桌、椅子、书架是明朝的东西。吴元厚传他老头子代,手里有钱也欢喜寻觅前朝老东西。他用的笔洗就是雍正年代官窑里的东西,稀罕得很。纪学览做这一行见过的老货不算少了,进了吴元厚画室,还是大开眼界。眼瞅着墙上挂的“元四家”倪云林,“明四家”唐寅的字画,桌上的斗彩笔洗,纪学览眼红眼热得很,心里想以后有机会,便教吴公子把这个家输个干净两茫茫!
吴天玉先前进了屋子,直接去吴天泽书房。
吴天玉敲门,吴天泽不开门,便接着敲门,一边说道:“哥,外面有个姓纪的人来找你!”里边没有回应。吴天玉再敲门,又说了一遍,这时候听见里边“啪啦”一声什么东西掉在地上。
一会儿只见吴天泽把门打开一条缝,露出一半脸,神情慌里慌张地问了那个人的摸样,“哈”一声道:“我忙得很,不见!”随即把门关上。吴天玉一怔,也不想多问,转身就走。
纪学览一脚踏进吴元厚画室的时候,吴天泽正闷在自己书房里发呆。吴天玉一走,他神情恍惚,脸色煞白瘫坐在椅子上,眼珠子翻上去一动也不动,嘴巴朝天翕动,好像鱼儿浮在水面上呼吸氧气……就这样怔了一会儿,突然“哈”一声从椅子上跳起来蹿到书房门口,抬起脚猛一脚踹门;一拍脑袋想起来,这个门是往里边开的——急着把门打开,跑了出去。
吴天泽在外头赌钱,欠了一屁股债,数目忒大了。债主找上门来,白纸黑字放在吴元厚画桌上。吴元厚一下子气得折断毛笔,两只手疯了似的把桌上刚画到一半的山水画抓起来撕掉了。大概是气昏了头,花了眼睛,吴元厚接下来一把抓起桌上的笔洗,举起来就要往地上掼,——幸亏阿仲刚才看老爷撕画的当口靠近了过去想阻拦,——眼瞅着老爷要摔那个笔洗,一刹那间双手扑上去,救了老爷手上的那个官窑瓷器。这时候纪学览站在一边惊呆了,张开两只手,看着吴元厚头上、身上滴下来的水,倒吸一口冷气,吁出来说道:“喔,这个东西传世的宝贝哦,要是摔破了作孽!”纪学览这会儿颇有历史感,心里想这个东西,是个东西,往后半个世纪以后便是特吗的天价!
阿仲赶紧把那笔洗放到靠墙书架空档里头,回头找了一条毛巾给老爷擦脸上头上的水。吴元厚手一摆挡开阿仲递上来的毛巾,自个儿撕了半张宣纸擦了手上的水。看吴元厚一屁股坐下来,牙齿咬紧了不说话,纪学览清了一下嗓子,开口说道:“……我说,要是吴先生家里一时拿不出那么多现大洋,家里的字画也是可以拿来抵的。——要不,刚才吴先生要摔的那个笔洗也行啊,现在给我,不就结了?”
吴元厚头转过来,眼睛定定地看着纪学览——看了一会儿,身子仰了仰,干咳一声,闷闷地吐出两个字:“送客。”阿仲一听,立马上去将手一让,眼睛一斜看着纪学览,下巴一抬,说:“走吧。”纪学览嘴巴一呲,“也”一声微笑,掸了一下衣服袖口,脑袋一偏看着阿仲,说道:“哎,这钱,是不是不给了?哦,是不想给了。——恐怕,没这个道理吧。”纪学览说着,转身到桌边上拿起那张字据,眼睛一瞟,面对着吴元厚,手指头指着字据,似笑非笑说道:“自古借债还债,天经地义。吴先生,您不能坐在家里头凭着身份压我,不还钱吧?”纪学览顿了一下,一想接着说道:“哦,不想还,也可以。跟我到城里走一趟,寻个讲道理的地方……如果说,那个讲道理的地方说,这个钱不还。那我就趴下,听那个讲道理的人一句话,我立马把牙齿打掉往肚皮里咽,不说一句屁话。吴先生是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物,名气大得很,受人尊敬。您不至于跟鄙人来一个我不理你吧?”
吴元厚瞟了纪学览一眼,一手撑在画桌上,揉了一会儿眼睛,额头,深深吸了一口气,吐出一个字:“还。”然后转脸对阿仲说:“送客。”阿仲头一点,面孔一拉,开始对这位客人有点不客气了,手一挥,说:“走吧!”话音一落,就推纪学览往外面走。
“不要推,”纪学览一个转身回头道,“我自个儿会走——马上走。不过走之前,也要把话说清楚了,要说个时间,什么时候还?”阿仲冷笑一声道:“你说呢?”纪学览眼睛一斜,说:“你是用人,我不跟你说。我跟吴先生说,——吴先生您这会儿不想说话也好,我来说,——我纪某人好说话,不为难人。我来说个时间,吴先生要是同意,我马上走。要是有难度,吴先生说一句话,我也是好商量的。请吴先生说个时间。吴先生不说?我来说——”
“说。”
“也,既然吴先生要我说,我就说,——再放宽两天;今天算一天。还有明天一天。到了后天上午,还钱。我过来拿,怎么样?”
吴元厚一直听得很专注,脸色愈来愈阴沉,铁青的脸绷得紧紧的,好像挂了一层神圣不可侵犯的严霜。纪学览说罢低头若无其事地活动一下手指,间或抬头瞟一眼画室里的摆设,嘴巴翕动,也不言语,等待吴元厚回音。
吴元厚轻蔑地吊了一下嘴角,眼睛透出犀利的光,扫了纪学览一眼,一转脸舔了舔嘴唇,随即咬紧牙根“呼——呼——呼——”胸口一起一伏喘气,像拉风箱似的。一会儿只见他闭上眼睛,长长地吁出一口气,点头“嗯”了一声,手背朝纪学览一挥:“走吧。”
“好,”纪学览龇牙咧嘴一笑,瞟了阿仲一眼,说,“吴先生点头了。我一句废话不说了。走,再会。”说罢,转身走出吴元厚画室——回头一看阿仲跟在屁股后面,纪学览突然停住脚步,阴着脸把阿仲从头看到脚,“也”一声说:“府上的人叫你什么来着?哦,仲叔。——哎,仲叔留步,不劳你仲叔送了。我知道怎么下楼梯,我也晓得怎么走出去。”
送走纪学览,阿仲转身回到楼上。吴元厚双手按在画桌上,猛一抬头见阿仲进来,揉了一下眼睛,说:“阿仲,去把天泽喊到楼上来。”
阿仲去了一会儿,回上来说:“少爷不在家里。明香说她看见少爷刚才跑出去了。”吴元厚一听,脸色惨白,耷下头坐在椅子上沉默不语。
阿仲悄悄地退出去;走到楼梯口,见太太上楼——吴太太问道:“阿仲,是不是有人来过?什么事儿?”阿仲急着往楼下走,示意跟太太到楼下去说。
到了客厅里,阿仲把刚才发生的事情跟吴太太说了个大概。吴太太听了,眼前一黑,昏倒在地上。
这时候吴天泽一个人坐在马车上直奔城里。
马车奔到半路上,吴天泽才想起来,自己口袋里空空如也,要一分钱玩玩也没有——想回头——是不可能的。
真的一分钱没有,心里也不急了。他想了一会儿打定主意,到了城里,叫车夫直接把他送到庚子家门口。
庚子原先读书的时候住在惟亭;自从他父亲生肺病去世以后,他跟母亲搬回到苏州城里原来的老房子住。
车到了庚子家门口,吴天泽下来,拍拍屁股对车夫说:“喂,你等着,我进去拿点东西马上就出来——还坐你的车;今天下午把你的车包了,别走开。”说着,悠然地掸了一下衣服下摆,抬头瞟了一眼门牌,便转身往门里边去。那个车夫起先听了一怔,随即一口答应;这会儿眼瞅着这个公子哥儿模样的人一头走进这么一个破旧的老屋门档子,他起了一点疑心。但是一想,不要紧,这排老房子背后是一条河,人进去了后面是跑不了的。
一问庚子他娘,庚子在家,吴天泽“哈”一声走进屋里。
庚子在里屋听到吴天泽声音,吃了一惊;见他进来,庚子忙站起来嬉皮笑脸道:“喔唷,吴天泽,你今天怎么来了?教我想死你了。”吴天泽一哂,上去拍了一下庚子肩膀,然后一屁股坐下来,说道:“我现在肚皮饿死了。先给我弄点吃的过来——”“好,”庚子立马回道,“吴天泽,我就是欢喜像你这样的朋友。你就是你,角别得很,跟其他人就是不一样。比如说,你到我家里来,不跟我说一句废话,也不跟我来虚了虚的。你现在肚皮饿了要吃饭是吧?那就吃!”
“蛮好,”吴天泽咽了一口口水,一笑,一边抚摸肚皮,说,“快,家里有什么吃的?先给我垫垫肚皮,再跟你说话——”
“哎,吴天泽,”庚子似乎有点意外,头一歪,眼瞅着吴天泽,说,“在我家里吃?”
“是。”
“哎呀,”庚子拍了一下大腿道,“你——你怎么不早点来呢。”
“怎么了?”
“唏,”庚子一副似笑非笑的面孔,“中饭早就吃过了。现在这个时辰我家里有什么吃的?你看一下时间,这会儿还有什么吃的?没有了,全吃光了。要么晚上烧饭吃;要么你现在跑到外头去吃……外头小店里,有什么吃什么,——你自己看。”说罢,若无其事立起来倒了一杯白开水,往吴天泽面前一放。吴天泽和庚子对视了一眼,推开杯子,瞟了门外一眼,嘴巴一努说:“庚子你出去,把外面那个车夫的钱给了,就算你请我的——”
“啊?”庚子嘴巴一张,“哇,你来的车钱还要我来给啊?”看吴天泽突然变了脸色,庚子立马说:“好好好,我来就我来……我说过么,我们同窗还是同窗。我们朋友还是朋友。以后我们还是同窗,以后我们还是朋友——这不,我是很够朋友的……你吴天泽到时候就是用得着我,是吧?嘿嘿……”
“嘿你个屁,”吴天泽立起来走到庚子面前,手指头指着庚子鼻子,皱紧眉头,眼睛凶狠说道,“我操你个庚子,跟我说了一通废话!你赶快给我出去,给人家车夫钱。要不,我揍你!去——!”庚子一怔,随即哈腰转身出去。
在正门外面等候的那个车夫,等得急了,便寻进去;回头又不放心停在外头的车,他到里头张了张就跑了出来——见庚子出来,上前问道:“哎,刚才进去的那个少爷是住在这里头吧?他怎么不出来付车钱?还有我这个车他现在还要不要接着用啊?谢谢你帮我进去问一下那个少爷——”
“少爷?哼,”庚子眼睛一斜看了车夫一眼,向前跨了一步,说道,“谁是少爷?你是说刚才进去的那个小子?呸,什么狗屁少爷!是讨饭的,叫化子。我才是少爷。车钱是多少?给你——不用找钱——走吧!”
看庚子嗒然若丧回进来,吴天泽干笑一声,嘴巴一撇说:“钱给了?”
“给了。”庚子身子向前一倾,伸出两个手指头,换了一副嬉皮笑脸,“怎么样,爽气吧,够意思吧,够朋友吧。”吴天泽面无表情,将庚子从头看到脚,突然“哈”一声道:“还行。”
“不是还行——是行得很。”
“行,可以。”
“不是可以——而是可以得很。”
“好了,庚子。”吴天泽立起身来,上前一把将庚子摁到凳子上坐,凑近他脸,说道,“你行得很,也可以得很。我现在可以跟你说话了。我今天来,没别的事儿,就一个事儿要你帮个忙,行不行?”
“什么破事儿?”
“说出来,有点不好意思。”
“吴天泽,见外了不是?我庚子,你晓得,爽气得很。你的事儿就是我庚子的事儿——你吴天泽只要放一句话,我风里雨里跟着你,帮你忙,哪怕我跟你艰难跋涉在沙漠里,我马上要饿死了渴死了,那最后半个馒头最后一口水,我也让给你吴天泽吃。这就是帮你帮到根上,才是够他妈的意思,你说是不是?”
“好,庚子,我今天跟你开口……”
庚子一听吴天泽要借钱,马上立起身来,摇头摆手说:“哎,吴天泽,问我借钱,我没有。除了这个事儿,其他什么事情都行,都可以——比如说,你要叫我帮个忙,去把那个唐小姐喊出来,我立马去,不说一句废话。再有,比如说你跟外面哪个人有仇,叫我一声,我立马帮你一道去教训他——再比如说——”
“操你个庚子,”吴天泽面孔一拉,抬手拉起来一个头皮掴上去,“你不借就不借,跟我虚了虚的说什么屁话。我不问你借了。你别虚。过来,给我坐下!你说了那么多废话,没用。我现在就叫你帮我一个忙,把韩进给我约出来,我跟他说,马上!”
“好,”庚子眼睛一闪道,“我来帮你约。哎,要不要把我表哥银子也约出来玩一会儿?要不三缺一,不好玩。”
“去你的,”吴天泽回道,“我现在坐在你家里等你——你去,帮我把韩进约出来就没你的事了。”说罢,吴天泽将一杯白开水一口气喝下去。
“苦啊,”庚子尴尬一笑,立起身来活络了一下头颈,头一歪道,“哎呀,吴天泽,你这不是难死我了么,我现在到哪里去寻他?他住在哪里我不晓得,你叫我怎么去喊?再说了,大白天他怎么会待在家里?——你问我怎么待在家里;我是我,我又不是韩进。人家韩进二少爷有钱得很。我口袋瘪塌塌的,只好待在家里睡觉,我哪里都不想去。哎,吴天泽,你还是问韩进借……你问银子借,借不到。我那个表哥小气得很。那天我想买一双皮鞋,钱不够,我问他借点钱凑凑给我买,他就是捂住口袋一分钱都不肯借给我,怕我不还他似的。还表哥呢,表什么表?一代表,三代了。我看他是人家的一块手表。我是看穿他的。我这个表哥要你相信,狗眼乌子看人头,石头往山里背……人家韩进有钱,他就跟着拍韩进马屁,一天到晚请韩进又是吃又是玩的……暗地里还帮他找了一个小女子……是我看见的,不是瞎讲。我告诉你吴天泽,你今天就问韩进借,不怕他不借。他要是不肯借的话,你就提醒他一下,说你晓得他在外面做的什么好事儿,他心里就虚了。只要他一虚,你就乘虚而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