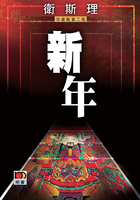铃姐到云南边境去这件事不是小事,我即刻写几句简短的信寄给鹤哥。
鹤哥和银珍嫂安慰我,不必为铃姐的事忧虑,说铃姐应当勇敢地去爱于鲁。当军人太苦了,应该得到人的爱戴。这点他们体会最深。
鹤哥虽然没有告诉我他遇到的困难,但我读那纪实文学时,一切都清清楚楚了。
天伢突然发烧,小脸蛋烧得通红,浑身像火炭一样。已是凌晨一点半,刘鹤和银珍还没躺下。孩子一直不退烧,咋办?他们盘腿坐在床上守候着孩子。银珍不时地给孩子擦汗。天伢刚醒醒又沉沉地睡去,小嘴巴微微翕动着,叽叽呱呱说梦话。
只有银珍才能听清孩子在说些什么。
“孩子说要小青蛙,要书包……”银珍说。
刘鹤说:“哪有小青蛙呢?你不是缝了个书包吗?”
“等他好了,我就给他背上。”银珍小声说。
银珍抱起孩子,不停地摇晃:“天伢乖乖睡,乖乖睡……”
孩子在蹬腿,双手乱摸,喃喃说:“花,这朵花好香,好红……”
刘鹤给孩子喂一口温开水。孩子啧啧地吮吸着。
“多点儿,孩子渴得厉害。”银珍说。
刘鹤端起杯用嘴唇去试了试,然后放近天伢的嘴巴。孩子拼命地吮吸杯里的水,长长地舒着气。这个时候,刘鹤猛地感到颤栗,一种不可名状的悲怆感袭击心头。他看到孩子消瘦多了,蜡黄的脸上有一种渴求而难以得到的苦楚。儿童的天真烂漫蒙上一层阴影。他咬着嘴唇,又去倒开水。
银珍猝然觉得丈夫神态不对,忧伤的眼睛跟踪着他倒开水的动作。她看到他的手有些颤抖,滚烫的开水泼在地上,发出“啪”的声响。她低下头,轻轻地摇着怀里的孩子。
“妈妈……”孩子喊道。
“妈在这儿,妈抱着你,孩子。”银珍用手抚摸孩子额上的汗渍,小声说。
“爸爸,爸爸……”孩子又喊。
“爸爸不就在这里吗?傻孩子。”银珍说着轻轻地摇着孩子。孩子还在喃喃地说些什么,迷迷糊糊地睡去。
刘鹤把开水凉在桌面上,对银珍说:“我出去一下就回来。”说着,开了红柳条门。
夜色灰蒙,四野岑寂。刘鹤敲了一下连部隔壁那扇柳条门。卫生员沈汉民立即开门问道:“连长,有事?谁病了?”
听说天伢发高烧,沈汉民背起药箱就跟连长走。检查结果是重感冒。打了一支针,服了些感冒药后沈汉民说了些注意事项便走了。
刘鹤的心稍稍安定一下,但脑子感到很乱。白天在如火的太阳下训练流点汗倒没什么,到夜晚,战士要求退伍所采用的“硬磨”战术,会活活把人拖死的。在这里,政治思想工作该怎样做,确实没有头绪。上头呢,又没有具体指示。还是迁徙时说的几条干巴巴的原则:服从命令听指挥;这是战略战术的需要;稳定军心,坚守、训练。连里战士的思想动态已报上去半个月了,未见复函。前不久,听说团李参谋长和容副营长骑骆驼来,只到半路,就被突然刮起的风沙挡住了去路。骆驼在迷蒙中转了一天一夜,又回到了团部。这狼烟滩到底是个什么地方似乎还是个谜。他想去找李雁声聊一聊,看着连队沉睡的样子,又不忍心去把战友叫醒。
他站在门口,敞开衣襟,任凭风沙劈打胸膛。他觉得这样会清醒些,舒服些。
他痴痴地望着眼前的一切——一个奇特的军营,一个古老神秘的重新跃动着生命的灰褐色的世界。一百多人靠军人的纪律和尊严蜷缩在这个没人问津的世界。这个世界同南方边境比起来,是那么萧条、荒凉、冷漠。他记得那年在云南扣林山阵地时的情景。那时蹲在猫耳洞,任山上的水从洞顶滴落,打湿军装,也一动不动。说冲就冲,说杀就杀,快刀砍乱麻,干脆利落。那天夜晚也有风,是湿漉漉的风,墨绿丛中发出风雨和绿叶的喧响。他带一排战士摸上被敌人强占的406号高地,全歼了敌人两个排。那情景还历历在目。可现在呢,远离战场,在渺无人迹的荒滩大漠,却有永远也处理不完的事情在缠绕心头。这里的确一刻也不能安宁。前天,接到彭洛母亲去世的消息,已派二排长去彭洛的故乡,半个月了,音讯全无。昨天,关雨的父亲又拍来急电,催他速回。豹子头近日好像好了些。还有,贤珍就要到了。李雁声、阿大的事儿……天伢和他妈被困在这儿,总不是个办法呀!最令人心寒的风沙不断,说不定来一场风暴,一百多人的生命便很危险。
刘鹤痴痴地望着朦朦胧胧的沙漠,忽听屋里天伢在说话。他回到房间。银珍抱着天伢倚在墙上睡着了。天伢的嘴巴还在翕动着说梦话。他从妻子的怀里抱过天伢,让妻子和衣躺下。他吹灭了蜡烛,在室内来回走动,双手学着银珍平素的样子,在轻轻地摇。他不会唱摇篮曲,也不会讲一句安定孩子的话。只是来回走动,轻轻地摇。
妻子太累了,鼾声很沉,还不时地翻身,不时的“呵呵”地哄着孩子。他俯下身子,隐隐约约见妻子的脸变得蜡黄,瘦削多了。这些日子,她在狼烟滩闲不着,不是帮厨,便是替战士洗衣服,洗被子,缝缝补补。看不到猪拱槽,听不到三鸟叫声,她的心很烦躁、很乱。她想干活,想同女性讲孩子,拉家常,但没有机会,一次机会都没有。孩子嘈着要同伴,她何尝不是如此?她惟一的同伴就是天伢,同他玩沙玩腻了,捡石子也捡腻了,一天到晚被毒花花的太阳烤着,被滚烫烫的风和沙子抽打着。她变黄变黑了,头发也由墨黑到焦黄。
刘鹤用手拨开遮在她脸上的一绺头发,眼睛一动也不动地望着她,心里一阵内疚。她跟着军人在这里受苦了。可她从没怨言,没事似的。
他依然抱着天伢来回走动。他不会唱摇篮曲,只会“哼呀哼呀”地摇晃着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