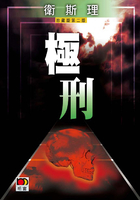暖暖的。淡淡的香水味。
脚步轻轻,一阵温馨的风。
喷香——是本地鸡炖香菇,一阵热腾腾的轻烟拂着我的脸。我懒得睁眼。我仿佛在作梦。
暖暖和和的,淡淡的好像非常熟悉的香水味。我忽然顿悟到什么。心房像流进蜜糖似的。
我不由自主地睁开眼睛。天!是雁雁。她坐在我身边用她的手帕擦拭我前额和颈部的汗珠。她?是她吗?我眨了眨眼睛,以为是梦,用手拧了拧我的大腿,钻心的痛。不是梦。眼前坐着的是雁雁。是失踪多日的雁雁。是她,就是她。
“雁雁!”我立即要爬起来。声音颤抖着。
她用力按住我的胸膛,说:“云飞哥,你不能起来,你受酒伤了,好重好重。”她说着用手擦了擦眼角,两颗热泪滴在我的脸颊上。她的眼有两束火,明亮而温热。我这才看清她的容颜:脸蛋越显白嫩红润,眼睛充满温情。她穿一套得体的警服,帽子上有一只徽章,全身上下显得异常威严。那年,唉,那年给我上手铐的也是一位穿警服的……今天,雁雁也穿警服,她坐在我身旁,一阵阵温热,一阵沁进我肺腑的淡淡的馨香。她怎么竟一下子出现在我的身边?雁雁,难道你是仙姑吗?你真是个谜。你给我的是天空远去的云,是令我捉摸不定的幻梦。你真是谜中之谜。
“雁雁……你……”我撑着起来,这才见到一床崭新的红绸被和绣花的木棉花枕。我不明白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我说话的时候,门响了。是阿花和李冲堂。阿花提一袋大苹果,冲堂捧一瓶罐装奶粉。
“他好些了吧,雁妹妹?”阿花问道,“你觉得哪里不舒服?”她转向我关切地说。
“谁知你独斟独饮,差不多干完一瓶白兰地?”冲堂说,“没有酒量又充大头鬼!”
“昨晚若不是他俩,我看你还躺在门槛上。”雁雁责备说,“我离开一时都不行,失魂似的。”
责备越重,听起来越舒服。从他们的对话中,我知道昨晚自己出的洋相。快凌晨一点时,我跌跌撞撞摔倒在店门槛上。阿花他俩在斜对面同老婆子商议租房子和档口的事,一出门就见到我如此这般。是李冲堂撬开我的门的(我的钥匙不知扔到哪里去了);是阿花去找雁雁的;是雁雁搬她的红绸被和木棉花枕来的。
昨晚的事我记起来了。唉,那死田螺,那该死的白兰地。还有……人家是好人……我怎么啦?
阿花和雁雁在嘀咕什么,我听不清。李冲堂说了声“孔兄多保重”就出去了。阿花也跟着往外跑。
“雁雁,”我心很难过,停了一会儿接着说:“你悄悄地干了这行,你真的离开我了。为什么说走就走?为什么不愿告诉我,你当了民警?你不知我多想你……”
“云飞哥,我对不起你。我是一气之下走的……后来,我想你,偷偷地想……”雁雁低下头说。
“气什么呀!我至今不明白你为什么说走就走……”我站起来松了松筋骨,能同雁雁讲话,我轻松多了。
停了停,雁雁说:“那时的官下街,个体能活下去吗?再说你硬要同雪月合办鞋厂,像一家人似的,我受不了。”
我沉默下来。外头热闹非凡。早市过去,官下街的游人像潮水似的涌来涌去。鞋和服装的生意正“爆棚”,可惜我的“归雁鞋店”还不能开档。雁雁在拾掇散乱的皮鞋,像往日一样,经她的手,一切都井然有序。然而,我的心依然忐忑不安,像失落了什么似的。雁雁那身警服,使我失望。她忽然变得很陌生,离我很远很远,我无法同她走在一起了。我目不转睛地望着她。
我的脸色一定很难看,如果她转身望我一眼,定会吃惊。可她不,还在有条不紊地拾叠皮鞋,弄脏的,她小心地擦干净。她做这些的时候和往常一样轻松、干脆利落。
“不要整理了,这个店我要封了。”我说。
“封你的头,今天你怎么说晦气话?”她瞪我一眼。这眼神我很熟悉,只是她穿警服,我又觉得异常陌生。
“你走吧,”我说,“我一切正常。你当你的民警去吧,我这低人一等的个体户……”
“我向你三叩头行不行,皇帝。”她显然是对我的懊丧不满,“我说过,检讨过,我一气之下离开你是我的不对,眼下……”
我不说什么了,再说她会受不了的。她会哭的。
她叠好皮鞋之后,拆去了窗板,立即展现出往日档口的容貌:男装皮鞋和女装皮鞋各排一侧,新款式皮革凉鞋放在中间。她站柜台,穿一身警服卖鞋,确是奇谈。围观者多,买鞋者少。她站到晌午,只卖去一双皮凉鞋。她心里很难过,把我叫到柜台旁,安慰我说:“云飞哥,你要顶住。风花和李冲堂的鞋店立即开业,小心他们会挤垮你。我回去同父亲和我的领导说说,我停薪留职来帮你——不,是一齐开店,和过去一样。我和你在一起。”
“真的?”我惊喜地问。
“我不骗你,云飞哥。你一定要拿出男子汉的气魄来,一定。知道吗?”
OK!雾散了。雨过了。天晴了。
我的好雁雁飞回来了。
我真想紧紧搂她,抱她,热热烈烈地吻她。可是我不敢,她穿一身警服。她是威严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她见我高兴地盯着她,便低下头,笑了。
“云飞哥,我回来好办,你得依我三条:一不喝酒,二不发火,三不消沉。也就是文雅点、冷静点、刚强点。依不依?”雁雁约法三章。
“我不依你是龟孙子!”我说。
“粗俗!”她拧一拧我的脸皮。
痛得舒服。我一蹦老高。差点没撞断门楣。官下街像一条彩色的巨龙。最新款的时装都展出来了。六百多档口,五颜六色。来自全国二十多个省市的个体户和游客缓缓地流来,又缓缓地流去。越看我越觉得顺眼。我孔云飞因祸得福,吉人自有天相,到走运的时候了。
我想,雁雁,你真的是仙姑吗?
下午,雁雁回单位去。她那身警服很得体大方,真有点神圣不可侵犯。
这一夜,我睡得好香、好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