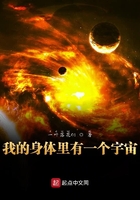阿花已经两天没有露面。
我不敢到跛脚女人那里去了。因为没有钱,去了不买酥皮,她瞪眼怎么办?在葵葵小学门口,我足足等了两天,不见阿花的影子。她为什么也不来上学?她是不是生了病?也许是跛脚女人知道她来为我洗澡的事打断了她的脚骨?我就知道跛脚女人冷冷的目光像贼眼,她不是好人。她若是打断了阿花的脚骨,我就要报仇。她可能是因为太坏,才被什么人把脚打跛的。
我胡思乱想了很久,都无法得出一个正确的答案。这世界本来就没有答案。爸爸被撵出广州是什么原因?没有答案。妈妈为啥跳珠江?没有答案。铃姐跟明婶到深圳那边去,到底怎么样了?没有答案。我一个人守红砖楼,往后到哪里去?也没有答案。我想,一切都没有答案,也不需要完整的答案。譬如隔壁那栋红砖楼,昨夜发生了什么事儿,我不知道。清早起来,见人把一具死尸抬了出去。门口挤拥着。有一排造反派手持枪支守着。我挤在人群里看。听说是一个什么大干部被斗了三天三夜,放回来后服毒药自杀了。“打倒畏罪自杀的走资派!”一条新标语贴在那栋红砖楼的墙上。奇怪,死了不已经倒了吗?是倒了,我敢担保,我亲眼见到那死人直挺挺的被抬了出去,当然是倒着的。倒了,还打倒,倒到哪里去?对了,倒到地下去,倒到十八层地狱去,倒了再倒吗?有道理。
那栋红砖楼的家人一连哭了四天四夜,我数得着的。我四天四夜没有睡好。作了一场美梦。阿花终于来看我了,我们又洗澡,这回是我先脱她的裤子。其实在作梦之前两天,我去看了阿花。她正发烧,躺在家里。我不知怎样终于知道她住在什么地方。离跛脚女人的档口不远处,有一栋旧的二层楼,她住一楼靠东边的小房里。我是经过一整天侦察发现的。我趴在窗口往里望时,见到阿花躺在那儿。我当时高兴极了,喊道:“阿花。是我,阿飞。”她睁开眼望了很久才说:“你怎么来了?你知道我住在这儿?”“知道。我找了一天,在学校守了两天。”我说。
她挣扎着起来,开门,叫我快进去。我说,不,你妈会回来的。她说妈在档口不回来,回来也不怕。
我一闪身进了她的房。房很小,床也不大。一张小课桌上摆着课本、笔什么的。床上有一本小人书,壁上还挂着一把木剑,一把大刀,我一摸,是铁的。
我进去时,她坐起来说:“那天洗澡,我着凉了,躺了三天了。”
我一摸她的头,还发烧。“不吃药吗?”我问。“吃是吃了,老不退热。”她说。我见她嘴唇很干,就给她倒了一杯开水。她咕咕地饮了。“厨房在哪?你还没吃什么吗?”我望着她难受的样子,心里也很难受。她摇了摇头后,手指着西边说:“厨房可能有妈煮的粥,你去吃吧!”
我去厨房给她打了一碗粥,是一种香喷喷的粥——她妈真能干,煮出这么香的粥。有妈妈真好。
我给她喂粥,一匙匙喂。
“你赶快吃两碗。”她催促道。
“我不吃……”我摇头。
“不吃我揍你!”她虎起脸,“眼圈都黑了,成了马骝精,两三天不给你拿吃的,饿死你了,还不赶快吃?!”
我立即复回厨房,哗啦啦地灌了三大碗。
“来,我背你。”我说,转身用背对着她。
“干什么?”她瞪大眼睛。
“背你到医院打针。以前我发烧,妈背我打两支针就好了。”我告诉她,那针不太痛。
她说,妈本来是今天带她去看医生打针的,因为档口出了事,夜里有几个造反派来吃了许多糕点,她要去打理打理,就没空带她看医生。我说:“正好,我来了。我背你去。”
“我可以慢慢走。”她说。
“不行,不让我背,我揍你。”我也虎起脸,以牙还牙。
我把她背在背上走出街口,向医院走去。街道上不少人望我。有的还站定像看猴子表演一样。有什么好看的?我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我知道,医院离她家并不近,要过三条街。我背得动。阿花说要下来走,我拧她的屁股蛋,说:“起风了,风很大,下来走又会冲风,病好不了更惨,知道吗?”她乖乖地趴在我的背上。
“三十九度。”医生对着体温计说。
开药打针,忙了一阵,医生说:“吃点药,不碍事的。”
我背着阿花回来的时候,悄悄对她说:“我很想你快快好,去上学。我真想上学去,可是……”
阿花说:“不管烧不烧,明天我要上学去。我拉下几天功课了。以后我教你……”
我把阿花轻轻地放在床上的时候,她说:“你真好。”
我用脸贴着她的脸,听到她的心在扑扑的跳。我敢说,她很想我久久地贴着她的脸。我的身体接触到她的身体的时候,又有异常感觉了。我全身感到舒服,“斑鸠”又翘起来了。她在发烧,我不能老呆在她身边,得赶快离开。
“明天我再送糕点去……”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