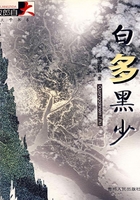事后,我问起哥哥说:“你出手打人的事,风波一定很大,当时是怎样被平息的?”
鹤哥沉默了一会儿,才讲起李排长是怎样介入并处理这件事的。
“连长出手打人之事,上级会过问的,这里按下不提。”李排长狡黠地盯着阿大,严厉地说:“阿大不报告,把战友的生命当儿戏,又不好好地如实地回答连长的话,有点目无上级,应当立即检讨!”
会议很快严肃起来,众人的目光一齐投向阿大,看样子他不检讨是过不了关的,你阿大这个班长算老几?班里跑了三个人,担当得起吗?
“我错了!”刘鹤忽地站起来,恭恭敬敬地在阿大的面前行了个礼,“阿大同志,我错了。我向你赔罪,我打你是违反纪律的,是军阀作风。我错了,我除向你赔罪外,当即报告营、团党委,请求处分我……”他是真诚的,话语沉沉的。
阿大低着头不说话,听到连长诚切的声音,立刻站起来喃喃地说:
“连长,你打得好。我的确错了。我对战友的生命这样不负责任。万一出事,怎么得了啊!唉……半夜里,我以为是风沙响……原来他们没有睡,在沙上躺着说悄悄话。崔指导员走时要我看顾他们。我没看着。他们果然跑了,我还不报告。我想,方圆几百里大戈壁,滴水也没有,渺无人烟,神仙会腾云驾雾也跑不出这块死地,他们会回来的,……我错了……我请求组织上处分我。”
“现在的问题不是处分谁的问题。是找人!”李雁声神色严肃,急切地环视会场,“二班长,蔡亮怎么独自持枪跑了?会出大事的!”
“报告排长,”二班长程伟站起来,“蔡亮是带着自己那只‘考古袋’跑的……我想,性质不同……不过,也很难说……我有责任。”
“先不定性质,把人追回来再说。做好抢救战友的准备。”刘鹤说,他抖掉军帽和衣领上的沙尘,把口气缓和了下来,“立即分三路寻找:回原连址之路;南古长城口;北边境线。各路都骑几峰骆驼,带上干粮和水,随时报告!注意,一定要保证人身安全。”
话毕,各路由李排长布置人力,立刻出动。
刘鹤未进家门,天伢就扑出来,紧紧地抱住他的大腿,不停地摇动:“爸爸,爸爸,我要鸟,我要玩鸟……”
要是往常,他会高高兴兴地俯下身子,在孩子的小脸蛋上重重一吻,然后像抛皮球一样,把小孩抛向空中,双手接住,再轻轻地捏一把,捏得孩子格格地笑。现在呢,他听到孩子的叫声就烦,浑身燥热,心绪纷乱,眼睛冒火。他变了。
“爸爸,我要鸟,爸爸,这儿怎么没有鸟……”天伢越发叫得厉害,满脸尘埃,满额汗珠。
“去去去,要什么鸟!”刘鹤抖动着大腿,孩子被抖落在鹅卵石地上。“讨厌鬼!”
孩子哇地哭起来,哭得好伤心。泪水汗水一齐淌,打湿了脸上的尘埃,脸蛋儿竟被涂成了大花脸。他是被父亲阴森的脸色吓哭的。他从未见过父亲这种嘴脸。他记得父亲是和蔼可亲的。在野马滩那阵,他见几棵红柳上有一只绿色的鸟,可能是美丽的神鸟哇!“爸爸,我要鸟,这是我在这儿见到的第一只鸟,我要,我要!”
“好的,好的,我捉住它!”爸爸把皮带往腰里一扎,直往鸟儿冲去。可怜的小鸟见有人追它,拼命地往沙漠的上空飞去。方圆几百里没有一棵树,没有一棵草,鸟儿累了,落在沙丘上。鸟儿被逮住了。天伢多高兴呀!他给鸟儿喂了些碎玉米,就放飞了。鸟儿还飞到红柳上。
“爸爸真好!”天伢高兴得跳起来,“爸爸,你是不是连长?”
“是呀!”爸爸立正敬了个礼。“有何吩咐?”
“我是团长!”他一挥手命令道,“有事报告,听我命令。”
“是!团长。”爸爸又立正敬了个军礼。
“刘——连——长”天伢厉声唤道,声调很长。
“到!”
“我命令你,”他随手把一个鹅蛋般圆的石头扔进床底,“立即把床底的大坏蛋抓出来!”
“是!”爸爸俯身爬进床底捡“坏蛋”,“嘭”一声,头撞着床板,后脑鼓起鸡蛋大的包儿。
那时的爸爸多好啊!可现在……天伢哭得很伤心,直撞回草棚里,妈妈缝衣服,听到儿子的哭声,立即撇开手上的活计抱起孩子。一见孩子的大花脸,丈夫的乌云脸,立即明白了几分。
“啥事不顺心,拿孩子出气?”她是善良的农村少妇,不会发脾气的,怯生生地问。
“珍,给我拿酒来!”刘鹤把军帽挂在柳条篱笆上,冷冷地说。
“啥事这么发火?”银珍望着他冰冷的脸,心里很害怕。每逢见到他不高兴她总是惴惴不安。
“酒呢?”他吼叫着,脱掉军装抛在简陋的床上。他似乎无法控制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