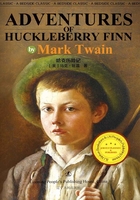在营地,我住下来了。我亲眼见到这里的战士们艰苦至极的生活。我听银珍嫂讲述这段时间发生的事儿。尤其是她到连队前后几天所遇上的事,三天三夜讲不完。
银珍带着天伢子经过几天几夜的跋涉行程数千公里来到那个“火星”腹地。一切都如此严酷。无情的枯燥的日子苦苦折磨着来自绿色南国的母子俩。
孩子要鸟,要蝈蝈,要青蛙,要花,要草,要野果儿,没有,统统没有。他失望了。
妻子要猪、狗、猫,要墨绿的韭菜,金色的南瓜,要女伴,没有,统统没有。她沉默了。
孩子缠着妈要蜜蜂。妈向空中撒一把沙子说是蜜蜂群。这里沙子贱,随手可以撒。孩子说这是死蜂。“死蜂死蜂不会飞,不好玩,我不要,就不要……”孩子哭了。“我要真会飞的蜂群。”
有一天正午,太阳毒花花的。孩子指着前方说:“妈,那是海,好蓝的海……我要游泳,我要游泳……游泳去罗!妈,你看那海真蓝……蓝蓝的海……”
妈拉着孩子追向“大海”,追了两三里,“海”还是在跟前,却不见水。孩子哭了:“我不干;我不干,海骗人,我不干……海骗人,海骗人,我不干……”
“孩子,那是戈壁的幻景,不是海。”刘鹤说。
“我不干,我要海,我要游泳!”孩子很固执。这个鬼地方啊,孩子和他妈都失望了。
此刻,刘鹤和银珍并排走着。月光像冷冷的水泼在他俩的身上。他们该说些什么呢?
突然,连队那边传来孩子的哭声。
“是伢子!”银珍立即在沙堆里奔跑起来。刘鹤没有跑。他仰起头望着冰凉的月亮,默默地在沙丘上徘徊。风,扬起沙子唱着尖厉的歌。
就在我住下的第三天晚上,我因为高地缺氧,整夜难以入睡。我的胸口像被大石压住似的。
忽然,在迷迷糊糊中听到了嘈杂声。
“报告。”二排长李雁声风风火火地跑过来,声音异常急促,“报告连长,一班彭洛、关雨、罗一波、还有二班蔡亮失踪!”
“什么时候!”刘鹤嚯地站起来,神色冷峻,他极力按捺着内心刹时涌起的火气,静候李雁声的回话。
“天刚拂晓才发现,可能是零点以后。”李雁声说得很急,“那时正起风沙……”
“他们带枪吗?”刘鹤问。
“不带枪。鼓洛、关雨、罗一波的枪早就锁起来了。娘的,蔡亮他……他背走一支冲锋枪……”
刘鹤沉默片刻,接着追问:“是谁负责做蔡亮的思想工作的?”
李雁声用袖子抹了一下额上的沙尘汗渍,摇了摇头说:“没有安排谁管他。这小子倒没发觉他有思想问题……唉,知人知面不知心,谁能包他不出事?”李雁声说着重重地跺了跺脚。
刘鹤愣住了。他竟没料到事态会发生这么急剧的变化。在野马滩时,来磨牙要求退伍的,被连排干部的“个个击破”战术给镇住了。关雨、彭洛和罗一波被大伙取笑为“赖皮蛇”,迁徙路上,还用了车轮战术死缠着连排干部不放呢!党支部分工指导员崔军天负责做这三人的工作。可是鬼使神差,崔指导员在队伍就要拔寨起程时说有急事到师里去了。谁料就在这节骨眼上出事?他浑身躁动,热血往上涌,恨不得长出双翅腾空而去,鹰抓小鸡地把他们四人攫回来,再用炸雷的声音警告他们:“在这死漠里离开队伍等于自取灭亡,你们懂吗?!”
十万火急。他们不知天高地厚,不知什么叫死亡,哪里是死亡线……就这样撞入死亡圈了。再迟,一旦龙卷风顿起,他们必死无疑。几百里死亡地带能去闯吗?刘鹤想到的首先是他们的生命。这是祖国的卫士,我民族的宝贵财富,如果就这样葬身于沙海,当一连之长承受得了责任吗?他还是使劲压住心中的烦躁和恼火,两眼死死盯住苍茫的大漠。
“传一班长阿大!”刘鹤想起发生失踪事的一班之长,顿时虎起脸,“通知所有班排长立即集合!”
“是!”李雁声转身就跑。
连里一阵骚乱。风沙呼啸,一片迷蒙。
这一带简直是死荒滩。原劳改场的芨芨草棚已经破烂倒塌,棚底全灌满泥沙。除了沙丘就是焦土、石砾。没有任何路,也没有可供集合队伍的小广场。全连官兵在沙窝窝里蜷缩了一夜之后,更显得困倦不堪。杂乱的脚步声和风沙声混合在一起,教人心神不定。连队一下子失踪四人,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在这无边无际的大漠,失踪就意味着死亡。刘鹤背着手急匆匆地来回踱步,他忽然站定,咬着牙,目不转睛地望着朦胧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