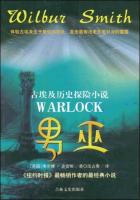铃姐在深圳那偏僻的蛇尾村的日子到底是啥样子,我一点也不知道。明婶只说她草草嫁了人。嫁给隔壁一个也叫明婶的儿子于刚。于刚当兵到了云南边境。铃姐心中似乎已经没有我这个弟弟了。她不来看我。我更没法去看她。时间长了,心也就渐渐地平静下来。
天常常会捉弄人,给你开个大玩笑,让你的心翻江倒海,难得平静。
这大玩笑开在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姐夫于刚(我从未谋面的姐夫)在边境自卫还击战中壮烈牺牲了。
铃姐麻烦了。她的命怎么这样苦?
我记不起是谁把这坏消息带到我的红砖楼来。我也不知道是谁把我带到了深圳的蛇尾村去。
我不敢认铃姐,她完全没了儿时那份活泼和机灵,生活的重担和精神上的损伤使她变得沉默寡言。我的突然到来,她是意料不到的。她端详我很久,才慢慢地走过来拉着我的手说:
“飞弟……”她很痛苦,两眼哭得红肿肿的。她的爱情就这样匆匆到来,又匆匆离开。丈夫在边境牺牲,使她更加孤单了。我安慰她。我说我知道这消息后,心也很乱,我不知铃姐怎样去承受这么沉重的压力。我的从未见过面的姐夫是怎样的,我不知道,只听说他当尖兵排的排长,攻敌人的堡垒时,他冲在头里中弹牺牲的。
“弟弟,姐姐的命不好。”铃姐还在抽泣,低声对我说。“我以为离开广州这个杂乱地可以求得安稳的日子,可是我一直未能安稳过。我们没了爸妈,三兄弟妹各分一路,永远没有安稳的日子了。”
我高声说:“看开一点吧,姐姐。安稳不安稳有什么呢?妈跳江,爸被石头砸死,安稳吗?不也过去了?你就闭了闭眼睛冲过去吧!我们的家都这样散了,还有什么比家破人亡更惨?你就放开一点,该怎么活就怎么活吧!”
铃姐不哭了,又去忙着家务事。
她留我多住几天。她说她不想到广州去,不想见那红砖楼。爸妈不在去见了红砖楼,她会更伤心。我说,这楼我在看守就行了。
姐夫有个弟弟叫于鲁,在大队里开货车。听铃姐说,他正和一个叫婉雯的女孩子恋爱着。
我这几天是个闲人,在铃姐的家里闲逛,冷眼见到一些事。这些事其实也很平凡。我未见过我姐夫,但我暗里注意姐夫的弟弟于鲁,我很想从他的言谈中推测姐夫的样子。
很奇怪,许多片断一幕幕地呈现在我的眼前。就像电影一样。我只觉得后脑在微微地颤动。这一颤动不要紧,我的脑海里就有了许多逼真的影子。
于鲁刚跳下闷热的驾驶室,就见婉雯蹲在马蹄河的石阶上洗衣服,河水被拨弄得哗哗响。
“喂!”他喊道,随手捡起一颗小石子。
婉雯稍抬起头来,冷冷地一瞥,不予理睬。
“怎么?吃了闷心丸啦?”他把小石子扔下河去,溅起一束水花。
没有回声。马蹄河的水咕噜咕噜地响着;一串串雪白的肥皂泡倏然散开,消失在急促的漩涡里。婉雯狠狠地甩打着衣服。
这是于鲁第一次遭到婉雯的冷遇。他真不明白,平时亲亲热热的婉雯,她的热情为什么遽然降到零度?
姐姐告诉我,于鲁和婉雯读高中时同班。他们都喜欢在一起玩。吹拉弹唱,活蹦乱跳的,日子一长便彼此生了爱慕之情。可以说,他们的爱刚刚开始。我不懂,乡村这样穷,这么偏辟,有什么爱情可言?的确,我一点也不理解,他们究竟是怎样谈情说爱的。就这样,于鲁就算遭到了婉雯的冷遇了么?
要是雁雁和阿花这样对我,我就受得了。冷遇?冷遇怕什么?你冷遇,我就不睬你,天地这样宽广,我流浪去。这于鲁算啥男子汉?
于鲁无精打采地走着,还未跨进家门,就听到母亲的咳嗽声。母亲明婶有老年肺气肿和胃病。昨天那场暴雨,来得那么突然,母亲受凉了。他跨进家门,就打开抽屉拿出止咳茶。他泡了一杯送到母亲床前。母亲半躺着,戴着老花镜在给于鲁的衬衫钉扣子。
“才回来呀,快过午啦,累坏了吧。”见儿子捧茶进来,明婶摘下眼镜关切地说。
“妈,我不累。今天跑二百多公里,大队买的那批尿素全运回来啦!”他把杯子搁在那张木桌子上,“喝吧,你咳得好厉害……”
“阿铃又把饭菜做好了,热在锅里,趁热吃吧!”
“阿铃呢?”
“到处挑柴草去了……这姑娘这样会累坏的。”
于鲁转身望着窗外,远去的马蹄河蠕动在迷茫的烟波里。他在想那件可怕的事: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这是多么不幸的日子呵!那天中午,由云南自卫还击前线传来了噩耗:比他大两岁的哥哥于刚在战场上壮烈牺牲了。年迈的母亲面向西南,老泪纵横。但她强忍着悲痛,没有哭出声来。那些日子,剧烈的痛楚和忧郁使这个壮实的小伙子消瘦多了,他变得沉默寡言,夜里常常在床上盘脚而坐,凝视着挂在床头上的哥哥的遗像,泪水落在席子上。
这个家实在是多灾多难。一九七二年秋天割“洋尾巴”,父亲被批斗含冤死去,抛下母亲和兄弟俩,日子越来越艰难了。于刚的突然牺牲,又倒了全家的顶梁柱。公社为了照顾烈士的家庭,让于鲁当大队的汽车司机,每月收入一百多元;明婶也进了大队缝纫社,生活得到了保证。最值得宽慰的是于刚的女朋友阿铃用姑娘那颗炽热的心温暖着这个蒙受着重大悲伤的家庭。
至今于鲁还记得,那天阿铃把母亲扶到床上,用嘶哑而低沉的声音劝道:
“明婶,不要伤心……我今生今世陪着你……”
我铃姐就这样傻头傻脑地生活。她对于刚就这样爱得死心塌地。她一天到晚总是这样默默地忍着内心的痛楚,像牛一样忙个不停,烧火煮饭,扫院子,里里外外打理得妥妥帖帖。
每见到可铃的身影,听到她勤快的脚步声,明婶的心就隐隐作痛,她不忍心这样耽搁铃姑娘的青春。她噙着热泪对阿铃说:
“姑娘,让你这样受累,我心痛……你该想想自己的事了。找个好主……这样,婶也放心……”
“好婶子,我不想走……我不能走。你身子骨不好,鲁弟又天天出车……这个家……”阿铃声音哽咽着,“好婶子,我求求你,别提这事好吗?我舍不得离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