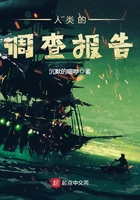事情总是离奇古怪。有时,你天天祈求那样东西,却无法得到。有时,你没有想它,它竟出其不意地来到你的身边。
卜风花就是这样出现在我的面前的。
春节连续几日弄得我越来越没劲儿。要吃没吃的,要玩没玩的。见到小胡子和三个女子鬼混,算我撞邪,行了衰运,今年怕要撞得鼻青脸肿了。我信这个。
我正在床上睡觉时,有人敲门。
敲了三五声,我不理。我这流浪者谁看得起?谁来敲我的门?小胡子是不必敲门的。他有钥匙,他随时可以带女人进入。
“阿飞,开门。我是阿花。”一个女子的叫声。
她说她是阿花!是阿花回来了吗?我一骨碌爬起来,赤着脚跑去开门。
来者是阿花?我不敢认。她个子比我矮一点,身体匀称,胸部浑圆挺着,脸蛋圆而红匀,眼睛很黑很亮。是阿花,那眼睛在说活,我认出来了。她已出落成一位少女,一位漂亮、和善的姑娘。我几乎不敢认她了。
“阿花。”我上前拉着她的手,不知说什么才好,嘴里喃喃地说。“你去了很久很久,今天才回来。我好想你,好想你。”
她低下头,久久不说话,两行泪珠落在厅的地板上。
我心里一颤,不知道她为什么落泪。
她抹着泪告诉我,她妈死了。
跛脚女人死了?我心里这样想的时候,突然觉得内疚。我不该老这样说“跛脚女人”。阿花是我的好朋友,她妈也应当是好朋友呀,怎么能老叫人“跛脚女人”呢?况且,她已经死了,阿花正伤心呢。我一时很内疚,我不知怎样安慰她。
“妈死了。”她重复着。“外婆早些日子也去了。银珍姐和珠海一间工厂的青年工人结婚了。剩下表妹……我把她带回广州……”
我一听心里好像有炸弹爆炸。
我走过去把她楼在怀里,她放声痛哭。
“阿花,有我在,你不要哭。我们都一样,家没有了。”我搂着她咬着牙这样安慰她。“表妹呢?带来了吗?”
她摇摇头。她说表妹留在她的小房间里,她就跑来找我了。
我知道阿花两姐妹已无依无靠。又没有档口了,日子更是不知怎么过。
“你一定还没吃饭,你妹也一定还没吃饭。你等等,我去弄点吃的。”我说着把阿花扶到我的床上,我拿着一个盆子,开门走了出去。
我摸摸口袋,还有六七元,就买了两碗猪肉面,装进盆子里,又买了十多只大馒头。
我要阿花快吃点填填肚子,还带一碗面和几只馒头回去让表妹吃。
她吃了几口就不想吃了,推到我的跟前说:“你瘦了。一定饿坏了。你哪有钱买东西吃呢?”
我说,我一个人饿不死。
我决意去看她的表妹。我把面和馒头带着。
那栋旧二层楼我去过,还和阿花在一楼靠东边的小房里睡过呢。
她的表妹叫贤珍。也有十一岁了,长得很乖巧机灵。她不怕生人。听阿花介绍我以后,她就更不害羞了。她吃着面和馒头,用大眼睛盯着我。
阿花在卫生间里开了水龙头。
哗哗流出来的是铁锈水,棕色的水把地面都染成了赤黄色。她惊奇地叫着:“这水变色了,是怎么回事?”
我说这是铁管生锈的结果,久不用水了,铁锈把水都染成棕色了。我告诉她让水龙头开着,流一会儿就行了。
一会儿,水清了。
阿花用脸盆打了一盆水给贤珍洗脸。她是个勤快的小姐姐。贤珍很少说话,任由表姐摆布。
“干脆洗个澡。这套衣服也该换了。”她把贤珍拉进冲凉房把门关上了。
“飞哥,你就在房里等一会儿,我给妹妹洗完澡再说。”阿花在冲凉房里大声对我说。
“我也洗。”我说。“让我进去,一同洗吧!”
“不行。”阿花说,“你是男仔,我俩是女仔不能在一起洗澡的。”
我觉得有一盆冷水向我当头泼过来。先前我不是和阿花一同洗澡吗?还脱得光光的一起睡在床上呢,现在却不能在一起洗澡了。阿花好像变了。她不是过去的阿花了。想着,我心里很闷。
我听到洗澡间里,花洒在沙沙沙地喷着水,她们一定是脱得精光,抹上香皂,滑溜溜的身子一定又嫩又白。我闻到洗澡房里飘出的香皂芬芳的气味。听到水触到皮肤发出的辟里啪拉的声音。这个阿花,过去同我一起洗澡,嘻嘻哈哈笑个不停。现在变成了陌生人似的。我觉得在阿花和我之间隔着一堵什么墙似的。
我忽然心灰意冷起来。一种被人抛弃,被人羞辱的感觉。
没等她俩洗完澡我就走了。走时我一句话也不说。我窝了一肚子气。
回到红砖楼,我倒头就睡。
连续两天,我都在倾听敲门声和脚步声。但一点动静也没有。阿花为什么不来找我?
第三天早晨,我按捺不住了。我悄悄地到卜风花住的地方去。我没有直接到她的房间去,而是在对面的猪肉档口旁远远地观望。
不知过了多久,我望见阿花和贤珍推着一部小车。车上堆着满满的破烂。有报纸,有酒瓶,有厚纸盒,也有烂水管和烂铁锅什么的。
小车装得太多,又高又大。她俩个子并不高大,一前一后,一拉一推,十分吃力。
她俩没有进家门,车子向前走了一段就拐了个弯不见影儿了。
我连忙跟上去。远远的望见她俩把那些破烂卸下来交给收购站。阿花和贤珍一件一件地卸,一件一件地称,约莫一个钟头,她俩才干完活。这时已是中午,太阳毒花花的,街道有一种灼人的气浪。她俩又推着小车走街过巷去收破烂。
好几天,我都在阿花的住处观望。发现她俩天未亮就出门去。中午必定在破烂收购站,晚上很黑才回来。
我失望了。我觉得世界在突变。我变成了极其孤单的人。我的心胸空荡荡的,脚步虚虚浮浮。心烦躁极了。
这天下午,日头虽然已经西斜,但还很毒。我到女头头的司令部去,女头头办公室的门上了锁。我在门口站了很久。这里已经没有先前的喧闹场面,更没有荷枪实弹的人急匆匆地走来走去。空气中没有火药味,只有灰蒙蒙的尘埃在阳光下悠闲地飘荡。
有人走过来问我到这里来找谁。这人穿件西装短裤,一件半新半旧的短袖衬衫,样子很机灵。我说找我的好朋友。他似乎有点惊愕。
“你的好朋友?你也有好朋友?”他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我。
“你怀疑么?”我用凶狠的目光盯住他。
“我就是怀疑。”他吼起来。“你大不了是个叫化子。”
“我是个贼头,丢那妈你想怎么样?”我的心躁得按捺不住,我要给他点颜色看看。“你有什么权来盘查我?”
这家伙也不示弱,一手扯住我的衣领,照着我的肚子就是一拳。我忍着。
论个子我同他一样高,论气力我看差不多,但论命我贱,我随便同他搏。也就是说,我有一股蛮劲,我一点也不怕他。
我的肚子吃了一拳后,剧痛。我捂了捂肚子,蹲了下去。他又抡起右拳向我的鼻子尖砸来,我一闪,他扑了个空。
我趁势扑过去,双手抱着他的头往后一拖,只“啪”一声他就往后倒地。我抡起拳头,在他的肚子上重重地击了三拳,再复一拳击中他的鼻梁。血,从他的鼻孔里喷射出来。
他翻身站起,一手拿过墙脚边一把铁铲,一阵风似的向我削过来。
如果不是我闪得快,脑袋瓜就会被削去一半。我猛地觉得,他已准备把我往死里打了。
我不能不防。
我一眼看见另一个墙角也有一把铁铲,就冲过去抡起那把铁铲。
铁铲的碰击声把人们召唤过来了。好几个人扑来,把我和他的铁铲抢走,两个青年死死抱住我。
“把他捆起来!”那家伙恶人先告状。“他冲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有人拿来绳索,真的把我捆起来。
好像惊动了楼上的人,都格登格登地走下来。他们好像在楼上开什么会。有人在上头问:“什么事?”
“打架。”
“谁和谁打架?”
“一个叫化子冲击司令部。”
我一听就火冒三丈。
我向着捆绑我的人吐唾沫,使飞脚猛踢他们的阴囊。他们痛得呱呱叫。
“把女头头叫来!”我咆哮起来。“女副司令,我的好朋友,你在什么地方?你的兵卒獠猡出手打我了!”
我的声音好像旱天雷。人们惊愕了。
有人悄悄去找女副司令。
我的好朋友终于出现在我的面前。
“飞。你怎么来了不告诉我?”女头头惊讶地说。随即喝住左右:“你们够胆把我的好朋友绑了?好大的豹子胆!还不赶快松绑?!”
他们忙着为我解去绳子,搭拉着脑袋站在那里。打我的后生对着女头头立正,脸色刷白。
“副司令,对不起,我不知道他是你的好朋友。”
“好了,好了,快散开!”女头头喝道。
她开了办公室的门,让我在她的座椅上坐下。她告诉我,楼上正开会。军代表在和各派头头在开会。看来小胡子要进革委会。
她告诉我,小胡子已经承认前几年抓错了许多老干部,打错斗错了不少老干部。擅自把他们流放到大西北是错误的。他说他做错的要由他改正过来。她说我父亲的冤案正在调查,小胡子态度还是好的,她要我保护小胡子。
我说,我的心很烦很烦,我说除了你一个好朋友外,我再也没有好朋友了。
“你先回去吧。我再设法去找你谈谈。”她说着从挎包里掏出八十元交给我。“你的生活一直没得着落是吗?先拿去买点吃的。”
众人已经离去。
司令部平静下来。女头头又上楼开会了。
我听到上面发生了剧烈的争吵声。
有人拍起桌子来,天崩地裂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