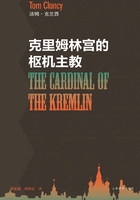五月七日凌晨,云南边境的扣文山在炮火里燃烧。敌人陷入弹雨和火海之中。战士在流血。山峦在流血。界碑在流血。祖国这一角灰蒙蒙的天空充满着战争的恐怖。愤怒和硝烟、血液和尘土混合着铺一条胜利之路,中国可爱的儿女们在浓烈的硝烟中穿行,在生与死,胜利和失败曲分永岭上冲杀、搏斗。
也在这天,另一个边境威市迎来了繁忙的早晨。在铁丝网和界河相交界的地方,飘荡看一片淡淡的晨雾。转眼红日喷薄而出,远近的建筑群被烧红了。炽热里,汗水和尘土搅拌在一起,急促的旋律,高频率的颤动,使每一寸土都不能安宁,每一空间都有建设者们建设的呐喊,创造的欢悦和爱情的甜蜜。
祖国的大地上,流血和流汗的土地是紧紧地联系着的。边境的战火也烧灼着特区人的心灵。
人们焦急地听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消息。这两天,阿铃和春兰为了方便照顾,搬到明婶的家里住。
夜,月光朦胧。春兰摸了摸阿铃的床位,空着。她一骨碌爬起走出门去。阿铃正在院子里徘徊,昏暗的月光穿过高高的杨桃树,洒在地上,显出淡淡的倩影。她徘徊一阵子,就坐在石碾子上,面向西南方久久不动,仿佛要透过万重关山遥望弹雨交加的战场。
“阿铃,睡不着吗?”春兰问。
“睡不着,夜太长了。”阿铃笑着说。
“我知你在想什么,嘻嘻!”
“你猜不着的。”
“想念于鲁,对么?”
“猜对一点儿,不具体,记六十分。”
“哟……”
“我是想,于鲁打胜仗来……”她心情很复杂。
“哦……”
月顿时亮了。杨桃树下两位姑娘靠得很近,笑声象哗哗的泉水。
“我们找婉雯去?”阿铃说。
“去,看她在忙些汁么!”
月色渐渐淡了,田野的虫儿已停止歌唱。远近宁静极了。
她俩来到婉雯的家门口,悄悄地靠近婉雯的窗口。窗口敞开着,里面传出轻微的鼻鼾声。她俩不想叫醒她,转身出了院子。
“那封信交给婉雯了吗?”阿铃问。
“我才不交呢!”
“你敢?!”
“我才不怕呢!哼,‘内详’,说不定……哼!”
“拿来!”阿铃命令道。
春兰狠狠地瞪阿铃一眼,无可奈何地从裤袋里掏出那封信,塞给阿铃:“听着,万一是香港同她搭上线,我同你算账。”
阿铃拧了拧她的耳朵,她哎哟哎哟地叫起来。
阿铃放轻脚步走近婉雯的窗口,把信投了进去。
三天后,云南边境来信。
明婶、阿铃、婉雯、项雨各得一封。阿铃那封也写着春兰的名字。日期,四月五日,这些信整整跑了一个月。于鲁是否参战,一概不知。信,感情浓烈,详细介绍边境战士生活的艰辛。
阿铃、春兰:
你们能想象出我们的生活吗?半个月长途跋涉,我们被晒成了红辣椒似的。我们曾在“八十年代上甘岭”上扎营,每天只分一碗水!有一次班长带我们下谷取水,在半山腰上滑了脚,班长滚到谷底,壮烈牺牲了。我们饥渴得说不出话来。我写了两句诗:“我守卫着祖国的万条江河,只赢得难忍的饥渴。”这境界不高吧,而事实正是这样。你不要笑,我老想着家里一箱箱汽水呢!你们知道什么叫猫耳洞吗?这猫耳洞般的小山洞是我们的宿舍,洞壁全是湿漉漉的泥浆,还滴水呢!我们半躺着,满身黄泥水,整夜不能睡——敌人就在对面的山上,夜里常常偷袭。不少战友得了综台疲劳症,就是睡不得,吃不下,时刻处于紧张状志——的确我们有点面黄饥瘦了。你不要笑,我老想着家里的弹簧床和软软的沙发呢!你们知道什么叫黑暗吗?夜里,山洞是黑暗的世界,我们不能点灯。敌人的贼眼老盯着我们。灯一亮就开炮。那晚在山脚放电影,灯一亮大炮弹就落下来了,周围的草丛全是敌人先前埋下的地雷,鸟飞落也会炸飞,腾起一蓬蓬鸟毛毛!不要笑,我真留恋特区明亮的灯海,隆隆的机声!
不写了!你以为我怕苦么?嘿,怕苦我就不来了。死都不怕,还怕苦?!很快我们就投入战斗,流血牺牲在所不辞。我只希望你们在崭新的特区生活中,不要忘记我们,彼此都在边境。你们投入建设,我们投入战争,看谁先立功吧!
祝你们快乐!
于鲁
四月五日
读完信,两们姑娘沉默了许久。阿铃小心地把信折好,慢慢地放进裤袋,还按了按,怕飞了似的。
阿铃说:“把婉雯的信送去!”
“是!”春兰倏地立正。
婉雯接到信,脸色沉下来。她迟迟不想拆信。春兰不想走,老瞅着她。脸上有几分怒色。
“哎,这鬼天气,我又感冒了。”婉雯用手捂着额角,长长地叹了口气。
“我有驱风油……”春兰立即说道。
“不用了,让我躺一躺吧!”
“躺吧!要不要找阿铃来?”
“不,不,让我安静安静。”
春兰踏着重重的脚步走了,头也不回。
婉雯的头的确很痛。那封“内详”弄得她两夜不得安宁。
“我总算找到了你,我心中的女郎。”她想起信中那段话,“想不到唐诗宋词为我们架起桥梁。踏着这桥过来吧。其实,这种桥是空的。我以为世界应该是个实体,只有酒家、银行,旅馆、一幢幢洋楼、一辆辆汽车才是实实在在的。你不妨想一想……感谢舅舅和伯母,他们多希望我们好!……人生在世有几何?你想到美国的纽约,法国的巴黎去吗?你妈妈要重游香港,这是很容易办到的。”
她闭上眼睛想了一阵,慢慢地睁开眼,手情不自禁地撕开信封。
“我终于能给你写信了,我的雯。”她读着信中那刚健有力的文字,“想不到界河流通了我们爱情之路。其实,界河的流水只是一道幻影。我们的汗水才是充满活力的,有一股巨大的能量,爱渐渐在这种能量的支配下成熟。……感谢刚哥,为我指出这条战斗之路。……战斗结束后,你来吧,我带你看看猫耳洞,看看鲜血染过的战壕。你愿意吗?”
她被困在人生的漩涡里了。她感到天旋地转。她的确头痛得很。她隐隐约约地觉得于鲁去打仗了。这对她似乎没有多大的震动了。但愿他平安无事。他是好人。她清楚地记得干爹说过,秦先生很快又要过来洽谈大生意。“他与我有何相干?”她想道,“可是‘内祥’是他写的,怎么不相干?”她的确头昏脑胀。
这天中午,天气闷热。方娟在门槛上坐着,等婉雯放工回来。老远,她熟悉的摩托车一响,她就忙开了:打开冰箱,端出冰冻橙汁汽水,接着就端出炒龙虾、炖鹌鹑,蒸鲜鱼来。她觉得自己生了个宝贝女儿。
“吃吧,是妈专为你做的。”
“我不想吃!”婉雯感到胃口很差。
“你忘啦,今天是你的生日哩!”
“……”
她拉着婉雯走进里屋,指着放在桌上的一部双卡音响组合,喜笑颜开地说:“干爹说这是秦老板送给你的。祝贺你的生日。”
“妈,你怎么随便接受人家的礼物?”
“秦先生是好人,你若不是八字正,命好,能得到他的赏脸吗?”方娟瞪女儿一眼,兴高采烈地说,“他说……可带我们出港逛逛。唉,我已有三十多年没回港了……”
婉雯不想说什么,无精打采地坐在那里,丰盛的午餐一点也没动。
她想睡午觉,歇息一下纷乱的脑子。特区生活的节奏太快了,每天都弄得筋疲力倦。她迷迷糊糊地躺在床上,大地蒸腾起来的高温气流从窗口钻进来,烘得她满头大汗。她索性对着电扇解开外衣,只穿三角裤,戴着乳罩,直挺挺地躺的床上。她心很烦,睡不着。于鲁的来信又在脑际闪现。看什么猎耳洞、战豪啊?!她从箱子里掏出那封“内祥”,仔细地看着。心里象有潮水在激荡。她到了这样烦闷的年龄,常常难以抑制自己。爱的力量充塞着整个身心,象一条潜藏的暖流盘踞着她的心灵;爱情会化成种种形式,它渴求献给别人,给人家以养份,并随时为之牺牲。然而,于鲁走了,带着她的爱走向遥远的地方……太渺茫了,几个月来又该与谁倾心相许。剖腹相示?正在这时,秦先生大踏步闯进她爱的领地。潇洒、大方,才貌出众,他是有文学修养的企业家吗?凭这些,能没有三妻六妾么?为什么爱上我呢?是真的吗?是梦吗?她无法向自己解释。
她瞌睡得迷迷糊糊信纸飘落在床上,压在她的腋下。
……黄昏即将降临,天宇倏然拉开辽阔的帷幕。
——晚霞如火。秦奉月突然驱车来到方娟的家,亲自请母女俩到友谊大酒家赴宴。朱经理、崔云志在座。香槟和威士忌的桔红溢满杯盏。秦奉月醉眼陶然,盯着婉雯,含情脉脉,婉雯脸色绯红,方娟未饮先醉,朱经理示意崔云志频频斟酒……冷气虽然开得很大,却遏不住这炽热的酒宴和他们火热的心。
——残阳似血。于鲁率领的爆破组,被弹雨压在土坑里,尘土一层层地盖下。——整整一天没喝过一滴水了。眼睛快要喷火了。他冲出土坑,肩部中弹,殷红的血渗湿军衣,一滴滴落在泥土里……于鲁带着战友硬冲上去……洒一路鲜血……
——星辰在望。项雨、阿铃、春兰,淑莲和妞妹围坐在明婶家,焦急万分。宴席的酒肉味,战场的火药味一齐呛来,令人窒息。阿铃望着桌上的汽水说:
“于鲁他们一定饥渴难忍了。”众人默默地吃着,边境的硝烟笼罩着她们的心,提不起情绪。唉,阿铃是把泪水和汽水一齐灌下肚里……
阿铃、春兰在悲愤中呜呜地哭了、在项雨面前,她俩可以放心痛哭,平素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她俩喜欢找项雨倾诉。项雨最痛爱她俩。他觉得阿铃正真、善良、勤恳、人品好,心灵美,他在内心是深深地爱上她。她也很尊敬和体贴他。他记得有一次,港方来了什么代表团,大队决定让项雨出席作陪。他匆匆去了。
阿铃见项雨穿一件中山装走过,马上拉住他的手:
“你的西服呢?”
“不见了。”
“我烫平叠在你的枕头底啦,真糊涂!”
“不用啦。”
“不用?下午快穿上!”
“好的。”下午他果然穿得笔挺。
平素,阿铃是他的得力助手。想找她单独谈谈,吐露自己的爱幕之情,可始终没有这个勇气,只得把感情按在心底。
春兰呢,这位坦率、直爽、泼泼球辣的姑娘,在项雨心灵的底层上也留下不可磨灭的印。那几天,他患重感冒发高烧,躺下了。春兰守候着他,给他煮药,煮粥、擦汗……
这些,项雨都默默地记在心里。
项雨、阿铃和春兰骑着自行车奔向威市人民医院。姐妹和淑莲被项雨派到友谊大酒家去“刺探军情”。明婶的刀口虽已愈合,但胃切除了三分之二以后,只能进少量的稀粥,胸膜炎和肺气肿使她咳嗽不止。这几天,她惦记着在边境打仗的儿子,食欲很差。项雨每天都从酒家饨些营养补品托春兰送去,常常原封不动地端回来。
阿铃知道明婶的脾气,每天的新闻联播,她都要听完,便把家里那部收录机搬到她的床上。
三人坐在床前的凳子上守候明婶,明婶的脸露出笑容,这笑容饱含着欣喜、激动和慰藉。
“明婶,鲁哥没事,你放心吧。”春兰说。
“他跟他哥那样不怕死,总喜欢冲在前头……”
大家沉默着,心都跳得那样急。
三人告辞明婶的时候,妞妹和淑蓬气呼呼地跑来,说婉雯从酒家出来时,成了个醉鬼,同秦奉月搂搂抱抱。
大家脸色大变。阿铃和春兰气得涨红了脸。项雨叫她俩别心急,要沉住气到她家找她淡,情况若真有变,马上告诉他。说完驱车回酒家去。
当晚,阿铃和春兰在婉雯家门口等到夜里一点,还不见婉雯回来。她们又到电子厂询问,守门老汉说,从昨天起她已不来上班了……
直到第三天中午,她俩才在婉雯等到婉雯。她的卧室换过了淡绿色窗帘,床已换成双人弹簧沙发床,桌面有一盆开得火红的海棠花和一瓶高高昂起的红玫瑰。音响组合机在播着香港流行的时代曲。她俩刚进房就闻到浓烈的香水味,禁不住倒退两步。
“哟,几天不见,洋啦!”春兰说,“彩电呢?”
“在妈房里。”婉雯若无其事地说。
“我俩有件事想问你,你能老实同我讲吗?”阿铃郑重其事地说。
“啥啦?问吧。”婉雯把咬在嘴里的发夹夹在瀑布式头发上。
“你给于鲁写信了吗?”阿铃温和地问。
“写了,昨天寄走了……”
“写些什么呢?”
“我不想告诉别人。”
“我看你心里有鬼!”春兰的脸涨红了。
“……”婉雯面色如蜡。
“你到底写了些什么?”阿铃焦急地追问。
……没写什么。”婉雯负疚地低下头。
“一定有鬼。为什么不敢讲?”春兰的胸脯起伏着。看来,她死心要打破沙锅问到底了。
一阵沉默。
“是安慰于鲁,还是……”阿铃的态度缓和了些。
婉雯的脸顿时变得铁青,反问道:
“我是犯人啦!你们有权审判我么?说就说,我怕啥?恋爱婚姻有自由权。告诉你们,我和于鲁的事,吹了!”她从抽屉里拿出几张信笺,“啪”地掷过来,“这是我给他的信,留的底,看吧。”
她俩大吃一惊,拿起信就看。
于鲁:
你读到我这封信的时侯,或许我已离开威市。你不要伤心,让过去的化作一场梦吧!
历史太多情了。人生的梦多么奇怪。我不想也无法去解释,当初我们为什么相爱。
你抛开美好的生活,跑到边境受苦,还要献出鲜血和生命,我同情你。但是,同情决不是爱情,我不能不作新的选择。我们都有自己的追求。你的信仰和追求可能比我的崇高得多,然而对于我却是那么渺茫。我认为我的追求会更现实一些。
爱情如果永恒不变,地球也就凝固不动了。于鲁,让我们各走一方吧。等待是一种慢性自杀,我的愿望在等待中消失了,我的心已在等待中死去。原谅我,我只能作新的抉择。
忘掉我吧!于鲁……
战争是残酷的。我希望你多多保重。我默默为你祈祷,祝你平安归来。
婉雯五月八日
象重型炸弹同时落在阿铃和春兰的心上。心碎了。她们都觉得一阵眼黑,差点昏了过去,她们强忍着内心的痛苦,站起来,眼睛迸出憎恨的光。信被狠狠地摔在地上。
“无耻!”阿铃从不骂人,今天她无法容忍,“婉雯,你的良心呢?你的良心……”
婉雯把脸转向里屋,她低着头默不作声。
“你要讲清楚,对着威市,对着电子厂,对着甜风酒家,对着特区的兄弟姐妹讲清楚!你是怎样戏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鲁哥哪一点对不起你婉雯?!”春兰暴跳如雷。
婉雯呆呆地坐着任她俩数落。
“走!”阿铃满腔怒火,连看也不看婉雯一眼,拉着春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