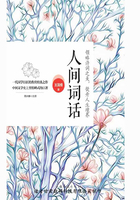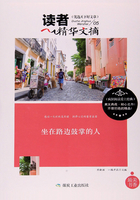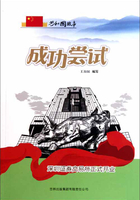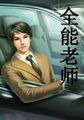余中明最喜欢一个动作。每当做完一笔业务的时候,他就要重复几次这个动作。这个动作一出现,手下兄弟们都知道:老大高兴了!
这个动作其实很简单。就是香烟抛出手后在空中划一道弧线,然后,看着对方忙天火地地把香烟接住,然后,再笑一下,说谢谢老大。每当这时,余中明就有一种主宰世界的感觉,心情是无比的欢畅。吞云吐雾后,往往就再这样抛洒一次,或者两次。这既是一种庆祝,也是一种犒劳的表示。接下来就开始分钱。想想这是多么快乐的日子。
有些事是说不明白的,比如爱好。有的人一生不吃泡菜。有的人一生不吃凉粉。有的人天生怕打针吃药。有的人喜欢抠鼻子。有的人喜欢头自然摆动。有的人喜欢跺脚。有的人喜欢摇腿。余中明却特别喜欢看着香烟在空中飞,然后再划一道弧线落在手上,或者掉在地上。这喜欢由来已久,已深入骨髓。
其实,在华蓥山一带,香烟不叫香烟,叫纸烟。抽烟也不叫抽烟,叫吃烟。后来,在城里生活很长时间后,余中明仍然喜欢叫做吃烟。掏出烟来,在烟盒上磕一下,这是要发烟的前奏,然后,眼光望向某人、手一抛:“辛苦了,来吃烟!”
这种叫法虽然不普遍,但很形象。华蓥山从唐代开始就是川东北佛教圣地,位于川东,延绵三百余公里,主峰海拔一千五百九十米,地理位置和气候决定了这里适合种植旱烟。在余中明幼小的心灵烙了最深印记的是,每家每户都种了那么一块地的旱烟。到了七月,在太阳的强烈照射下,烟叶开始发黄。巴掌大的烟叶由碧绿慢慢转淡黄,好的烟叶就转成了金黄。若遇雨水多,那烟叶就带一点黑色。父亲和哥哥的烟瘾都特别大,因此,家里种了一大块地的旱烟。烟叶收割后,余中明看见爸爸和哥哥在阶沿上把这些晒得干燥的烟叶打捆,那动作是异常的小心,如对待珍贵东西一样,有时,两人捆着捆着就停下来,把零碎烟叶卷一支烟卷。这样的事情爸爸做得最好。他把这些零碎烟叶理顺,看来烂渣的烟叶,在他手里一过,就变成一条归整的、长短一致的烟叶了。爸爸往往把烟卷成中指长,然后,掏出简易的竹管烟竿,点上吃一口,说:“够味!”然后,又把烟递给哥哥:“你也吃几口!”哥哥就拿着烟竿,在身上擦了一下,狠命地吃了几口,吐出股股浓烟。呛得余中明连忙跑开了。
农民一日复一日的劳作,男孩子长到十三四岁不上学了,就开始下地重复父辈的生活,因此,干农活不到一年,都学会了吃烟。看着孩子呛得鼻涕眼泪的,但父亲总是笑着鼓励:“再吃几次就舒服了!”因此,山里的男孩子都会吃烟,并且用手裹烟的技术都很好。
吃旱烟往往有一个竹管烟竿,因此,互相吃来吃去的时候,是不用摔或抛的,因为点着火,容易烫伤人手。别人吃几口,递给你,后者就连忙跑过去接着吃。
在山里长到十六岁,余中明是不会吃烟的,这在大家的眼里很不寻常。像他这样年龄的山里娃,牙齿有的已经被旱烟熏黄了,走到哪里都有一股浓浓的烟味。有时还甚至边吃烟,边刺溜出一泡口水,那样子,完全与农民融合成了一体。可是余中明初中毕业回到山里两年了,还是那么清清爽爽的。别人递他烟,他就摇头。别人向他脸上喷烟雾,他连忙跑一边去,栽地下猛咳,那样子真是活受罪。都笑着说,余二娃这小子不是吃烟的料,不像一个农民。
余中明的内心,也确实不想吃烟。他有时看着同龄的孩子,旱烟一支接一支的吃,就想不明白,没有吃什么啊,吃了又吐出去了,有什么意思呢?再说,还有很大一股熏人的气味。一支烟递来递去的吃,也不卫生。余中明是上过初中的人,自然知道的比别人多。
另一件事,留给余中明的印象也特别深刻。大凡偏僻、落后的地方都很原始。人们的心灵还没有一点污染。山上有座庙,建于唐代,庙虽不大,大雄宝殿却很庄严。每年的各个节日,特别是有关观音菩萨的生日、落难日的什么都香火旺盛。山上另外有一座煤矿,国有企业,工人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做一个煤矿工人在山里人眼里,那真是国家的人啊,每天按时上下班,有时还有电影看。这些煤矿工人或者家属都自觉地去烧香,有时,还请和尚念经。为的是保平安。山里的农民有时扯皮,就提上公鸡到庙里去砍鸡头发誓。那仪式非常庄重,余中明去了一次就不再去了。赌咒发誓的两家人站成两排,两家的男人就高举着公鸡,对着庙里的菩萨庄严地说:“菩萨有眼,我如果拿了耗子药闹他猪,就让我全家死绝!”然后把呱呱叫着的大公鸡放在神龛上,手起刀落,鸡血四溅。那情景看得人心惊肉跳,大脑神筋都绷紧了,再看面前的菩萨,竟然怒目圆睁着主持着这一切一样,让人不寒而栗。
山里虽然没有法律,但庙宇就是法庭,所以很少有违法乱纪甚至偷鸡摸狗的事发生。村里有个余中全,有次父亲生病想吃肉,没有钱下山去买,就到其他人家去偷了一只鸡,没想到,第二天就被别人家发现了。凡是从他家路过的人,每人都吐了一泡口水。吐口水是山里人最鄙视你的表达方式。后来,余中全在父亲的带领下,挨家挨户的登门磕头道歉。每到一家,余中全都狠命地抽自己嘴和脸。等一趟下来,腿跪麻了,嘴和脸都肿了。余中明看着余中全那副样子,自己不由自主的就筛起糠来,颤抖得不能自已。
都担心说,余中明这孩子,一点不像农民不说,还弱不禁风的,后来怎么生活哟!
表面平静的余中明,内心却翻江倒海。在农村他做农活基本上是磨洋工。如果连农活都做不好,这样下去,是很难讨到老婆的。爸爸妈妈常常看着余中明单薄的身子担忧。
余中明的第一个变化是想抽烟了。是抽烟而不是吃烟。这个想法来自隔壁余红伟家。余红伟的舅舅在县城火柴厂工作,一次过年到余红伟家来,山里很少有城里亲戚的人家,有这样亲戚的人家就特别不一样。每逢亲戚来了,全村老少都要来家看一看的。至于看什么 ,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妇女们来看城里人的穿着。看客人的皮鞋、裤子。皮鞋是人造革的,用水一洗,特亮。男人们来看城里亲戚的派头。城里亲戚就是不一样。看见男人,就掏出一包烟。这是许多山里人第一次见到什么叫香烟,与旱烟完全不一样,用白纸包着,每支都完全一样。每支还自带烟杆(烟嘴)。那亲戚就把烟拿在手上,向男人们一个一个的抛:“来,抽香烟!”被叫着的男人就去接。跑着追烟,有的接住了,有的未接住。接住的就笑未接住的。没接住的就更加狼狈,赶快弯腰捡起地上的香烟,用嘴吹一口,又在衣服上擦了几擦,就拿在手里端详,又用鼻子闻了闻。城里亲戚说抽啊。又为大家点火,都围上去借火,于是一派喜气洋洋。
城里亲戚也给余中明抛了一支。当时余中明还没有心理准备。因为山里人都知道他不吃烟。他也没想到城里亲戚会给他抛烟。城里亲戚向他抛烟的时候,说了声:“来,小伙子抽烟”话未落音,烟就抛来了。余中明伸手就抓住了徐徐下落的香烟。城里亲戚说:“小伙子怪敏捷嘛。”又掏出火打上:“来,点上!”
余中明在大家的鼓励下抽了第一支烟。刚抽时,他也学着其他人的样子,一口烟突然卡在了喉咙,呛得他大咳。连忙跑回家了,等一支烟抽完就天旋地转了。躺在床上,天旋地转的难受。脑里出现得最多的,就是香烟在空中的那一道弧线,如海市蜃楼般烙在了余中明的心里。其实他知道那叫抛物线,把一个物体抛出去,由起点到终点形成的线,就叫抛物线,多为曲线,即弧线。当时老师还做了一个示范,把半截粉笔头抛了给大家看。当然如果抛物很轻,受风及空气影响,也是会改变路线的。
打工潮席卷大地,对于那些急欲脱离土地的农民来说,无疑是福音,对余中明来说,常常感叹是生逢其时。对于一个农民,不会或者做不好农活,那是一件悲哀的事情。证明自己根本不是当农民的料。余中明带着小侄子,常常坐在山上,看着爸爸、妈妈、哥哥、嫂嫂在田间忙碌,就陷入了苦恼。自己快十七岁了,再这样下去,肯定连老婆都讨不上。好在这时的初中同学邀他跑沿海,说是打工。
望着能吃不能住的余中明,一家人很快达成了共识,让他出去闯,说不定还能带回一个婆娘来。爸妈最操心的是,要给余中明盖几间房,还要给他找个老婆。比较而言,盖房还是容易些,不外乎多累几年,三间泥瓦房就立起来了。最让人操心的是,余中明在农村是很难讨到老婆的。其实,打光棍的也不少,可是,如果一个家庭出一个光棍,是很让人看不起的。一家人商量,把栏里的一头肥猪卖了,怀揣几百元钱,余中明就开始闯江湖了。
都说沿海遍地是黄金。那要看对哪些人说的,对于做大生意的老板,可能弯腰就能捡到钱。但对于余中明这样无学历无技术的进城民工来说,则是异常的艰难。好在沿海兴起的企业多,需要大量的农民工。余中明和同学总算在一家厂里找到了搬运的工作。
搬运的工作是辛苦的,而且不分时间。有时冬天睡得好好的,运货的车一来,就得连忙爬起来,这样一折腾,作息时间根本没有规律,再回到床上就怎么也睡不着了。余中明就坐在床上,和同学一支接一支的抽烟。抽完一支,就向对方抛一支。那烟就在空中飞来飞去的,余中明故意抛高,让烟在空中划出那一道道迷人的弧线,也不接,让烟掉在床上。
辛苦的劳动,终于有了令人满意的结果。一年下来,余中明净存了八千元。他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钱在存折上只是一个数字,一个很抽象的概念。余中明很激动,下午偷偷把钱取出来,晚上躺在被窝里,拿着那一沓钱翻来覆去的看,怎么也看不够。就放在鼻子底下闻,一股纸张和印刷的味道香入心肺。他狠命地闻着这味道。这一晚,在这醉人的钱香中,余中明睡了一个好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