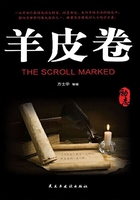无论做什么事情,没有坚定的信念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遇到闲难,或急躁或退缩或希望它凭空消失,都是不现实的。只有持之以恒、坚忍不拔地进取,才能克服危难取得事业的成功。
1.志有定法,脱于俗流
天生为凡人,怎能脱流俗?每个人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只要忠于自己的理想和选择,就获得了脱离世俗的心志。
志向,与其说是奋斗的目标,不如说是生存的意义。
立志是一个人成事之根本。任何人欲成就大事业,就必须要先立志。孔子日:“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诸葛亮讲“志当存高远”。曾国藩的同僚胡林翼说:“人生决不该随俗浮沉,生无益于当时,死无闻于后世。
惟其如此,我们应自立自强,努力做众人所不敢为、不能为的事情,上以报国,下以振家,不负此昂藏七尺之躯。”他所以说得好,是因为他说得全面、朴实,我们人人都可以做到。当然说得和曾国藩最为接近的是王阳明,他主张在学习和奋斗之前要先立志,不立志就好比种了植物不培根、不浇水,只能是徒劳无功而已。这种观点与曾国藩主张的以志为本是一个道理。
立志是一个慎重又多思的过程。曾国藩曾为立志心神不宁:“自从去年12月如日后,我常常忧心忡忡,不能自持,若有所失,到今年正月还是如此。
我想这大概是志向不能树立时,人就容易放松潦倒,所以心中没有一定的努力方向。没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宁静,不能宁静就不能心安,其根本在于没有树立志向啊!”
曾国藩不仅为无志而忧,更为有志而叹:“人苟能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有大抱负,才有大动力、大毅力、大魄力,也才会有大境界。所谓大抱负不是好大喜功,不是好高骛远,而是放眼天下,志在四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谓大魄力也不是有勇无谋地一味付出,而是危难时刻的果断与冷静,谨慎与精明。可以说,想确立远大的志向就要先学会放下小的情怀。过多地咀嚼一己之悲欢,就看不到脚下的土地、身边的世界,也意识不到自己对天下的责任,当然不会产生大的气象和作为。
曾国藩在20岁以前,虽然跟随父亲勤奋读书,但并没有大的志向。道光十年(1830年),其父曾麟书将其送到衡阳汪觉庵先生处学习。一年后,又回到本县涟滨书院肄业。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曾国藩眼界大开,助长了他锐意进取的精神。为痛下决心,他毅然将原字伯涵改为涤生,按照他自己的解释,“涤”
就是“涤其旧污之染”,“生”即“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寓意自己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出淤泥而重生。
他给自己定下的座右铭是: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只问耕耘。
这也是曾国藩传于后世的最经典名旬。
早年的曾国藩就经常自比于李斯、诸葛亮等“布衣之相”,幻想有朝一日自己也成为像他们一样的名相,千古流芳。随着其学识的增加,思想的逐渐成熟,他对其志向的思考更加深入和具体。
曾国藩认为立志必须有步骤,但光有志向还不够,更需要“勤”、“俭”、“明”、“孝”、“信”等素质予以辅助,几方共同作用才能够达成志向。
“勤”是曾国藩本人谈得最多,体会最深的品质之一。它与曾国藩的“力行”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说,“勤”字为人生第一要义,无论居家、为官、治军,皆以“勤”字为本。自古以来,当政之人皆以“勤政爱民”为训;为官之人只有勤于做事才能造福于一方百姓。曾国藩也深知这一点,他不仅率先,而且还勉励部下做到“身勤”、“手勤”、“口勤”、“心勤”,所以说,“勤”的精神贯穿了他的一生。
“俭”。鉴于明清统治阶级的奢侈腐败导致的社会危机,曾国藩主张戒奢崇俭。他认为,这样既可以减少应酬开支,又可达到“俭以养德”的效果。他说:
“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息则难望有成。”这一点对于现代的年轻人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
“明”既可指办事能力,又可指道德修养。曾国藩说:“大抵莅事以‘明’字为第一义。……凡高明者降心抑志,以遽趋于平实颇不易。若能事事求精,轻重长短一丝不差,则渐实矣,能实则渐平矣。”由此可见,心明眼亮,办事明快,有效率、有水平是实现志向的必备素质。
“孝”。曾国藩说:“盖君子之孝,尤重于立身,内之型家式乡,外之报国惠民。凡吾行事足以令人钦仰者,皆吾所以敬吾亲也。凡吾德意足生人感恋者;皆吾所以爱吾亲也。推此以求,则尊显之道事业无穷。”他认为只有立身、立志,方能更好地行孝,孝在这里不是狭义的尊老,而是广义的惠民、亲人,不只是父母,而是天下所有值得敬佩和尊重的长辈,有一些“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意味。他把尽孝与立志巧妙地结合起来,所以他能有比别人都豁达的心胸,事业有成也就不足为奇了。
“信”。曾国藩认为,“失信”为清朝官吏无为堕落的根源。为了挽救其堕落,纠正封建士大夫奸滑、浮伪的恶劣作风,他以“诚信”相标榜。他说:
“信,即诚实也。一言不欺,一事不假,行之既下,人皆信之。”
曾国藩指出的这几个方面,正在于他个人的精神修养。曾国藩认为,精神的修养全是内心所要做的功夫。
所谓治心之道,皆属于精神修为。由古至今,凡有所成者无一不注重精神所得。只为做事而做事,与为志向而谋事是不可以相提并论的。而只有达成志向的同时也能获得精神丰收,才是不流于俗之志。
2.以身作则,严于律己
一个统帅、领导别人的人,首先要不断地完善自己。最好的收心方法就是成为众人的榜样。
为人处事讲求原则,高标准、高要求、高效率,但能做到对人的过错不计较和苛责,这样的领导则少之又少,曾国藩算是一个。
曾国藩处理“秦淮灯舫”一事,充分说明了他的居官原则。
秦淮河是古都南京的古迹名胜,也是游船画舫的积聚地。太平天国运动期间,秦淮河一带受到战争的洗劫,日渐萧条凄凉。战争结束,秦淮河畔出现了昔日的画舫,恢复了繁荣景象。
六安郡的太守涂廉访,思想保守,对这种情形看不顺眼,便通令各县严厉禁止秦淮河的画舫灯船,并把此事的处理结果禀报了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曾国藩对涂廉访说:“听说淮河灯船,尚寥落如星辰。我多年前曾过此处,只见千万船只来往如梭,笙歌之声彻夜不绝,实在是太平年代的一大乐事啊!”涂廉访听后,甚是别扭。
没几天,曾国藩约各位官员共游秦淮河,并设宴款待太守涂廉访。席问,曾国藩风趣地对大家说:“30年前,我是心向游弋而不敢游弋,30年后,我是心不想游弋而不禁别人游弋。”停了一会儿,他又说道:“30年后的今天,我身为两江总督,处理政事不能凭一己之好恶,一定要为金陵百姓恢复一个源远流长、大家喜爱的游乐场所,并重建一个人文荟萃、河山锦绣的江南名城。”
曾国藩对秦淮灯舫所抱的开放态度,对幕僚中的官员启发很大,最受教育的还是太守涂廉访。他撤销了原来的禁令,并采取积极措施,修复鸡鸣寺、莫愁湖、胜棋楼、扫叶楼,恢复了六朝旧迹,使龙盘虎踞的石头城再放异彩。
曾国藩不禁秦淮灯舫的举措,在金陵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时,各地商贩云集秦淮河畔,富商大贾携眷游玩,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
选择贤人委以重任,听其言而察其理。这两句话是曾国藩自认很难做到的。但他仍旧尽力而为,在选任用人上尽量做到宽容。
他在给好友的信中写道:“今年我在省里,在下辖的武职官员中特别赏识塔齐布这个人,实在是因为军营目前的风气不好,官兵们遇事退缩,行为虚浮,漫不经心,无所作为,骄纵涣散,如同撮合起来的泥沙不能当饭吃,令人又是叹气又是痛恨。获得一个像塔齐布这样热血澎湃、立志杀敌的人实在很难,因此我才倍加器重,屡加赞许。除此之外,我也缺乏可以信赖的心腹。
至于那些不受我肯定的人,则是人人对之斥骂唾弃。有些人想要混淆黑白,颠倒善恶,将大才、小才各种人才混为一谈,那么依着我这不够宽大的胸怀,对此实在不能容忍。造成今天整个社会的动乱,只因为人们混淆是非,万事漠不关心,才使得志士贤人灰心丧气,偷奸耍滑之徒得意洋洋。”
大凡居官为宦的人,仕途坷坎不平,身败名裂的不在少数,有的人甚至稀里糊涂就被免职罢官了。曾国藩总结古代高官失位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是四个方面:昏、傲、贪、诈。曾国藩家书中提到了四败:“昏惰任下的人败、傲狠妄为的人败、贪鄙无忌的人败、反复多诈的人败。”曾国藩认为要居官有成,就必须戒此四败。欲不昏惰任职,必须做到“明”,尤其是知人之明。只有知人之明,才能做到人尽其才;只有人尽其才,才能事业兴旺。曾国藩能文能武,在军中他可以预言谁可以为营官,谁可以为大帅,正如某人后来的表现验证了他的预言。如他保举塔齐布说:“将来如打仗不力,臣甘问罪。”后来,塔齐布果然屡建战功,后战死沙场。
曾国藩做事讲求原则,要求也很严格,但不管是多急多大的事情都能冷静。客观地对待,不以一时的情绪做事。他认为陈国瑞率军驻扎济宁,力量单薄,便把部将刘铭传派到济宁,驻守济宁城北的长沟集。陈国瑞性情暴虐,向来看不惯湘军,看到刘铭传军配备着先进的洋枪很是妒忌,于是产生了抢夺的念头。但他的方式过于激进,又杀人又抢夺,激怒了刘铭传,刘铭传把陈国瑞的士兵全部打死,还将他软禁。回去以后,陈国瑞恶人先告状,向曾国藩控告刘铭传,刘铭传也不示弱,两人就争吵起来。曾国藩对于陈国瑞的蛮横早有所闻,火并事件以后,对陈国瑞屠杀自己部下的行为十分不满,但在向皇帝的呈禀中,他仍客观地详述了陈国瑞的功与过,使陈国瑞受到了适宜的制裁。这样,陈国瑞不得不向曾国藩认错,并服从曾国藩的调遣。
曾国藩不仅对部下要求严格,而且能够做到以身作则,严于律己。他提倡节俭就由自身做起。做官的人,几乎没有不爱钱的,而曾国藩对钱就没有兴趣。曾国藩的日常生活极其俭朴,即使是女儿出嫁的大事,也才给压箱银子二百两,说到做到,未多放一两。儿子曾纪泽新婚,曾国藩谆谆告诫儿子,要求新妇亲自下厨做饭,并学习绩麻织纺之事。曾国藩一生廉洁自律、生活俭朴,官至一品总督,家庭生活与普通家庭无异。曾国藩30岁生日时,添制了一件青缎马褂,平日并不穿着,只有遇到庆贺或者新年时才穿一次,所以,那件衣服始终显得很新。
曾国藩做京官十多年,尽职尽责,鞠躬尽瘁。他在给父亲的家书中写道:
“对于衙门里的各种事务,现在都已经很熟悉,同事都很佩服我。和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我处理得很好。既然我现在在礼部衙门,就应当为国家做好自己分内的事,不敢苛求什么,也不敢懈怠,为国家尽心尽力地服务,才是我最大的心愿”。虽然这只是普通的家书,但是却反映了他严以律己的作风。
身为一家之长,一国重臣,对国家,他始终忠心耿耿,尽忠职守;对部下,他赏罚分明,管教有方;对子女,他教学相长,调理有方。曾国藩为人处事始终有自己的原则,因此,曾国藩不像历史上某些权臣,虽然权倾一时,但最终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既是名人就必有非议,功过是非自有定论。作为后世的人,要学会忆史思己,取长补短,这才是正确的学习观念。
3.靠自己渡难关
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在危难之际当然可以请求别人的帮助。
但是,无论何时,主动权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
俗话说:靠人不如靠己。危难来临之时,唯一可以依靠的人就是自己。
如果寄希望于别人,后果极其危险。越是危机的时候,侥幸心理越是要不得的。
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在危难之际当然可以请求别人的帮助。但是,无论何时,主动权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经过血的教训,曾国藩深知这个道理的重要性。
1862年5月,曾国藩率军在天京城南门外的雨花台扎下营寨。曾国荃和他的心腹大将李臣典、刘连捷、朱洪章等在太平天国的叛将韦俊的带领下,察看了这座江南名城。天京城高池深,城围辽远,想要轻取这座城池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他没有轻举妄动,而是一面督促湘军在雨花台一带修筑工事,做长期战争准备,一面派人投书,催促各路人马尽快会师城下。然而,曾国荃等了多日也不见别路人马到来。李续宜和鲍超都因各种原因难达天京,这时,可指望的援军只有多隆阿一路。
曾国藩接到雨花台寄来的加急求救文书,命多隆阿迅速南下。多隆阿接信后,开始还有所行动,攻陷庐州,准备南下,但突然按兵不动,拒赴合围天京之约。曾国藩再三恳请赴援,多不为所动。这时,有一股四川农民起义军入陕。多隆阿与湖广总督官文密约,再奏令多隆阿本人率队入陕,皇帝居然准奏,多隆阿借以不赴天京之援。事实上,多隆阿心里不服曾国藩,根本无心相助。
曾国藩因为没有援兵而有些乱了阵脚,派人飞马送信给官文,仍请将去之不远的多隆阿追回。然而官文明知天京城下急需多隆阿赴援,却置曾氏兄弟的求援于不顾,使曾国荃的雨花台之师成了孤军。通过这件事,曾国藩似乎发现了人性的弱点,也印证了他早已提出的危急之时不能靠别人的道理。
人心到底如何,只有在发生了事情的时候才能看得清楚。
曾国藩在1862年9月13日《致沅弟季弟》信中说:“都将军派四个营的兵来助守,自然可喜,但也未必靠得住。凡在危急时刻,只有自己靠得住,而别人都不可靠。靠别人防守,恐怕临战时会先乱;靠别人战斗,恐怕会猛进而速退。幸亏这四个营人数不多,或许不致扰乱弟弟你那里的全局。否则,这部分军队另有一种风气、另一种号令,恐怕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弟弟要珍惜小心地使用这支队伍,把尺度拿捏好。去年春天,弟弟没要陈大富一军,又不留成大吉一军,我很喜欢弟弟的见识”。
经过这次惊险之后,曾国藩认为,危急之际不要靠别人,专靠自己才是稳招。
成丰五年(1855年),自从罗泽南等离开江西以后,曾国藩在江西的处境堪忧。在这种危急时刻,曾国藩认为首先要“自救”。在内湖水师缺乏一位得力的统领,几位营官也都是平庸之才的情况下,曾国藩只好让李元度兼辖水师事。
曾国藩不断地给李元度写信,教他如何带勇、如何列阵打仗。信函中,需要注意的事项一一列出,反复叮咛。但写了这些,曾国藩仍然不放心。他想起上年写的《水师得胜歌》在军中影响很好,既通俗又实用,便再花几天的工夫,写出了一首《陆军得胜歌》。歌中讲到了湘军陆师在扎营、打仗、行军、法纪、装备和训练等6个方面所应注意的事项。
尽管曾国藩如此苦口婆心,但李元度仍然不能将他的陆师部队训练成能战敢战之师。曾国藩寝食难安,预感很不好。在陆师方面,湘军在江西的两支主力的统领周风山和李元度也都不很出色。曾国藩花在他们身上的心血很多,但还是不放心。因此,曾国藩在自救的同时,不得不求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