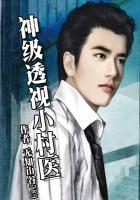“那个小伙子醒了没有?”一袭青衫,手抚折扇,看似瘦弱的书生柔和地问道。
“已经醒过来了。他身上的毒,已请宋大夫给他诊过了,无大碍。”书生身旁,一位美貌绝伦的年轻女子说道。
“嗯,这次行动,有劳你了。”书生模样的人说。女子微微低头,半晌,叹道:“那么,你是开始了对吗?”
周夫子右手举扇,眉宇间有英朗坚硬的气息在凝结。他望着庭院里的春日的芳草怔怔出神,一直过了很久很久,用一种风轻云淡,却无比饱满的语调幽幽地说:“开始了。”
西山医阁,东厢房。
彭辉这才醒来,眼力还不甚好转,只觉头昏目眩。一时迷茫,不知眼前为何地。然而神志已经清醒了许多,身体中的痛楚,也亦解去了些许,已不是那么苦痛难忍了。他恍恍惚惚地忆起在悠长的巷道中被黑蛇一般的女子袭击之事,而当自己就快要死去时,不知是哪位女子出手援救,把自己一下子提到了马背之上..
正想间,东厢房的门扉被轻轻推开,一束温暖的阳光射将进来,徐徐照亮床沿。迎着阳光,他看到一男一女两个身影。
“彭大人,今日可有好转?”这是彭辉听到的第一句话,温和、饱满、坚毅。一个书生模样的人走进东厢房,微笑着面对自己。
彭辉脑海里一震,陷入了沉思。这样的场景,在自己童年时代的某个黑暗阴冷的记忆里,也曾有过,是那样熟悉。当年之人之时之地,依稀也是眼前这般模样。转念一想,其人早已死却,过往矣。眼下的自己,不过只是因眼前展现的熟悉一幕,浮想起内心深处的场景和物事,感时伤神,平添愁绪罢了,念及此,不禁轻轻一叹,为光阴、为故人。
“大人是不是还有哪里不舒服,我再请宋大夫过来。”周夫子看到彭辉在发呆,连连叫了他很多遍。
彭辉登时反应过来,连忙回答道:“彭某好多了,不知此地是?”方才错愕间的溯往,真是有如梦幻,却又无比真实。
“西山医阁。是潘玲姑娘救了你。”
彭辉听后,目光转向书生身旁的那位貌美女子,其人亭亭玉立,五官俊秀,玲珑的身材,白皙均匀的肤色,当真是世间鲜见的美女子。一时有些哑然,艰难地从床板上立起身子,拱手弯腰道:“承蒙潘玲姑娘救命之恩。在下感激不尽。”潘玲走上前去扶他躺下,说:“现在不能乱动,你体内的毒素还未消却,若是死了我们可救不了。”彭辉点头言谢,又转向书生模样的人,“那先生是?”
书生坐在茶桌旁,轻摆折扇,说道:“在下周夫子,乃一行走江湖的文士。在这东都摆点摊子卖卖药草罢了。无足挂齿。”
彭辉听后,登时明白过来,拱手道:“原来是西山医阁周阁主,失敬失敬。阁主悬壶济世之名,长京大理都是家喻户晓的。”
周夫子用折扇轻拍额头,说:“相识一场,自是缘属。既然是朋友了,客套话语也就免却吧。繁文缛节,乃是你们朝中之人的琐事,在周某之所不需有。以后我叫你本名,你叫我本名便是。我虽读得经阁半卷书,不懂医术是真。能开得这家医阁,全是仗着几个朋友的能耐,混口饭吃罢了。”
彭辉应允道:“先生真是过谦了。能交到先生这样的朋友,也是彭某荣幸。”他晃动了一下身体,觉着有些松软,然而毕竟为修武之人,自己也能感觉到周身的毒素已然散却,实无大碍,心下越发感激莫名,说道:“彭某承先生恩德,不知以何作谢。”
周夫子把扇子一折,浅浅一笑,“彭兄言重了。小潘姑娘也是恰逢路过,不忍心见到这东都的小巷被鲜血沾染,才路见不平,相助罢也,彭兄不必再多思酬谢之意,这样的小事,亦是周某等当为之。”
彭辉正准备继续诉说言谢之词,突然想到了一件要事,“不好,公主殿下.。。”说着便欲再起身,不料目前一黑,险些跌将下来。潘玲连忙稳住他,说道:“你身体还尚未痊愈,切不可轻举妄动,阁主还需兑药于你,再行些医治才是。”
“不行,我得去羽朱宫护驾。那杨牟利府上的兵卒是唐..”才脱口,又不免犹豫了,毕竟自己对这位周夫子还未算得上深识,若要再说下去,恐怕不妥。
周夫子眉眼一蹙,思量了一阵,似乎明白了什么,径自说道:“彭大人现下不能离开周某之所半步。当然你也不必担忧。你所说的那些兵卒其实都不是唐国军队,而就是杨牟利自己的下属。而那个万花公主,安然地在羽朱宫中,凤体无恙。”
彭辉听后略为惊讶,问道:“先生竟然都知道这些?”
周夫子说:“这有何难。你初到东京,对杨牟利府前守卫之人并不熟识。而我每天都在这东都之中,穿街走巷,自然认得杨牟利府上有哪些个兵卒。羽朱宫里的人时常会到我阁中取些日常药草,安插几个线人在那边做内应不是什么难事。今早我已得到了线报,万花公主一切安好。而且,万花公主向来不问政事,我想她也许根本就不知道东都这几日发生了什么。你若果贸然闯进羽朱宫,倒是真的很像一名刺客了。所谓唐军进驻了杨牟利的府邸,不过是你自己的臆想而已。”
凭借自己多年探查案件对别人说话时语气的甄别经验判明,这位周夫子那温和坚毅的言语不像是谎辞,一时间倒也平生了对他的几分信任。心内的紧张情绪竟然也松了一些,可还是不解地说:“先生也许不知。这兵卒驻防队形之样式,乃是兵法严令,任何人不得随意更改。否则可是触怒龙颜之举。杨牟利身为统兵大奖,自然不会犯下这样的错误。在下只是以为..”他顿了顿,还是说道:“时机恰逢大唐节度使来访东都,却出现了这样的异常,不符合将军府的常理,正是这样一个细节,让我怀疑兵卒变换驻防队形一事,乃唐军借机乔装进驻东京,欲图对公主行不善之举。既然不是唐军,那杨将军又为何要?”
“彭兄说到点子上了。”眼见彭辉还是一脸迷茫,周夫子说:“在下有几句话,真不知当讲不当讲。”
彭辉说:“周先生但讲无妨。”
周夫子沉吟,徐徐站起身子,微微地摆扇,“彭大人对南诏国的忠诚,实属可贵。可是这份忠诚在乱世又算得了什么,无非就是被奸人利用的棋子罢了。”
彭辉瞪大眼睛,问道:“先生,何来奸人利用在下一说?”
周夫子略略一叹,沾了一口茶水,差遣潘玲走出门去,把门窗关好。续说道:“奸人是你的那位师父,大理寺卿郑买岑。你不过就是他手中的一颗棋子罢了。”
“啪”一声,彭辉一掌拍向床板,厉声说:“先生救我,彭某自知大恩难报。可是,先生又为何,出口污蔑家师!”
周夫子倒也不生气,徐徐说:“彭大人,你别着急。见了这个,你就不得不信了。拿进来。”
潘玲又走了进来,这一次,手里却拿着一张纸。“打开给他看。”周夫子对潘玲说,潘玲点点头,慢慢展开纸张。这赫然是朝廷缉拿重犯的通缉令,仔细一看,那个被通缉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眼下,他的人头已经被悬赏到了四百两白银。彭辉只觉天旋地转,而最令他感到悲伤的是,通缉缘由是彭辉与逆党郑买岑合谋行谋逆公主之举。一时间,他整个人怔在当场,说不出一句话来。
像是经过了几个世纪,彭辉才幽幽地道:“周先生,你倒是说一说,家师何以会陷害于我..”
“彭兄先请不要难受。请你认真答复在下几个问题。你身上为何有先皇的黄纸钱?”
“是师父两日前亲手交给我的。他说,我是大理寺纠察使,随时都要代天子正君威,而铲奸除恶就得身犯险境。有黄纸钱在手,有如先皇亲临,至少可以有所助益。”
“你师父身为大理寺卿,朝廷正三品大员,更是从先皇开始便倚重的重臣。难道这样一个重臣,会不知道私自授予他人太祖皇帝的黄纸钱这样的行为,是欺君罔上之举吗?”
彭辉无言以对。周夫子接着说:“如果皇帝察觉,怪罪下来,他担得起这个蔑君的罪名吗?当然不行。那他为何敢于这样做?因为他根本不用去担这个罪名,而是你,来替他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