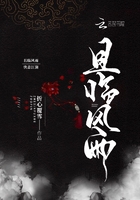“皇上呢?”水烟和紫音卷系流苏帐,乐滋滋说道:“回娘娘话,皇上走了好几个时辰呢。”
皇后命人更衣,责怨道:“你们也不提唤本宫起榻,好伺候皇上更衣。”
紫音忙说道:“是皇上不教奴婢们提唤娘娘,皇上说娘娘昨夜侍寝辛苦,让娘娘多睡几个时辰,不必起早送驾。”
紫音说这些话时,皇后正握着紫玉银面萄葡落地靶镜,瞧见镜中的红潮春波,想想自己昨夜的情形,又是羞恨又是甜饴。
“娘娘,今日的梳妆有什么吩咐?”眉心用黄松琥珀梳为皇后梳理垂鬓,玉棋亦来抱着好几件衣裳询意。
皇后端坐于妆镜前,款款而道:“昌婕妤有孕在身,心绪躁乱,本宫去看她不宜浓妆盛服,打扮轻便些罢。”
因怕昌婕妤与其他妃嫔起纷争,所以绮霞宫是离尘宫之后第二路途遐远的椒殿。好在绮霞宫一带的花木大多由外邦边番进献,亭台楼榭也是宫匠们照着异域风情建造,路长景秀,皇后坐在撵上也不致太无聊。
行至油绿繁茂的醉香含笑,忽闪过一只黑毛绿眼猫,着实把人骇得够呛。
侍撵姑姑急忙叫停,眉心,水烟等人匆匆前看皇后安好,好在抬撵太监经历老道,没有惊吓得把皇后颠倒。
皇后拍抚着胸口,闭眸言道:“不过是只黑猫,没什么要紧,还是趁午前快到绮霞宫。”
侍撵姑姑持歉禀说:“请娘娘担待些,自得知昌婕妤主子身怀皇嗣,太后娘娘便下懿旨,命内侍监带宫匠翻修绮霞宫并周围的景样儿,好让婕妤主子住得舒心畅意。这人来人去的,保不定有什么东西跟溜进来。”
“到底是太后娘娘,比我等思虑得周到妥怗。”皇后嘴上说得敬服,心里不免敁敠,闷自说道:“太后又要使什么计量?方才的黑猫若不是巧合,难道是……”
越想越觉得危殆,皇后催抬撵太监快行,直至催到绮霞宫宫门。
“启……启禀主子,”传事宫女避挡昌婕妤抛扔的御赐器物,嗑不成句,“皇……皇后娘娘驾……驾到。”
“嫔妾给皇后娘娘请安。”幸昌婕妤及时住手,皇后才没被周鼎抛伤。
“既有了身子,不要讲这些虚礼,子嗣为重。”皇后亲身搀抬昌婕妤起来,且扶她躺到榻上。
昌婕妤看皇后为自己铺褥盖卧,很受所感,鼻子酸涩,扑落下泪珠:“绮罗一个异族番人,父母族人不在身边,脾气不好,性子又倔,在这皇宫里头孤伶无靠,能得皇后娘娘的关切照顾,是绮罗几世修来的福份,等绮罗死了,下辈子必当给皇后娘娘做牛做马,报答皇后娘娘待绮罗的大恩大德。”
皇后忙轻声喝住,说道:“都要做母亲的人,还死啊活咧不离口,你不忌讳,本宫还为你肚子里的孩子忌讳。”
昌婕妤看着身腹,冷冷自嘲:“是啊,谁都是为了我肚子里的孩子,皇上是,皇后娘娘是,太后娘娘是,紫微城的上上下下都是,没有了这个孩子,我野利绮罗便是一文不值,都不如马厩里养的马驹。”
“妹妹万不能这么想。”皇后略侧盘髻,对宫人说道,“你们都下去罢,本宫要单独和昌婕妤说话。”
“是。”阿那带头出去,并将房门关掩好。
皇后端正衣裙,挨坐榻边,对昌婕妤说道:“妹妹可知我们中原妇人讲究的‘三从四德’?”
“嫔妾听阿爹提过。”昌婕妤对此没什么兴致,但诚敬回道,“是专来管束汉妇的训条:三从是没嫁人听阿爹的、嫁了人听丈夫的、丈夫死了听儿子的;四德是妇人要讲究自己的品德、辞令、仪态和女红。”
皇后蔑然而笑:“妹妹说的不错,不过,这‘三从四德’不是管束女子的训条,而是男人们可怜女人,留给女人的活路。”
昌婕妤面显惊讶,立直身背,睁大睛瞳:“娘娘说的是什么意思?”
皇后将她腾掀的被角抹捋好,复细细言道:“其实,不论在中原,还是在西羌,女人都是男人们的玩物,喜则用之,厌则弃之。妹妹如不信,可以想想,不用想得过远,你自己便是个例子。”
皇后说到这里停顿片刻,直视昌婕妤,昌婕妤避开皇后的眼神,没气力似的勉强道:“皇上贵为天子,是君王;我们西羌子民倚附大玄,是臣子。无论臣子做什么事,都要听君王的。”
皇后转容,看着满室狼藉,放重话音:“倘若妹妹真晓得何为君何为臣,就不会这样弄性尚气,跟皇上嚣闹。”
昌婕妤怒火窜心,几乎窜上天:“嫔妾虽晓得君臣的道理,可皇上也太看轻嫔妾,嫔妾好歹是个番国的——”
“如果妹妹是个男人,”皇后打断她的话,“妹妹觉得皇上会看轻妹妹吗?皇上待妹妹的父亲兄弟,会跟待妹妹一样吗?”
昌婕妤被驳得哑口无言,只能耷拉着脑袋闷不作声。
皇后平静而恳切说道:“我不想跟妹妹讨说君臣大道,在皇宫里面,君臣大道不过是男女欢爱的遮羞布。女人是要靠男人才能活在世上,不论市井乡野的民妇,亦或深宫内苑的妃娥。只不过像我们这些人,好似百尺危楼上的笼中雀,注定是要比别的女人活得辛劳痛苦,所以要比别的女人愈会利用‘三从四德’,才能在这皇宫找条活路。而妹妹你,如今占了‘三从四德’中最有用的一条,却不自惜,绝非明智,甚可说是糊涂。”
昌婕妤抬起头,神情肃然紧绷,皇后继续说道:“我方才说女人要靠男人才能存活世间,‘三从’说的是在什么样儿的时候靠什么样儿的男人,‘四德’讲的是为了靠住男人而如何使手段。未嫁从父是靠父亲为自己撑腰,从而嫁个自己合心的丈夫;既嫁从夫是靠丈夫对自己的眷爱,从而抚育出自己后半生的依靠;夫死从子,丈夫对自己而言,人死也好,心死也罢,反正自个儿膝下有子,便不再在乎那点子宠爱。甚好者,是能有从自个儿肚子里爬出的孩儿,血脉相连,心意相通,自己受多大的委屈,亲骨肉为亲娘心疼,总比别人的虚情假意强百倍,强千倍。妹妹想让皇上看重,就必须生养出儿子,有了儿子,不仅受皇上看重,自己也会看重自己,为了自己为了儿子,才不会任性胡闹给别人看笑话。太医和稳婆给妹妹相过身子,妹妹这一胎定是个小皇子,如若妹妹能够安安分分地养胎育子,妹妹便能在这深宫内苑,稳稳当当地活下去。本宫言已至此,望妹妹能领会我的良苦用心。”
昌婕妤头一回用做母亲的心情,打量摩挲着自己的腰腹,而后迎着皇后的目光,决然说道:“娘娘放心,嫔妾已经明白自己该怎样做了。”
皇后察度昌婕妤的言语神情,心放下了一多半,转而命盈瑞堂的宫人进来,敲敲打打地训诫,盈瑞堂的宫人俯首贴耳,没有一人显露出不谐。
皇后又独招阿那训教,皇后倚着案角问道:“你跟了你主子几年?”
阿那依汉礼回说:“回娘娘的话,阿那自六岁起,便贴身伺候我们主子,如今整有十年。”
皇后接着问道:“这里只有本宫和你两个人,你要如实告诉本宫,昌婕妤待你如何?”
阿那忙道:“我们主子就是脾气不顺,性子倔强,可刀子嘴豆腐心,虽说时常责骂我们,但也每每给我们赏赐和体面,比别处的丰厚很多。”
“你既跟了昌婕妤这么多年,”皇后收回臂袖,矜重地说,“本宫看你也是个灵透丫头,有些话没法儿叮嘱你主子,只能叮嘱你,你要提起一万分精神,给本宫听仔细。”
“恳请娘娘吩咐。”皇后覆袖嘱道:“你们主子身怀龙嗣,不管是谁都会对你们主子虎视耽耽,你身为昌婕妤的近身掌宫,眼睛心思要比别的宫侍更发亮敞,要通察清晓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绝不能出一点差子。若岀了一点差子,不用本宫讲,你也知道后果有多可畏可惧。依宫礼,自会有嫔妃和管事送东西,不论送来何物,不论昌婕妤喜欢与否,你都要收在挨不到昌婕妤的地方;昌婕妤有了身孕,食物必须倍加留意,衣妆必须倍加小心,香薰在孕时必须忌用,本宫亦会诫告御膳房,内务府和侍香居;昌婕妤孕时发生的大事小情,你定要斟酌处理,哪怕是牵扯到皇上,太后娘娘,乃至本宫,亦要慎裁。”
阿那郑重作礼,应诺道:“奴婢牢记娘娘教诲,不敢擅忘一言一句。”
皇后又嘱咐道:“本宫上嘱所语,皆是大体,还有一些细密事,不能明嘱。”遂命阿那近前,附耳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