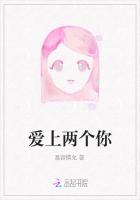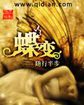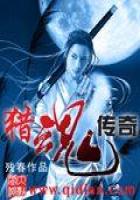一
上海解放后,为了尽快恢复市政建设,恢复生产,支援人民革命战争,争取全国胜利,上海市军管会立即公布了在未制订新办法前原有各项国税、市税仍暂继续征收的布告,沿用旧制征收各税。
以后,上海市人民政府财政局、上海市货物税局和上海市直接税局建立后,在修正原有征税规定的基础上,结合上海情况陆续制订了上海单行的税收法规,主要有:印花税、屠宰税、车辆使用捐、娱乐税、营业税、船舶使用捐、房捐、营业事业所得税等暂行征收办法,均由上海市人民政府于1949年6至11月先后公布实施。在此期间,废除和停征了“一切所得税”、“车辆市政建设捐”、“汽车季捐”和“土地增值税”等十五种税捐。在货物税方面,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财政部于1949年9月颁发了《华东区统一货物税税目税率表》,上海市按此表征收。
一开始,在当时上海财税工作就出现了两种税收方法之争:一种是中央财政部推行的“民主评议”(其实只适应于刚解放不久的中小城市);一种就是顾准主张的“税收专管”这一符合现代税收制度的做法,其核心是:“专管、查账、店员协税”。因为在顾准看来:“进入上海以后,货物税(纸烟、棉纱、火柴等轻工业产品的出厂税)照旧章征收,没有什么困难。营业税、所得税两者是否采用民主评议办法,一开始我就持有疑问。上海大厂商多,账册‘健全’,早在三十年代国民党政府开征所得税时,资产阶级就在学习在税法范围内和国民党政府作斗争(我在三十年代的潘序伦修改的那本《所得税原理与实务》,事实上就服务于资产阶级来进行这种斗争的)。”
顾准心里明白:“我们如果在上海搞民主评议,只能有二种可能的结果,一是征税实额低于税法规定的税率,这会使资产阶级占尽便宜。二是征税实税高于税法规定的税率,这就会变成‘摊派’。民主评议首先要我们提出应征税收总额,再层层派下去,这个应征总额怎样定法,实在摸不到底。又民主评议评到户,要经过各业同业公会。上海工商户如此之多,一个行业的同业公会内有势力的资本家可能占便宜,不占势力的可能吃亏。更重要的是,这种税收方法因其必然完全脱离税法规定,它可以保证完成税收任务,可是绝不能使税收成为对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限制反限制的斗争的武器。”
可见,正因为“民主评议”不符合税收法规,也不符合上海的实际情况,上海工商界的实际情况正如顾准所言,会计基础好,账册一般比较健全,完全可以依率计征,按照税法纳税,同时上海有强大的工人阶级队伍,可以动员他们来协助监督,防止偷逃税的行为出现。据此,顾准在税收工作上敢于直言,提出不同的意见,并且勇于坚持真理,当然也不是为了一己的私利。
这场争论因为涉及与中财部的意见相左,当然惊动了市委。据陈敏之介绍,市委(还有华东局)曾不止一次讨论过这个问题。1950年8月陈毅在去南京军区前夕,曾专门找潘汉年和顾准到他家讨论这个问题,陈毅同志的结论,毫无保留地要废除民主评议,采取“自报、查账、店员协税”的方法。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市委和陈毅同志的支持,顾准的正确主张是不可能付诸执行的。
这场争论当然也传到了中央。1951年12月,中财委主任陈云同志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指出:上海税收方法争论中,“顾准的方法是对的”,这个意见还得到毛泽东主席的肯定。已故的解放初期上海税务局副局长朱如言生前曾亲口对陈敏之说过类似的话,他告诉说陈云认为税收方法之争,“直在顾”。
按照顾准的税收方法,1951年3月税收实绩1.8亿元,较1950年增加6倍;1952年3月,入库税收3亿元,较1950年增加到10倍。1950年“二六”轰炸以后,上海工商业一度萎缩,1951年的税收增长,可视为工商业恢复的反映;1951年至1952年上海工商业已恢复正常,税收的增长明显高于经济的增长,应当认为这与税收方法的科学性以及采取有力的组织措施(根据顾准的建议,市委已批准各区设立区税务局和按地区设置税务专户专管员等)有关。
上海解放初期,根据中财部的指示,采用的是“民主评议”的方法。有着丰富会计实务与税务知识的顾准一开始先是“持有疑问”的。故而就在旧直接税局接收不久,他就采纳了吕若谦建议的营业税“自报实交,轻税重罚”的办法。据顾准回忆:这年“六月份,饶漱石找我谈了一次话,谈话中我提出,上海工商采用‘民主评议’方法恐怕不行,饶表示同意,并赞成采用‘自报实交,轻税重罚’方法。”饶漱石当时是上海市委书记,顾准得到他的支持后,便于6月在上海直接税局修改国民党时代的营业税率(国民党统治时代,逃税愈多,税率愈提高,税率愈高,逃税愈厉害,形成恶性循环),减轻旧税率约30%至50%,上报上海市委批准公布。
这样,第一期两个月内上海市的营业税由各户自报实交,征税实绩比国民党统治时代高出了好几倍,这还是在旧税务机构尚未完全改造、店员群众还未完全发动起来的情况下取得的。所以,顾准以此方法作为过渡时期的临时办法,然后进行税局的根本改造,彻底杜绝偷税、漏税。
在1949年底前,在顾准主持下,由直接税局公布了一批“特约查账员”,帮助深入企业查账纳税,办理税务代理业务。
顾准在上海公开执业的会计师中,挑选了二十几位人士由税务局聘为特约查账员。私营企业报税时,凡经他们查账、出具证明的,税局可以大体信任其可靠,但也不赋予税局不再查账,亦即逃税漏税者不予处罚的保证。对此,顾准先口头请示了陈毅,得到他同意后,即予公布。
当时受聘担任过“特约查账员”的诸尚一(1913—1997,建国后曾任民革上海市委副主任,市政协委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主任会计师),劫后余生,他以亲身经历告诉人们:
我与顾准同志在上海解放前本来并无交往。解放后,他出任第一任市税务局长,忽然于1949年约11月间,柬邀我去参加一个税务工作的座谈,这才开始相识。
刚入场,顾准同志看到我的签名,脱口就叫我:“尚公,欢迎你!”一下子就把我闷住了——素不相识,他怎么会以此称呼?“尚公”是我解放前供职《商报》时所辟专栏《尚公说法》用的笔名,由此有些熟人就以此相称,既带有尊称的性质,也是一种所谓的“爱称”。所以,于不意中竟然听到顾准同志这样叫我,顿时从心底里涌起了一股暖流,感到分外亲热,从此奠定了我同他的同志式的友谊。他这次之邀严谔声和我,是由于我们俩在解放前曾运用上海市商会的关系,长期代表民族资本家的利益,同当时国民党政府的上海市直接税局打交道,对旧的税制有一定的了解,在今天有可以借鉴之处的缘故。
就在这次会后,大约是在1949年底1950年初的交界期间,陈文麟同志邀我到顾的家里去。陈文麟同顾准都是潘序伦先生的学生,又是潘先生创办和主持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和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的同事,所以,由陈来邀我。其实,事先我已风闻,顾为了课征1949年度的所得税,深感税局干部力量不足,所以想聘请若干位老会计师担任市税局的“特约查账员”。在那时,会计师究竟怎么定性,不仅社会上议论纷纭,就连会计师界人士亦是心中七上八下,莫衷一是。所以,“特约查账员”这个桂冠,无疑就引起了会计师界不少人的关注,能轮得上戴当然好;戴不上,也至少可以证明会计师是能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果然讨论的中心正是此事。
在诸尚一的回忆中,当时顾准从一开始就特别重视人选问题,一再强调政治因素,要求宁缺毋滥。经过一再筛选,最后提出了十几个人的名单,其中包括陈文麟、李文杰、李鸿寿、汪诒和张更生等,这些人大多是立信的资深教授,同时也把诸尚一列了进去。
对此,诸尚一认为自己不能说一无思想准备,但坦率地讲,他又无志于斯的。因为:第一,他很忙,无暇及此;第二,他自感只会“说法”,对查账实务并没有实际经验。所以,当天在后半场,就几乎成为劝驾出山的会议。顾准更是坚持要他参加,他也就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诸尚一后来回想起来,“顾准同志何以厚爱于我?大概是我的《尚公说法》,在国民党统治的黑暗时代,还多少在客观上表现了有那么一点正义感,从而他站在党的立场上,执行了不忘记对人民做了好事的人政策吧?”诸尚一的感叹是发于内心的。
通过税务干部的努力和利用社会力量,顾准带领财税干部圆满并且超额完成了上海当年的税收任务。
二
1950年6月6日至10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并作了《不要四面出击》的重要讲话。毛泽东在前述的报告中说:“我们现在在经济战线上已经取得的一批胜利,例如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货停止膨胀和物价趋向稳定等等,表现了财政经济情况的开始好转,但这不是根本的好转。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
这次全会决定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上海的陈毅等参加了会议。
与此同时,中央还召开了第二次全国税务会议。出席对象既有各地各级税务工作人员,也有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顾准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旨在贯彻“调整税收”的总方针,很少涉及专门业务问题。故而会议期间,单独召集税务工作人员开会的次数不多。在顾准印象中,这次会议以后,直到“三反五反”为止,中财部从来没有提出过反“左”中要防右的问题。
为了贯彻上述两个会议的精神,上海市委采取措施,加以落实。在该年7、8月间,成立了直属市委的党的税务委员会,负责人由潘汉年副市长兼任,参加的除顾准本人外,还有各主要工商业区的区委书记和其他有关的党员干部。任务是监督税务工作,协调税务涉及的各方面关系。在这个委员会的推动下,由顾准创办的《税务通讯》发表了数篇社论,要求税务工作人员严格“依率计征”,贯彻税法要体现“合法、合情、合理”的“三合”精神。不久,这个委员会被撤销。
作为调整税收的一种措施,各企业的营业税采用民主评议的方法,由税务局派出五六百名工作人员,在副局长王纪华率领下移驻上海市工商联,与工商联秘书长胡子婴、副秘书长马龙桂一起组成“民主评议委员会”的工作机构。然后分别和各同业公会一起,民主评议各业内各户的应纳税额。据顾准回忆,用民主评议方法征收的营业税大约不超过三期六个月,后两期,专户专管其实已经全面实施,民主评议愈到后来愈流于形式,9、10月份,就正式停止了“民评”。因为所得税以一年为一次征收期,半年估征是预征性质,以年底结账时的利润为根据计算全年交税额,所以这次“民评”估征,对全年所得税征收实税是没有影响的。
在调整税收过程中,顾准发动进行了一次纳税户大普查。用顾准自己的话说就是:“完成纳税户普查,实行地区性的专户专管。这样,全市无论什么地方新增或减少一户工商业户,税务机关都可随时掌握。”表面上看,这次普查的缘由是对营业税的征收方式从“自报实缴”改为“民主评议”而做准备,实际上它为建立符合上海都市特性的“税务专管制度”奠定了基础。事实上,顾准倡导的“税务专管”制度一直沿用至今,并且推及全国。
为发动全体税务干部重视这项普查工作,顾准在局内刊物《税务通讯》第七期上发表了《做好普遍调查工作》的文章。他首先回顾了过去因实行营业税“自报实缴”产生的弊端,指出“自报”必须以专管制度为基础,“自报”必须把纳税人组织起来,必须对纳税人的会计记录和发票进行管理,这样的“自报”,加上查账,才能“实缴”。
顾准为了这一工作的圆满完成,与广大税务干部开展了如下工作:
一、制订普查方案,组织千人调查大军。据1949年的统计,全市有私营工商业纳税户十三万户,还有摊贩十万户。面对如此众多的纳税户,如何管理,如何开展民主评议,必须采取适当的方式。当时曾提出了三个方案:第一,分业评议,分区管理;第二,分区评议,分区管理;第三,分区管理,分区分业评议。但不论采用哪个方案,都必须按地区查清纳税户数,因为民主评议是按同业公会的系统进行,而纳税户参加同业公会的仅占四成,所以要同时查清每个纳税户是参加哪一个同业公会的,没有参加同业公会的也要确定其主要经营的行业类型,还要了解每个纳税户近期的缴税情况和经营情况,供民主评议时参考。
内容多、任务重、时间紧,是这次普查的特点。为了保证普查如期进行,这次普查工作得到华东局财经委员会和华东税务管理局的大力支持,从华东税校抽调四百人,从海关抽调三百人,加上沪中区稽征处和局机关各业务处室抽调的四百多人,组成了上千人的调查大军。
顾准还决定,在市税务局成立调查工作委员会,由他本人领衔,各区设分会,以下再分为若干个小队和小组,为普查的顺利完成起到了组织保证作用。
二、讲究方法,注意态度。这也是顾准所十分强调的。时值上海解放初期,工商界对税务部门存在很多疑虑,特别是一些小商人怕税务人员上门,怕查账,怕受处罚。早在1949年8月,市财政局也组织过一次核对税卡的调查,发现市中心区的大楼里设有很多“申庄”(即外地工商户驻上海的机构),一个门口挂着好几个牌子,看见调查人员前往,就纷纷把招牌拿掉,装作住户。所以,在这次大普查开始时,顾准主持调查工作委员会开会,专门制订了必须注意的事项,要调查人员讲究工作方法,多向调查对象宣传解释,消除对方的顾虑。如果遇到商人在做生意,就要耐心等候一下,或者约时再去。商人怕填资本额,也不要硬性强填,以防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即使受到抵制,也可暂时退出,允许对方考虑之后再填。由于调查人员的积极工作,只用了一个多月时间,便完成了全市十多万工商户的普查任务。
这次普查,共查出遗漏户21000多户,减除歇业和待销户数,实际控制的工商业纳税户数为107830户,具体的经营行业有四百四十三个,其中工业户占14.6%,商业户占85.4%;还掌握了各个行业的一般经营规律,为分区分业开展营业税的征收创造了条件。
三、根据普查结果,在顾准决策下,建立九十六块“专户”管理区域。1950年7月,在普查的基础上,顾准召开市税务局局务扩大会议,决定实行“分区分块的专管制度”,着手对纳税户的专户管理进行分工。把全市两千家纳税大户划归市税务局的稽核处管理,它实质是“大户管理处”;对其余众多的中小户则分区分地段划归税务分局的稽征组专管。按照当时的行政区划,建立二十个市区税务分局,它们是:黄浦、老闸、新成、江宁、普陀、静安、长宁、徐汇、常熟、卢湾、嵩山、蓬莱、邑庙、闸北、虹口、北四川、提篮桥、榆林、杨树浦等区分局;以及十个郊区税务分局:杨思、高桥、洋泾、吴淞、龙华、真如、江湾、大场、新泾、新市等。
顾准等人通过研究,还拟定在二十个市区税务分局中设立九十六个稽征组,也就是开始将市区的十万个中小纳税户分成九十六块,实行区域管理。当时每个稽征组管理上千家纳税户,于是又按街道地段划分为若干个专管段,每个专管段至少设一名专管员,担负一百多个工商业户的征税事务,同时要调查了解纳税户的变动情况,处理开业歇业的税务问题,以及联系职工群众,开展职工护税工作,便是顾准倡导的上海税务专管员责任制的开端。
从上述叙述中,不难体会顾准的做法初步构架了现代税收制度的雏形,其中独具匠心的创造性工作,是值得后人珍视的。
在税收调整时期,顾准批准成立了税务稽查队,其任务为从海关、铁路、市场搜集报税、货运、成交凭证,分发各分局,用来核对有关工商业账册。倘有单据而不入账,就是逃税,这样,便于专管人员随时进行查账;还征收无固定营业地址的行商税。
由于顾准工作出色,得到了陈毅的充分肯定。1950年8月,在一次专门的会议上,陈毅明确指示要实行“专管、查账、店员协税”的征税方式,给顾准以极大的支持。顾准以为:“从此以后,上海税收工作才开始纳入了正轨。”
“店员协税”是顾准在调整税收过程中,平衡各方利益,巧妙地提出来的,充分体现顾准领会对私营工商业“限制、利用、改造”的精髓。所以,当顾准代表上海市税局向市委提出“店员协税”问题时,市委立即批准了这个请示。于是,市税务局会商上海店员工会。该工会积极响应市委号召,组织了“协助税收委员会”,分业分地段动员会员参加协助税收工作,有效地防止了逃税漏税行为,为稳准狠地打击少数违法纳税户创造了条件,也为1952年店员大规模参加“五反”运动作了准备。
1950年9月,鉴于各区稽征组和市局稽核处专管户的基层组织已经普遍建立,店员协助也已实行,“民主评议”名存实亡,“专管、查账、店员协税”这一套办法已经初步贯彻实施,顾准决定,市税务局召开第一次稽征组长会议。会上挑选若干工作较好的稽征组作典型报告,用具体的例子来表明稽征组应该如何工作,对于推动全局工作起了一定作用。这次会议以后顾准的全部工作转向次年3月征收的1950年所得税的准备工作上,关于所得税法,向税务总局提过一些建议,派人出席了中央税总的专门会议,从工商联抽调回来的五六百税务人员,配备到需要的地方;为了统一计算利润的标准,和上海工商联及各业同业公会进行了一系列的协商;通过协商会议宣传税法,在税务内开展了必要业务知识的学习和政治动员等等。经过这些准备,1951年3月,包括所得税在内的全部税收实税记得是旧币一亿八千万元值,为1950年3月税收任务的六倍。
显然,采用了顾准的“专管、查账、店员协税”的征税方式,才取得了如此税收实绩。这些收入,大力支撑了国家的各项开支,并有力地支援了正在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
顾准办税有主见,有魄力,又善于利用调动社会力量,为了确保财政收入的足额完成,他确实殚精竭虑。据李鸿寿时任私立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校长)回忆:
1950年底将放寒假的时候,顾局长打来电话,说今年开征所得税,税务局要抽查部分工商企业账目,感到人手不足,打算利用大专院校会计学科高年级学生寒假期间帮忙。我表示赞同。这对学生是极好的实习机会。他要我与有关院校联系。他自己则与高教局联系。结果,各方一致赞同。
一天,税务局同志打电话来说,定于某日下午在中州路前上海商学院礼堂,集合实习生开一次会。请顾局长作动员报告,请我主持会议,讲讲实习的要求。这天到会的人非常踊跃,动员报告后立即编组,并定期在税务局报到,每人发一本《查账须知》小册子。这次实习,各方面都表示满意。回忆往事,崇敬之心,怀念之情,无时或已。
李鸿寿的这番发自内腑的话语,能够代表许多有识之士的见解,说明中央调整税收的决策和顾准推行的做法深得人心。
1951年3月,中共上海市委决定成立市财政经济委员会,潘汉年兼主任,顾准与许涤新兼副主任。同时决定让顾准放下市税务局的日常工作,移到市财委去办公。至此,税务局作了某些改组,局长仍由顾准兼(直到1952年7月),日常工作由副局长朱如言主持,但重大的事情都经过顾准的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