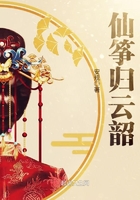“这样呢?”叶浅将她搂在更紧,换作平时可能就要无法呼吸了,可是现在她已经不在乎,她这辈子放的开的时候不多,公主的身份限定了她太多,也压抑了她太多,而今终于可以什么都不去管它了。
她的眉心微微蹙起,伸出手指,轻轻拭过他温热的脸颊,说:“这样好点了。”
他抓着她的手,指尖带着抹不去的凄凉:“你答应过不离开我的,你不是说等我们回楚国,就和长阳王说让你离开,这辈子都跟着我?现在还没到楚国呢,你可不能说话不算。”
娉婷声音脆弱且无力:“现在……恐怕不行了。”
“不会的。”叶浅突然固执的说道,声音那般大,回荡在树林里,像是一圈圈飘曳的叶子,他使劲的握住她的手,似乎在同什么人争抢一样:“你不会有事的!”
娉婷看着她,虚弱一笑,那一笑突然好似一只锥子一样扎入了叶浅的心,他是那样的惊慌,几乎带着乞求道:“别走,别走好不好?”他满脸无助,像是一个孤单的孩子:“你有没有想过你不在了,我怎么办?我一个人该怎么办?”
风突然大起来,月亮在透过树叶洒下一地的斑驳的银白,说不出的冷清与凄凉,叶浅的喉咙仿佛是被人咬住了,狰狞的疼痛。
月光斜斜的照在他们的身上,依稀间,似乎又是很多年前的那一场相遇,眉眼如画的玉面少年,在转身的刹那,明亮的面孔,好像初升的朝阳,如黑色玛瑙石般美丽的眼睛,比雨后的天空更明净,更清透,仿佛有光影在其中流转。
他看着她。
她也看着他。
看着他面颊上徐徐绽放出一丝柔和的笑容。“你,是不是在找人?”
岁月如同一场大梦,繁牟卸去,剩下的只足一片浓重的苍白。
娉婷看着他,目光凝于他微微敞开的胸口,一个银色吊坠露了出来,上面镶嵌着一块月白色的小石头那是小时候她送给他的,没想到他还戴着原来,他的心里有她,一直都有她。
如果没有这些恩怨,如果他们能够早一点重逢,是不是一切都会不一样了呢?
不过现在想这些已经没有用了吧。
在最后一刻,她努力的抬起眼望着他,她的目光那样深,仿佛穿透了记忆的沧海,掠过了时光的桑田,温柔的停驻在他的身上,久久不愿离去。只听她凑近他耳边,声若纳蚊道:“叶浅,我喜欢你。”然后她缓缓地闭上眼睛,嘴角血渍未干,却凝着一丝动人的微笑。
我喜欢你。
突然间,好似有一声裂锦般的戈弦响起,瞬间演化为一道惊雷劈天盖地的席卷过来,声势浩大的足以将世间一切毁灭,叶浅如同负伤的野兽歇斯底里的喊道:“娉婷!”
疼痛,非常缓慢,非常沉重,一下一下,然后才是痛楚,很细微却很清晰,慢慢顺着血脉蜿蜒,一直到心脏,痛不可抑,痛到连气都透不过来。
叶浅有点茫然的看着娉婷,就像不认识她,或者不曾见过她。
要不然这是个梦,只要醒来,一切都安然无恙。
可是没有办法再自欺欺人,她的身体还是温热的,前面还在听他说那些往事,他以为他一辈子也不会开口的往事,他不奢求她理解,可是她不仅理解还选择原谅,她这么善良这么宽容的女孩子,怎么能就这样死去呢?
他紧紧抱着她,脸上绷得发疼,眼睛几乎睁不开,五月的树林夜色绮丽,空气中散发着青草味和淡淡花香,可却仿佛是一种毒。
这样疼……从五脏六腑里透出来,疼得让人绝望,他一遍遍的喊着她的名字,希望这样可以唤醒她,就算任何人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他也不希望是她,上天怎么会如此残忍?
叶浅的眼睛仿若燃尽了的余灰,死死的冷,他低下头看去,她的面容平静在月光下恬静美好,仿佛一个闭着眼睛的瓷娃娃,正陷入一轮好梦之中。
他仰起脸,大风吹起他单薄的衣衫,空寂的天空上,有一颗仓促划过的流星。
自懂事以来,他已习惯于策划。
做的每一个决定都不是无的放矢,必需经过周密的考量,制订一个详细的计划,把每一个细节都算计进去,然后严格地按此做执行,绝不容许出现任何偏差。
至今为止,从无例外。
因此,他得到了所有他想要的东西,也击败了所有他想击败的人,更达到了一切他想达到的目标。
按照他的计划,他正不出意料的,缓慢但是坚定的一步步迈向权利的巅峰。
然而自从遇上她,他的计划被全盘打乱,他低估了她,在自己心目中的份量,也高估了他自己,以为不会这么在意她。他从没想到会在势在必得的时候毒发,计划中的重逢,出场的时间和地点都拿捏得十分精准,完美得不容任何人破坏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竟然再一次的失去她。
不仅仅是她,而是全部……
暗淡的灯光照在夏侯琰的脸上,越发显得他毒发的脸庞惨白若纸,嘴唇没有一丝血色。他卯足了力气撑起身体,顿时觉得天旋地转,不得不又躺回去。
抬眼打量周围,这是个客房,偌大的床上他一个人了孤零零的躺着,背脊上黏糊糊的,被褥周围也有些湿漉漉的,他一定是出了很多汗,怪不得口干舌燥。
“来人!”
他轻呼一声马上有人进来,来人正是柴剑。
柴剑看到夏侯琰虽然刚刚转醒身体还十分虚弱,但是一双眼睛却黑的好似暴风雨欲来的天空,剑眉斜飞,写满了冷酷与愤怒。
“人抓到了吗?”
“属下无能。”柴剑低头道。
夏侯琰虽然被周身的疼痛折磨的冷汗直冒可是目光却锐利如刀,幽深如夜,杀气腾腾。
柴剑触到他冰冷的目光,锐利如鹰,从心底激灵令打了个寒颤,不由眉头拧了起来,也不敢抬头与他对视,只能小心翼翼地说:“他们都受了伤逃不远的。”
“废话!”夏侯琰怒道,那些人当然是难逃一死,但是娉婷呢?她的脖子上的伤口很深,伤口可能会感染,她会发热会很疼会昏迷,她总是能够最轻易牵动他心里最柔软的地方,她让他一次次心软一次次担心即便到了这样的时刻他可以对自己不管不顾,但是对她却不能。尽管她心里没有自己,可是他的爱已经付出,覆水难收。
“公主她”柴剑欲言又止。
“她怎么了?”夏侯琰猛地坐起来,也不管浑身的难受,他突然有种念头,也许刚在那没由来的心痛不是幻觉,而是她已经,已经……
“她已经死了。”
夏侯琰蓦然一呆,似乎没明白他说的是什么。
他一字一句的问:“你刚才说什么?”
“公主死了。”
他身子狠狠一晃,强行压制住所有波涛汹涌的情绪问:“她是怎么死的?脖子上的伤口不足以致命她究竟是怎么死的?况且连尸首都没看到,你凭什么说她已经死了?”
“自古红颜祸水,那样的女人留不得,会坏了大事!”柴剑跪下来,虽然害怕,但是却有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决绝。
“你竟然杀了她?”夏侯琰瞳孔微缩,伸出手指,指尖颤抖,苍白的脸色阴郁的可怕,有着地狱般的恐怖凶神恶煞。
“是。”
“你竟敢”夏侯琰挣扎着起身下床,可是双脚刚着地只觉得膝盖发软眼前发黑,排山倒海的愤怒充斥着四肢百骸,他目光凶狠,声音剧烈的颤抖着:“谁给你的胆子?你说!”
柴剑看主公气得发抖,心下虽然害怕但是也豁出去了:“属下不才,擅作主张,还请主公责罚。”
夏侯琰吃了软钉子更加怒不可揭,无奈身体虚软无力,不能一掌劈了他。
一切都于事无补,理智告诉他在那时那地如果不能留住她,那么唯有让她没法活着回去才有可能保全自己,才能保全这些年辛苦创下的事业,才能保住缤城,可是不该是这样。
她不是说,死也要看着他先咽气么?她不是说,要他不得好死,要看着老天爷怎么来报应他么?既然这么恨他,他还没死,她怎么能先死了?
夏侯琰要杀柴剑可是浑身没一点力气,只能死死盯着他。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我不相信,这不是真的,我不相信。”
“属下已经派大批人马追踪他们,不久后就能截下他们,届时,应该能看到公主。”柴剑低着头回答。
看到她?
看到她?
看到她的尸体么?
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击中,他所有的力量与念想希望全部被掏空,他突然感到生命的空虚无力,愤怒的眼神变得涣散,苍白的脸血色褪尽,良久,发出一声低哑的笑,咬牙切齿地发出一个音节:“滚!”
柴剑跪着不动,雕像似地。
夏侯琰不再说一句话,一只手紧紧捂住胸口,额角源源不绝的渗出冷汗,身体颤得厉害,紧紧握住已经泛白的指节,突然身子一倾,吐出一口血,殷红的血洒在身上,现出一种异样的妖。
他喊出那个名字,像痛苦得不能自已了,嘴唇开合几次,才能发出声音:“娉婷,你不会死。”然后一头栽倒在床上。
楚国。
经过会诊后,所有大夫认为刘梓宣中毒的可能性非常大。并且一致认为,毒药都必须通过饮食,进入五脏,毒损心窍,一旦毒发,立即毙命,可皇上的症状却是慢症。他们又已经仔细检查过皇上的饮食,没有发现任何疑点。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皇上的所有饮食,都会有太监先试毒,没有任何太监有中毒迹象。玉玲珑每顿和刘梓宣吃一样的东西,也没有任何不适。
这究竟是什么毒,是如何神不知鬼不觉的进入刘梓宣体内,又该如何排解,竟没有一个人说得出来。
刘梓宣的眉头微微皱起,脸上的表情十分严肃,少有的怒意出现在他一贯平静的脸上,吓得一个个太医面色如土,而宁妃找来的民间大夫也是束手无策。
刘梓宣的神色有些疲惫,从恼怒到无奈,最后他挥了挥手吩咐:“这件事不得对外宣称,若有官员问起,说是风寒不碍事。”扫了众人一眼,又道:“好了,都下去吧。”
玉玲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刘梓宣最近虽然看来起来并没有什么大毛病,可是总是头晕乏力,有时候会胸闷心痛,半夜里会突然惊醒,一身的冷汗,手脚微微浮肿,身体日渐清瘦。
怎么会这样呢?
经过本朝最好大夫的会诊竟然会完全没有头绪,而且日趋严重,她真的不敢想以后会怎么样。
这天晚上,两人面对着面,都分外沉默。
玉玲珑轻轻抱住刘梓宣,双手环着他清瘦的腰身,心里十分难过,不禁又往他身边靠了靠,又靠了靠,直到紧紧贴着他。她紧紧抱住他,耳朵贴在他的胸口,听着他的心跳声。刘梓宣的身体有些僵硬,一时间并没有反应。玉玲珑的身子轻轻颤着。刘梓宣终于也伸手抱住了她,越来越紧,用尽全身力气,好似只要彼此用力,就能天长地久,直到白头。
玉玲珑低声道:“宫里的太医也许都是好大夫,却绝不会是天下最好的,我们再去民间寻访,一定能找到更好的大夫替你解毒。放心吧,你一定会没事的。”
刘梓宣抬手抚着她光滑柔美的脸颊,点头说好,可是却掩不住神色中的憔悴与失望。
他第一次想要挣脱所有的束缚做自己想做的事,可是计划刚刚开始实行,就碰上这样的变数。他感到害怕,不光是对未知的毒素,还有不能兑现诺言的惶恐,他说过要和她远走高飞长相厮守的,怎么能因为这该死的毒失信于她?
想到这里,内心骤痛,这种尖锐的疼痛一瞬间传到胸口,他的手一下按在了胸口上,额上冷汗涔涔。
玉玲珑大惊,立即去扶他:“梓宣,梓宣?你怎么了……我去喊太医!”
刘梓宣扶着玉玲珑的手,才能勉强站稳,过了一会儿后,胸口的疼痛才缓和,他说:“别去了,没用的。”
“可至少可以施针减缓疼痛啊,这样不行的。”她知道刘梓宣的自制力非常好,所有的喜怒哀乐病痛难受都可以不动声色的压制住,即便在发着高烧的时候也可以在朝堂上侃侃而谈,可是现在他的身体却在微微颤抖。
“梓宣。”她紧紧的抱住他,身体尽量支撑着他,她感觉到他的身体是那样的轻,那样的无力,好像轻轻一推就会倒下去,这还是她认识的意气风发风神绝世的傲气男子吗?
她的心很沉很沉。
她要为他做点什么,决不能这样下去。
第二天.长阳王府。
刘修祈刚下马车,守门的家丁就禀道:“王爷,有位姑娘来拜访。”刘修祈淡淡点了下头,倒是有些意外,平时长阳王府除了一些巴结讨好他的人并没有什么来客,他所交往的人虽然各有来头却都是止于相关利益的浅谈并无深交,更不用说有什么女子会认识他。
“哦,什么人?”
家丁说:“她没有说名字,只说找阴药师,小人告诉她药师不在,她却不信,非要进去不可。”
刘修祈立即问:“现在人在哪里?”
家丁说:“在大厅。”
刘修祈顾不上换下朝服,直奔内府而去。到了大厅却没有人,只见一个家丁在打扫,他问:“人呢?”
那家丁有些慌张,答道:“那姑娘坐了一会便走出去了,她对这里熟门熟路的,来去如风,谁也拦不住她。”
“她还在府里么?”
“往花园方向去了。”
绿荫蔽日,草青木华。一条小溪从花木间穿绕而过,虽是夏季,可花园四周十分清凉。
刘修祈沿着小径,边走边找,却也不见人影,心下有些着急,忽然想到什么,抬步走向夙澜居。
果然,刚到了夙澜居,看到门半掩,推门而进。
绕过几株金橘,行过几竿南竹,看到玉玲珑坐在藤椅上,微闭着眼睛,头顶是一棵石榴树,繁花怒放,灿若云霞,花红似火,分外鲜艳,红色映衬着她清丽绝伦的脸,美得几乎令人屏住呼吸。
刘修祈轻轻俯身,在石榴树下,静静地凝视着她。石榴花清香扑鼻。
玉玲珑的眉头蹙着,睫毛微微颤动,看起来心事满满。
两个月不见,她似乎瘦了不少,下巴尖尖,锁骨凸显,即便闭着眼睛,神色仍然是忧郁的,她不是被那个人捧在手心里宠爱着么,怎么也会露出如此叫人于心不忍的模样?她不是应该趾高气昂的对他宣称不要打扰她,不是应该早就把他这个人抛到九霄云外享受着神仙眷侣的生活吗?
她似乎是感觉到有人,突然睁开眼睛,看到刘修祈。
“你什么时候来的?”她有些尴尬,明明是气势汹汹来找人的,怎么不知不觉在院子里睡着了。
“这个问题我还想问你。不在宫里做你的皇妃娘娘,跑来长阳王府做什么?难不成你是思念故居了故地重游?”刘修祈一开口才发现自己的语气不无嘲讽,也许他只是太意外了,其实这并非他的本意。自从那天下雨他去宫里看她,明着是恭喜她被册封为妃,其实是去挑拨离间的,他知道她和刘梓宣一定有过争执,刘梓宣后来几天都没有上朝,说他心里不得意是假话。
后来知道他们和好了,而且越加的好,几乎形影不离,他又是欢喜又是担忧,欢喜的是刘梓宣越来越在乎她了,这对他来说是好事情,担忧的是她这样的女子,一旦爱上一个人是会因爱成狂的,为了刘梓宣什么事情都是做得出来的,这样一切就变得难以掌握了。
“我可没这么好的心情,这里没什么好留恋的。”玉玲珑冷冷说:“阴药师人呢?”
“就像你看到的一样,他不在这里。”
“不在?”她眯起眼睛看他,并不相信:“他在哪里?”
“去很远的地方办事情了。”刘修祈很平静的说:“你找他有事?”
“自然是有事。他什么时候回来?”
“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他说的轻描淡写,却不料胸口一紧,衣服被她揪住,她的眼里满是不信任,还带着一丝恼火:“早不在晚不在,偏偏这时候不在,你是不是故意不让我见他?”
刘修祈拉住她的手冷冷甩开,微怒道:“我根本不知道你会来,何谈是不是故意的?”
玉玲珑见他如此说话,自知明明是有求于人这样说话只会让他反感,不由放软了语气:“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找他。”
“他是真的不在楚国。”刘修祈见她态度好转,语气也缓了一些:“他去了西域办事,几个月都回不来。”
“能联系上他么?”
“恐怕不能。”刘修祈的语气绝不像开玩笑:“你有什么事情,可以和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