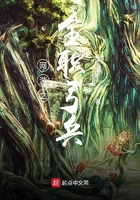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黄彩玉遭受了许多屈辱,但其间也不乏人间的温暖。那些来自乡亲的同情与帮助,曾给予了她无限的感动。他们的一言一行,看似那么细微,那么漫不经意,却蕴藏着最朴素的人性关怀。
“大跃进”时,象山掀起兴修水利的高潮。大小水库上马,万余人上工地。黄彩玉作为受惩罚对象,自然得上前线出力。她像男人们那样,掘土挑泥打夯,挥汗如雨。
“叫高山低头,河水让路!”在豪言壮语下,人们不顾朔风凛冽、雨雪纷飞,为“提前实现农业纲要四十条”而早出晚归,拼命地赶任务。
毕竟是女人,再说黄彩玉个子又长得小巧,长时间的强体力劳动使她不堪重负。同乡有几个男人看在眼里,有时会暗暗助她一把。
人常说寡妇门前是非多,再说她又是地主婆。黄彩玉每每见有人帮她,也不敢开口道谢,怕人听见说闲话。
在山坡掘土,看到同乡用锄头挖起的泥土纷纷落在自己的畚箕里时,彩玉便默默地心领神会于他们的一片好心。偶尔见边上嘈杂,趁人不注意,她也会与乡邻攀谈几句关于家常与农事的话。彩玉自感成分不好,怕连累人,原本性格内向的她,被接二连三的运动搞得越发沉默寡言。像这样劳动中的平常交流,对她来说也是极少的。她主动与人攀谈,往往也是出于对人家好意的回应。
让黄彩玉最感动的一回是“扔军刀”。
说起来这事还得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初,那时正掀起“镇反”运动,腥风血雨。王松甫有个嫡亲侄子曾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官,村里人揭发他有一把黄埔军校发的军刀,据说上面还刻着“蒋中正赠”的字样。
如果这事属实,在当时可是杀头的罪名啊!揭发者说得有根有据,而且不止一人见过这把军刀。
与王松甫一样,这个侄子平时也爱好搓麻将,搭子们聚在一起时,他免不了提起过去的军营生涯,说到兴头处便拔出明晃晃的军刀炫耀……
人命关天,王松甫的侄子自然不肯承认。于是,领导们下令严查军刀下落。村里也有许多血气方刚的运动积极分子,角角落落搜不着,竟把附近小河、池塘的水抽干。但寻得底朝天,仍不见军刀的影子。虽然侄子因历史问题,也常常与彩玉一起同台遭批,但因没有铁的罪证,不至于被判死罪。
没想到若干年后,这把军刀却落在了黄彩玉手里。
那刀真的是扔进河里了,不过不是在附近,而是离木瓜很远的一条河,况且地处偏僻,难怪以前没找到。
兴修水利把河占了,埋没的军刀才见光。这天,正在填土筑坝的黄彩玉踏着了硬邦邦的东西。她低头一看,见淤泥中半露着金属似的物品,不由弯身去捡拾。感觉沉甸甸的,抹去黑乎乎的河泥,不由惊诧:什么东西这么贵重,还套着盒子?拿出一看,天哪,这不是曾经兴师动众寻找的军刀吗?!
她来不及细想,赶紧把刀放进盒子,然后又急忙把它埋入河泥中。但想想不对,如果被人发现传出去,侄子岂不要遭殃了?于是,她又挖出来想藏到自己的畚箕里去。可是军刀的长度超过畚箕,藏不下!
黄彩玉的举动,正好被在近旁打夯的人看到了。他过来,对彩玉悄声说:“你背不起罪名的,我是贫农,还是交给我去处理吧。”
彩玉抬头见是同村的老王,常常帮她铲土的。但她犹疑道:“这东西扔到哪里好呢?被人知道要闯大祸的。”老王二话不说,一把拿过军刀藏进自己怀里,说:“放心,我有办法。”他边说边转身快步离去了。
后来,彩玉得知老王把它扔到大海里去了。那天,他先是把刀藏在附近比较隐蔽的树丛中,因军刀长,衣服里藏着露出一截走路怕人看见。等到半夜三更,老王再偷偷出来取刀,跑到海边去扔掉。
黄彩玉在村里的人缘一直很好。世态炎凉,人情冷暖。运动中,尽管有些人难免有势利言行,但彩玉很谅解人,并不计前嫌。她会用一种土法治疗孩子的疳积,很见效。那时候谁家的小孩消化不良了,都会来找她治一下。彩玉用缝衣服的针在火里烧一下,算是消毒吧。然后,她就在孩子手指头穴位上挑,挤出里面的黄水,孩子就会吃饭了。
说来也真奇怪,针扎过后的地方挤出来的不是血而是黄水。自古人们就用这种方法治疗孩子的疳积,从前农村的人多数都知道这个方法,只是很多人不懂穴位,所以不会扎针。
村里有个妇女,曾经散布流言蜚语,并与彩玉当面过不去。可一回,她儿子得了严重的消化不良症,中西药吃了不少,还是不见效。无奈之下,她尴尬地找上门来。
善解人意的彩玉安慰道:“没事的,不用担心,扎几针就会好。”她动作娴熟地把孩子手指头的穴位一一挑了。
彩玉的大度,使那妇女感到很歉疚。有时,在田头双抢劳动时,遇上下雨等紧急情况,她也会和自家的男人一起,帮彩玉一把。
那时期,黄彩玉参加修水库、修公路等义务劳动不断,有的地方较远,一去就要好几天。因不放心家里的儿子们,她临走前总要对邻居阿婆阿婶们嘱托几句。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其实,那时可行、乐宾、阿光,生活都能自理了。况且家里找些吃的也有,虽然“共产风”余热还未完全消退,但因公共食堂的散伙,后来对农民的控制也有所松动,允许社员们在自己的屋边、地边垦植,种些蔬菜杂粮。
于是,会精打细算的黄彩玉,在荒芜的小园里又种起了南瓜、青菜、萝卜等,平日够家里人粗茶淡饭将就过日子。那时,农作物还不敢多种,怕“量变到质变”,多了就要算作资本主义。鸡、鸭也只能养一两只,三只以上是万万不能的,因为有三五成群之说。
王泽光回忆说:“村里有个堂房阿哥,就因为多养了几只鸭子,被当作搞资本主义的典型。结果他挨批,连我娘也一同上台陪斗。”
玩乐是孩子的天性。在娘外出修水库、修公路的日子里,家成了“小喽啰”的天下。老二乐宾颇有江湖义气,“狐朋狗友”多,邻居的孩子们都“哄闹热”跟着他一起聚会来了,大的十多岁,小的五六岁。大家同吃同睡,晚上挤在床上,棉被拉来拉去,脚踢来踢去,嘻嘻哈哈玩成一团。
乐宾动手能力强,小脑筋也蛮会转。家里的灶头就是他打的,烧点东西吃吃自然不在话下。这时候,通常是老二烧菜烧饭,老三旁边配合做帮手。老大可行是一副小老爷作风,往往袖手旁观,偶尔发几句话。
家里吃了不够,他们还到外面去“偷吃”。其实,也是想到野外疯玩。时值盛夏,那些孩子们四处偷人家的西瓜、桃子、李子等。因没节制地乱吃,又不讲卫生,结果一伙人全拉肚子了。除了老三阿光,他从小循规蹈矩,一般野蛮的事不会去掺和。
回到家,阿光见他们个个捂着肚子,痛得在床上翻来覆去“嗷嗷”叫,暗暗觉得好笑。可是,见伙伴们这般痛苦的样子,他也有些担心。于是,他就会去叫隔壁的阿婆或阿婶。她们来到屋里,边责怪边说是吃热了,于是不管三七廿一统统刮痧气,那帮孩子又痛得哇哇叫……
晚上,阿婆或阿婶会烧些粥来给孩子们吃,说拉肚子了不能吃不消化的东西。
远亲不如近邻。遇事相帮,多年的乡情让出门在外的黄彩玉感到踏实。有时要紧关头,即便帮不了忙,但相邻的一声招呼与问候便让人觉得安慰。
“文革”时,家里被“大扫荡”了两次。第一次来抄家前,有邻居已得知风声,悄悄告诉彩玉:“他们要来抄你的家了,如果有什么东西需要藏的,先到我们屋里放着。”彩玉领情,但不想连累邻舍,而事实上经过多次运动,家里早已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只是每次来扫荡,总让人心惊肉跳。
一家人全被赶到外面,任造反派们抄个彻底。
其实,家里最值钱的东西在角落里,历次运动都没被发现。确切地说,是没懂行的人,都不知道这些沾满灰尘的旧纸,竟是珍贵的文物。那就是书房阁楼中的那些画,它们有的是祖上传下来的,有的是王松甫在世时人家送他的。
可这些画,最终还是在劫难逃。文革要破“四旧”,那些古画当然被造反派视作“封、资、修”而付之一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