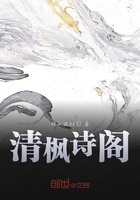现在想起来都不知道是物理反应还是化学反应,当时的情景不是诡异所能概述的,也正因为这一次的事件让我相信了《点穴风水》。当时大家都想尸体冒完白烟,然后化成一滩脓水,一切不了了之。可
这是我们大家的想象,现实是尸体嘴里发出“呜呜”恐怖的叫声,低沉而又模糊。可能是她疼痛吧,真搞不懂完全僵死的尸体为何还能攻击活人,无敌的她竟然怕那半碗鸡血。没多么会,浓烟滚滚也变
成了一丝青烟,鸡血好像是失效了。
我发现大家的脸随着白烟的慢慢的消逝变的惊恐起来,每个人都把已经放下的镐头、铁锨之类的又握在了手里,一副虎视眈眈的样子。我得承认我是里面最紧张的,甚至紧张程度超过了张家的父子,也
可以说是惊恐吧!前两次尸体的攻击目标只有我一个,如果鸡血没起到什么作用反而彻底激怒了她,恐怕我这次危在旦夕了。不过看这个僵尸还是有些思想的,按理僵尸应该把矛头换成张家老汉,因为
是他给泼的鸡血,顺利自然吧!
或许是我多虑了,尸体最后也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只是接触过鸡血的地方变的黑乎乎的一片,如同烧焦的木炭。直到一阵风吹来,尸体终于栽倒在地上,众人也喘了口大气。张生是第一位冲上去查看
尸体的,他的心情到底有多复杂也猜不透了。自己的媳妇刚亲热没几天不明西去,自己还没来得及伤心又发生尸变。好不容易请了个神婆子唱唱跳跳,本以为一切安静了,没想到今天入土又来了这么一
出。如果媳妇活了过来,从灵柩里面爬了出来,他能乐掉大牙。如今是爬了出来,不过不是和他继续过日子,是要带他一起入土,这失望加绝望啊!
最后还想再次入殓,瞧今天这情景怕以后再从坟里爬出来,最后还是大家一起搂草火化了她。其实当时国家就开始要求尸体火化了,不过一些偏远的地方思想闭塞,始终不能接受尸体焚烧,怕影响第二
次投胎转世。大家得到张生和他父亲的授意之后,找树枝和杂草,围了一个比人高的草垛,众人把尸体架了上面去,这次滚起了浓烟。秋季干燥,树枝之类的遇火就着,加上北风吹着,一会火光冲天,
一片火海。大火来的快,去的也快,尸油似乎比煤油还爱着火,瞬间尸体也化了灰烬。张生拿着杆子进去扒拉着灰烬,找出了头颅等几块大的骨头,用布垫着,收集在了一起。棺材又重新修了修,破的
地方也补了补,把捡到的骨头按着顺序给摆了里面,最后封棺入土。
记得当时虽然在上风处,但现场的气味真的让人难受。那天尸体的腥味我都忍受着没吐,这次焚化的烧焦味让我恶心了一天。不是说单纯的肉糊了的味道,是那种臭味加些酸味,而且还掺杂写烂鱼烂虾
的臭味。入棺封土之后,张生在坟前倒是哭的声嘶力竭,捶胸顿足。可能是他缓过劲来,知道这次真的是和她媳妇天地永别了,大男人哭出来也就马上好了。最后张家老汉把那无头的公鸡叫我们带回去
熬汤吃了,但是当天的五脏没有福分,回去恶心的吃喝了几口茶,连动筷子的欲望都没有了。
这次僵尸的事情就告一段落,后来也没发生什么怪事,一直也风平浪静的。就是第二年的时候张生的父亲就是张老汉也去世了,当时村庄里的流言蜚语也比比皆是。最后张生在处理完父亲的丧礼之后移
居到了外面,这些年也没有人再看见过张生回来。我们这些知青也被村干部叮嘱了几次,不要对外讲村子张家发生的怪事,反正我是没有乱嚼过舌头。不过没有不透风的墙,后来村子里人人皆知,而且
谣传的更加神话。什么青面獠牙,身高八尺之类的假话传的多了也有人信了,不知道过了几代人之后,会不会也当作一个传说流传下去呢?
在那时,知青们的思想算是彻底洗脑了,每天都是在地理埋头苦干,大家手上的老茧大部分都是当时留下来的。我右手上的一条伤疤不是刀伤之类的残疾,就是当初握着镐头之类的工具磨合出来的,流
血之后随便一包然后又扎了人群里比赛。每天大家都会比谁的劳动成果多,谁的力气大,苦并快乐着。那本《点穴风水》我也没有放下,看书成了我每晚的必备功课。夜晚自己也想,古墓中那么多的惊
险和刺激,等以后有机会了我到底去还是不去呢?
过了十五不愁过年,在不知不觉中春节也马上到了。我们中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在外地过年,大家的思乡之情不言而喻。幸好农村里的过节气氛很浓烈,代替了我们的思念和孤单。到了小年的时候大家
做豆腐,煮猪头,蒸馒头,不亦乐乎。还有豆包子,菜包子等等,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真正的吃上白面饽饽,而且份量足够你大吃特吃了。山东的煎饼也不得不提了,也是在冬季临近过年的时候,家家
户户都泡上麦子或者玉米,研磨成浆糊倒入鏊子,用煎饼筢子摊平烙制而成。配上大葱和豆瓣酱,真是人家美味。
在下乡的这几年里,我的性格也变的很温顺,甚至可以说是很随和。身边的人见我没有什么心机,身世又那么可怜,大家也很照顾我。本来性格内向的我也变的健谈起来,偶尔也和大家幽默了一把。不
过爱新觉罗的本姓以及爷爷留给我的《点穴风水》我也没有和别人提起过,在我心中,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明天的太阳总是会升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