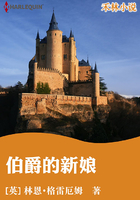这家寿器店“****”前叫宋记寿器店,远近有点名气。木材全是东北红松的,埋在地下百年不烂。“****”开始后不久,作为“四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被封了门。店主宋福寿被揪斗游街。剩下的几口寿器藏在草垛里。这两年,批斗的风潮一降,慢慢有人又找翟上门来定做。有些造反派头目的考妣之丧也来挑选。店主宋福寿见没事了,又默默操起旧业。大的小的厚的薄的标准不一,由用主选择。这种死人用的东西没谁敢说他家不用。再者,造反的红卫兵们也讲迷信。有一个红卫兵当时砸棺材时,一铁锤敲在自己腿上,棺材板子没砸断,自己的腿断了。就有人说是被鬼神魔着了。此后,他们宁可得罪活人,也不敢得罪死人。就再无人来寿器店查封、批判、揪斗。
甘薯疤和地瓜油找到这家寿器店,店主宋福寿领他俩进了后院。
宋福寿指着两口黑光油亮的棺材说:“这个尺码的还有两口。这是富贵棺材,纯大兴安岭红松的,庄重肃穆。你们随便挑一口。”
地瓜油看着这些棺材说:“操,寿器寿器的,把我寿器进胡黍玺地里了。这不就是棺材吗?”
甘薯疤:“你连寿器是什么都不知道。等你死了不用棺材、用胡秸箔帐卷巴卷巴埋了就行。”
地瓜油:“活着让我吃好喝好享受好,死了扔给野狗吃了也无所谓。”
地瓜油摸着自己的肚子说:“我肚子真饿了,你听,打鼓似的,咱装上棺材吃包子去吧。”
甘薯疤:“好。出门不能饿着。尤其帮忙办丧事,更要吃好点。”
甘薯疤和地瓜油伏下身抬那口棺材,抬了一下,抬不动。店主宋福寿笑着说:“你俩要是能把整个棺材抬起来,那就不是我宋记的了。先把材天抬下来,将材身抬上拖拉机,再把材天扣上。分两次就抬动了。”
两人按照店主的指教,将棺材抬到拖拉机斗里装好。
甘薯疤问:“路上下雨怎么办?”
店主说:“没关系,宋记寿器缝严漆匀,不怕雨的。”
甘薯疤开着拖拉机来到高密城里,在大街上找了一家饭馆。每人吃了十个包子,喝了半斤烧酒,感到身上热乎乎的了,就开着拖拉机往回走。
甘薯疤说:“你坐后斗里看着点,上崖下坡时别磕着碰着的,去了漆回去不好交代。”
地瓜油:“放心吧,你慢点开没问题。”
拖拉机出了高密城,雨点就密了起来。甘薯疤从工具箱里拿出雨衣披上。地瓜油喝了点酒就想睡觉。他穿的单寒,衣服一湿,东北风吹在身上直打寒战。他缩在棺材西面,想用棺材挡风遮雨。不会,脸上就往下淌水。他端详了一会棺材,心想,到里面躺着睡觉,又暖和又舒服。反正是新的没睡过死人。鲁老爷子没用,我先用一会。就掀开棺材盖,爬了进去。
高平路是沙子路,下了雨坑坑洼洼的满路是水。顶着风雨,甘薯疤开得很吃力。拖拉机走不快。
大约走出五公里左右,前面一个姑娘推着辆凤凰自行车转回身来向他招手。衣服一湿,姑娘的身体显出好看的曲线。甘薯疤见姑娘有点姿色,说不定今天能交上桃花运呢。就停下车问:“去哪?”姑娘说:“白沙公社。”
甘薯疤说:“好,一路的,上车吧。不用我帮你搬自行车吧?”姑娘说:“不用了,小车子,轻快。”姑娘先把自行车搬进斗里,又爬上去。
上车后,姑娘才发现拉的是口黑漆棺材。她心里有点紧张,可是已经上来了,车开了也不能再下去。何况雨下得这么急,顶着风走不动。反正时间不长就到了,饥困了吃鼻涕,没办法。
拖拉机一颠一颠的,棺材不时地发出响声。姑娘心里越害怕,两眼越盯着棺材不放。棺材盖好像动了一下,又动了一下,她以为看花了眼。揉揉眼,看到还在动,并且越看动得越厉害。棺材盖边下竟然开了一道缝,里面黑黑的。难道棺材里有死人?就在她吓得浑身战栗,牙齿得得响的时候,猛然间从棺材里伸出一只黑手,张着五指向空中乱晃。
“鬼!”姑娘高喊一声,跌倒在车斗里。
由于风大雨急,加上拖拉机的轰隆声和棺材的颠簸声,甘薯疤没听到,地瓜油也不知道斗里还有别人。
甘薯疤开着拖拉机进了公社家属院,雨暂时停了。地瓜油从棺材里爬出来,看到棺材旁躺着一个女的,吓了一跳。尖叫一声:“我的娘哎。甘薯疤,甘薯疤,你快过来看。”
甘薯疤脱下蓑衣往工具箱里放,斥责道:“叫魂啊,什么事这样急?”
甘薯疤光顾着开车,还忘了路上拉了个姑娘。过来一看,见姑娘脸如白纸,仰面躺在棺材旁。胸部鼻息看不出呼吸的迹象。他用手放在姑娘鼻子下一试,说:“糟啦,没气了,这可怎么办?”
甘薯疤瞅瞅地瓜油,地瓜油看看甘薯疤,老疖疤子瞅泥鳅,大眼瞪小眼了。
甘薯疤质问地瓜油:“你怎么把姑娘弄死的?”
地瓜油:“我还想问你呢。一上拖拉机我就爬进棺材里睡着了。她什么时候上来的我都不知道,是不是你搞的鬼。”
甘薯疤:“反正就你们俩人在后斗里,你干得什么事,你心里清楚。”
地瓜油:“你是属鳖的,咬人不松口?咱俩去找夏八斤吧,看看怎么办。”
夏八斤刚从饭店里回来,看到拖拉机停在院里就问:“拉回来?快找人抬进去,等着入殓呢。”
甘薯疤:“夏主任,麻烦啦。”
夏八斤:“多找几个人抬下来就是了,有啥麻烦的。”
甘薯疤:“拉了个死人回来。”
夏八斤问了声:“什么?”到后斗里一望,看见一位姑娘躺在棺材旁。惊得他张着个大口,半天才合上问:“这是怎么回事?”
甘薯疤把路上下雨遇到姑娘搭车,让她上了拖拉机的说了一遍。夏八斤又仔细端详着姑娘那张苍白的脸,突然“呀“的一声惊叫道:“是她——”
甘薯疤轻声问:“你认识?”
夏八斤随便“嗯”了一声,转惊为喜。心中暗暗说道,这会再没有找我麻烦的了。可是毕竟人命关天,得马上向鲁反修汇报:
夏八斤把甘薯疤和地瓜油骂了一通:“**操的,叫你们去找棺材,谁叫你们拉女人。人死了,判你俩的刑是小事,给鲁主任惹了大麻烦怎么办?”
夏八斤找到鲁反修,悄悄地把事情的过程说了。
鲁主任很恼火,说:“八斤,你这是办得些什么事。本来我心里就很乱,这不是乱上添乱嘛。”
夏八斤:“鲁主任,你别生气。都怨我派了两个不地道的人惹的祸,事情情办得这么糟糕!”
鲁反修:“遇上了,也没办法。你们先把棺材抬下来,别误了入殓。我通知医院院长,把姑娘的尸体拉到医院冰起来,丧事办完后再处理。马上打电话给忌三酒,让他立即向公安局报案。”
夏八斤:“好,这些事我亲自办。”然后又神秘地对鲁反修说,“鲁主任,你知道这姑娘是谁?”
鲁反修:“谯?”
夏八斤:“焦竹叶。”
鲁反修:“啊。”
五十
“东北风是坏风,早起来不下雨,下起来不起晴。”这既是当地的农谚,也是农民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
东北风吹着斜雨,不愠不火不急不慢地下着。中午停了一个小时,太阳在云彩里发了发光,农民称老天爷睁了睁眼,过午闭上眼睛又开始下起来。堪称是秋雨绵绵了。
各户家里的地瓜干有六七成干的,有三四成干的,还有新礤得没晒的。六七成干的和半干的好处理,只要有屋,在地上凉开了不发热,三天两天的坏不了。新礤的地瓜干放锅里煮熟,用盖垫,盘子晾着,天好以后晒成干地瓜。也有蒸熟了切成条的,放在锅里炒。最难处理的是三四成干的,边上发硬,中心还软,堆起来发热。时间长了,烂。放地里淋了雨,发霉,也烂。有的人家把锅和炕烧热在上面烘,只是烘得数量有限。遇到阴雨天,人们把心思都用在地瓜干身上,想方设法,千方百计把损失降到最低程度。有几户把这次分的地瓜竟然全礤了扔在地里。眼看着淋在雨里的地瓜干,心痛得滴血,老婆汉子相互埋怨。男人没处泄火了,就在家里喝闷酒打老婆。弄得全家老婆哭孩子叫的,好不凄惨。
仲地瓜把四间屋的檐下都等距离的栽上葵花杆,再把蔫了的地瓜蔓横着拴上,一道一道像拉电线似的。长蔓婆把礤好的那部分用刀一页页地从中间切上口,仲瓜蛋用篮子递给哥哥,仲地瓜踏着板凳从上往下挂。正屋是西南向,东北风雨淋不着,气温低又有风,地瓜干可以门屋檐下慢慢晾干。
仲地瓜大件医站打了五天防疫,昨天上午结束的。中午,崔淑花打饭给他捎了两个馒头,一碗炒菜。仲地瓜很不过意地吃了。过午,兽医站刘站长对今秋的防疫工作做了总结。在总结中,表扬了仲地瓜,并给他发了奖状。
奖状上的奖词是这样写的:
仲地瓜同志在一九六九年秋季生猪防疫工作中,表现积极,成绩突出,被评为生楮防疫先进工作者。
特发此状,以资鼓励。
白沙公社兽医站
一九六九年十月
同时,还发给他一张通知,通知是给地瓜庄大队的。通知上写道:
地瓜庄大队革委;
调你大队社员仲地瓜同志来公社帮助生猪防疫工作,已经结束。防疫期间,每天发给八角钱工资,三角作为本人生活补助,五角交生产队。望交款后给记同等劳力的工分。
白沙公社兽医站
一九六九年十月
仲地瓜领了奖状,支了补贴,与刘站长、崔淑花道别。崔淑花说:“先别走,帮我们千点活。”
仲地瓜问:“干啥?”
崔淑花说:“明天上午公社召开征兵工作会,发下标语口号让各单位写。刘站长叫我写,我没用排笔写过字,你字写得好,帮我写写。”
仲地瓜谦虚地说:“我也写不好。”
刘站长:“别谦虚,你就写写吧。我们站里还真没有能提起毛笔来的。
仲地瓜不好再谦让,把墨汁倒进碗里,拿着排笔跟崔淑花来到大街上。
崔淑花把刘站长在十个口号中下边划横杠的给了仲地瓜。崔淑花前面刷浆糊贴红纸,仲地瓜后面一个字一个字的往上写。
西面墙上写得是:应征人伍是每个青年的神圣职责!后墙上写得是: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刚劲有力的黑体字,赢得路人一片赞扬声。崔淑花听了,比仲地瓜听了都感到美。
崔淑花说:“明天上午征兵会结束后,下午适龄青年就可以报名。听说是四八年、四九年、五〇年出生的三个年龄段的。你在这三个年龄范围内,报名参军吧。”
仲地瓜的情绪马上低落下来说:“我倒想参军,恐怕夏八斤不能让去。”
崔淑花:“你回去先报上名。公社这边我找鲁主任和武装部穆部长通说通说。只要体检和政审合格,他们会同意的。村革委那边,你还得去找甘薯花,让她帮你做夏八斤的工作。尽管你与她断了关系,毕竟相爱了那么多年。我认为甘薯花不是那种薄情寡意之人,只是被逼无奈。”
仲地瓜:“谢谢你淑花。那我就碰碰运气吧。”
仲地瓜把地瓜干挂满了两间屋墙,又把长板凳挪到另两间屋檐下。他站在板凳上先往靠近屋檐橛子的地方挂。
团小组长甘薯好从街上走,看到仲地瓜站在板凳上挂地瓜干,招呼道:“地瓜哥,大队民兵连和团支部召开青年民兵会,传达今冬明春征兵工作意见,组织青年民兵应征报名,甘薯花书记让我通知你参加。”
仲地瓜应了一声,说:“好,我一会就去。”
仲地瓜昨天听了崔淑花让他报名参军的话,回来思考了半夜,分析来分析去,最大的障碍在夏八斤身上。自己的身体肯定没有问题,在学校多次体检都合格。家庭成分、亲戚关系也没有问题,都是贫下中农,就怕那次与黑面包的书过不了关。不过鲁反修当时说过,不做结论,不存档案。自己虽然不愿意再给甘薯花添麻烦,但不通过地做夏八斤的工作,还能找准?唉,既在矮檐下,该低头时得低头。他还是想硬着头皮找甘薯花帮忙。
仲地瓜来到青年民兵活动室,活动室里乱糟糟的,全村的青年聚到一块,就像几年没见面,说笑话的说笑话,掰手腕的掰手腕,拔萝卜的拔萝卜,仿佛有若干劲没使出来。
三队的田薯高见仲地瓜进来,说:“篮球运动员同志,咱俩拔个萝卜试试。”
仲地瓜:“试试就试试。”
田薯高和仲地瓜个子相当,身子比仲地瓜粗一点,也很壮实。
田薯高:“你先拔我吧。”
仲地瓜:“来吧,站好。仲地瓜两只胳膊扳住田薯高的身子,田薯高用力下蹲,仲地瓜一个猛劲,轻而易举地将田薯高拔了起来。
田薯高;“到底是篮球运动员出身,这么有力气。”
仲地瓜:“你拔我一个?”
田薯高摆摆手说:“拔不了你。你若是参了军,在部队上也是个大力士。”
甘薯贵和甘薯花手拿文件进了屋。甘薯花用眼睛与仲地瓜打了个招呼。
甘薯贵说:“大家安静一点,开会啦。先请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
甘薯花同志传达今年的征兵工作意见。文件不长,甘薯花用了十几分钟便传达完。
甘薯贵说:“文件精神大家都知道了。意义和重要性文件中也讲了。四八年、四九年、五口年出生的适龄青年想参军的,都到我这里报名。”
青年们立刻活跃起来,围着甘薯贵争着报名。
甘薯花看到仲地瓜在后面犹豫,走过去说:“先报上名吧,后面遇到什么事再说。”
仲地瓜悄声说:“那又要求你费心帮忙了。”
“什么求求的。”甘薯花嗔怪道。同时,给他一个信任的眼神。仲地瓜走上前去报了名。
就在青年们热火朝天应征报名之时,公安的两辆三轮摩托车鸣叫着停在大队办公室门口。青年们惊问出什么事啦?齐跑到门口往外看。
甘薯疤开着拖拉机拉着夏八斤和地瓜油也到了门口停下。三人从拖拉机上下来,两名警察走过来问:“谁是甘薯疤?”
甘薯疤说:“我。”